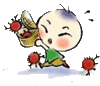但是,当艳遇的当事者是文学家的时候,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他们凭藉高超的叙事艺术,卓越的语言修养,把自己的艳遇写成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于是,他们的艳遇故事便会不胫而走,妇孺皆知,千古传颂。当然,广大群众通过阅读他们的艳遇故事,品味其中的诗情画意,或者心生羡慕之情,或者感同身受。无论是哪种阅读感受,都能得到莫大的快感和幸福。
作为文明古国、大国,咱们的文学史上,这样的作品是很多的。但是,我这里只举出一唐一宋、一诗一词两首作品作为例子。
第一首是唐代诗人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诗是这样写的: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诗背后的艳遇故事,是见诸记载的,大致是:诗人崔护到都城(长安)参加进士考试,落第了。清明时节,因为郁闷,便独自一人游览都城南部郊区。走到一处村居门前,只见院子里花木掩映。敲了好一会儿门,有一位女子从门缝里问他话,“何人叩门”之类。崔护回答是寻春独行,酒后口渴,想要讨点水喝。女子就开了门,递给他一碗水。崔护喝水的时候,女子倚靠在小桃树上,含情脉脉地看着眼前的陌生男子。崔护喝过水,起身告辞,女子送他到门口,跑回屋去时,似乎是挺难过的样子。第二年清明时节,崔护又到那里寻她,院子依旧,但是门窗紧锁,家中无人。崔护于是在门上题写了这一首诗。
有一种记载(例如《本事诗》),故事还要继续发展下去:几天之后,崔护偶然来到都城南郊,又去寻访时,听见门内有哭声。原来那女子自从去年一见崔护之后,便喜欢上了他,从此神情恍惚。几天前看见门扉上的诗歌,就生了病,绝食几天后,死了。崔护也感到很悲痛,于是要求入门哀哭。看到女子躺在床上,神色如生,他就抬起女子的头,放在自己大腿上,边哭边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啊!”过了一会儿,女子竟然睁开眼睛,复活了!女子父亲于是大喜,就将女子嫁给了崔护。
第二首是宋代诗人苏轼的词《蝶恋花》,词是这样写的: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不少研究者说这一首词是思乡之作,我认为这说法有深文周纳之嫌,不太可信。我认为,这是苏轼一次未遂艳遇的实录。艳遇发生在某一年(哪一年已经不可考,有人说是苏轼谪居惠州期间)的晚春或者初夏——“枝上柳绵吹又少”一句可以证明,当时风流倜傥的东坡先生大概是独自走路。路过一户人家时,在围墙外边只可以看到院子里秋千架上方的绳子,然后就是听见银铃一般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女子的串串笑声。美妙悦耳的笑声,不由人不顿时作如是遐想:那必定是一位妙龄的美女!是真名士自风流,东坡先生当时就理所当然地想入非非起来。因此,当时就吟成了这一首风格清新的小词。
有一个记载,说在惠州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苏轼先生想让爱人朝云唱这一首词,但是被朝云拒绝了。理由是,词中的“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两句,朝云情不能堪。这个记载如果属实,当然可以理解为朝云感伤春天已逝,感伤离家万里。但是,我们也不妨猜测这里边有吃醋的成分,吃东坡先生时时动心、处处留情的名士性情的醋。
两个艳遇故事,前者是两情相悦乃至结为夫妇,后者是一厢情愿短暂的想入非非,蜻蜓点水式的爱情折磨。看起来,似乎是后者不如前者实惠。但是,按照“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妻不如妾……不如偷不着”两种理论,我以为,后者其实是更加美好的艳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