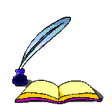相遇之初,黛玉把宝钗认作了情敌。而宝钗呢?
1 宝钗的心理
对于元妃那别具意味的赏赐,宝钗的感觉,却是“没意思”。居然还想着:“幸亏宝玉被一个林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只记挂着林黛玉,并不理论这事”(见第28回)。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宝钗对外的说辞,而是作者对其心理的客观描述。这不像是一个情敌的心理。否则,看到自己的意中人和另一个人好,可能会感到伤心和失落,而不会是庆幸。显然,对“金玉”之说,她感到尴尬和无趣:现放着两个人那么好,倒说我和他是一对儿!
尤三说:“只要我拣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凭你们拣择,虽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里进不去,也白过了一世。”对此,贾琏猜道:“别人他如何进得去,一定是宝玉。”二姐与尤老“亦以为然”。然而,尤三姐却啐了一口,道:【庚辰双行夹批:奇,不知何为。】“我们有姊妹十个,也嫁你弟兄十个不成?【庚辰双行夹批:有理之极!】难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没了好男子了不成!”【庚辰双行夹批:一骂反有理。】(见第65回)
那龄官虽是黛玉一流的人物,却也是情有独钟,对宝玉竟有“弃厌”之意(那贾蔷亦是“一心都在龄官身上”,连宝玉走了也不顾送);而在黛玉眼中,除了宝玉外,恐怕都是“臭男人”了;那尤三“能辨宝玉能识湘莲,活是红拂文君一流人物”(第66回末脂批),却只对湘莲一人痴情。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把宝玉当凤凰似的捧着。宝玉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错觉。好在龄官让他清醒了。
倘若宝钗真是贪图富贵、欲教夫婿觅封侯,那么宝玉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或是嫁个读书上进的,或是干脆拣现成嫁个高官,岂不好些?而要让宝玉“上路”,还须得一番“改造”才成。以她的眼力,岂不知这宝玉最是愚顽不化的(如贾母所言,是个不听妻妾劝的),又何必费这个劲儿呢?若论模样家世,不错的亦不少,又何止宝玉一个?若说她为了(宝玉)这个目标费尽心机、孜孜以求,也未免太小看她了。
如警幻所评,那宝玉“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也就是说,他虽在闺阁中获得了良好的评价,然于世道中却是不合时宜的,终致“百口嘲谤,万目睚眦”。嫁与这样的丈夫,果真是件幸运的事儿么?
宝玉的艺术气质,他的“无能”与“不肖”,让人想起梵高这样的人物。那梵高是绘画天才,然而一生中只卖出过一幅画,过着穷愁潦倒的生活,还要靠弟弟接济;而曹雪芹亦是文学天才,却过着“举家食粥”的生活。在我看来,宝玉亦属此类。虽为闺阁良友,在世人眼中,却未必是理想的夫婿。倘若宝钗果真是个世俗势利之人,反倒要躲开他了。
宝钗想:“宝玉和林黛玉是从小儿一处长大,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喜怒无常;【庚辰侧批:道尽二玉连日事。】况且林黛玉素习猜忌,好弄小性儿的。此刻自己也跟了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甲戌侧批:道尽黛玉每每小性,全不在宝钗身上。】罢了,倒是回来的妙。想毕抽身回来。”(见第27回)
不仅对宝钗,黛玉还对湘云也有过戒心:“原来林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里,宝玉又赶来,一定说麒麟的原故。因此心下忖度着,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鸳鸯,或有凤凰,或玉环金珮,或鲛帕鸾绦,皆由小物而遂终身。今忽见宝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因而悄悄走来,见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见第32回)
宝钗平素小心谨慎,注意避嫌。饶是如此,仍被黛玉猜疑。于是,终于忍无可忍,借扇双敲:“你要仔细!我和你顽过,你再疑我。”(见第30回)宝钗的这种特点,倒和“软猬甲”有些相似:她通常不会去主动攻击别人;但若遭遇攻击,却会让对方吃不了兜着走。
宝玉挨打,宝钗去看望。询问缘由,袭人便说出了薛蟠。待薛蟠回来,宝钗便来“劝哥哥”。不想把薛蟠说急了,“见宝钗说的句句有理,难以驳正,比母亲的话反难回答,因此便要设法拿话堵回他去,就无人敢拦自己的话了;也因正在气头儿上,未曾想话之轻重”,便说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闹,我早知道你的心了。从先妈和我说,你这金要拣有玉的才可正配,你留了心,见宝玉有那劳什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见第34回)宝钗的劝诫之言,被哥哥说成是出于私心偏袒宝玉。为此,感到“满心委屈气忿”,“到房里整哭了一夜”。
由薛蟠之言,亦可看出:对薛家而言,是先有金玉之说,后知宝玉有玉。
2 金玉之说
因着“金玉”之说,曾惹得二玉几次大闹;而在宝钗这里,竟也惹出一夜的眼泪来。前者是因黛玉“素习猜忌,好弄小性儿”;而后者呢,则因薛蟠冒撞,只想着把妹妹堵回去而不顾轻重地乱说。此三人,皆是与此说密切相关的,倒也罢了。而荣府中的其它人呢?
直到第66回,那兴儿演说荣国府时,仍道:“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则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过三二年,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了。”可见当时贾府内的舆论了。他们要么是不知有“金玉”之说,要么是没把它当回事儿。
那黛玉呢,还要“再过三二年”,“是再无不准的了”;而袭人呢,亦是“如今且浑着,等再过二三年再说”。可见,在贾府众人的眼中,黛妻袭妾不过是早晚的事。就连宝玉,也是笃信自己是要和这两人“同死同归”的。
想当初,那癞头和尚要黛玉出家,林家人不也没有当回事么,认为不过是“疯疯癫癫”,“不经之谈”,故而“也没人理他”。那癞头和尚要度英莲出家,士隐听了“知是疯话,也不去睬他”。试想,若是当真信了,也就没有后面的悲惨命运了。对薛家人而言,亦是如此。她们并不知那和尚是个神仙、可以预知未来的。虽然也依言将那八字錾在金器上,却不也过是当个“吉利话儿”罢了(只可惜,这话却未必真的“吉利”呢!曲名“终身误”,便道出了这一点)。
在“薄命司”中,正册之冠(薛林)和副册之冠(英莲/香菱),早年都遇见了癞头和尚。只不过,对黛玉和香菱,皆是(在其三岁时)要度她出家;而宝钗呢,则指出了她的姻缘所在。癞头和尚给了香菱八个字:“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也给了宝钗八个字:“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据说,那“金锁”便是长命锁(亦称“寄名锁”),多在小儿周岁时挂上(那宝玉身上也有一个);也有在百日时挂上的,那就更早了。诸如“芳龄永继”的话,錾在长命锁上,倒也合适。宝钗约大宝玉两岁。那么,在她挂“金锁”时,那宝玉还没有出世呢!黛玉比宝玉小一岁。若是她挂了这么一把金锁,倒有些伪造之嫌了。
如此说来,那癞头和尚是最先拜访薛家的(在宝钗出生后不久)。到了宝钗周岁,挂了金锁。再过一年多,宝玉携带灵玉出世。然后,癞头和尚便依次拜访了甄家(在香菱三岁时)和林家(在黛玉三岁时)。
那和尚携顽石下凡前,大展幻术将其变成了美玉,笑道:“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看来,通灵宝玉上的那八个字:“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也是癞头和尚给的。所谓的“金玉良缘”,不过是预先设定的命运而已,犹如童话故事中仙女的预言。
再说薛姨妈。“因薛姨妈看见邢岫烟生得端雅稳重,且家道贫寒,是个钗荆裙布的女儿,便欲说与薛蟠为妻。因薛蟠素习行止浮奢,又恐糟塌人家的女儿。正在踌躇之际,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对天生地设的夫妻,因谋之于凤姐儿。”“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错,且现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贾母硬作保山,将计就计便应了。”(见第57回)薛姨妈和邢夫人的心理,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薛姨妈看中的是岫烟的人品,并不嫌其“家道贫寒”,而是认为她和薛蝌两个很般配:“恰是一对天生地设的夫妻”;而邢夫人呢,则更看重薛蝌的“根基”,乃是一种俗常的心理。
那薛姨妈对薛蟠固然溺爱,却也知他配不上岫烟。这种看法,是基于人品、而非家世的。在这一点上,她和贾母的观点颇似:均是不重“根基富贵”、只看本人的。若说她看上宝玉的根基,为此居然伪造出“金玉”之说来,恐怕是把她当成邢夫人之流了。
3 金兰之契
那黛玉素有“疑癖”,好弄“小性儿”。然而,经宝玉“诉肺腑”(见第32回)、宝钗“解疑癖”(见第42回)。到了第45回,二姝已结成“金兰契”,“更比他人好十倍”。
宝玉对此深感不解,便找黛玉来问个明白:“那《闹简》上有一句说得最好,‘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这句最妙。‘孟光接了梁鸿案’这五个字,不过是现成的典,难为他这‘是几时’三个虚字问的有趣。是几时接了?你说说我听听。”“先时你只疑我,如今你也没的说,我反落了单。”黛玉笑道:“谁知他竟真是个好人,我素日只当他藏奸。”“因把说错了酒令起,连送燕窝病中所谈之事,细细告诉了宝玉”。至此,宝玉方知此中情由,笑道:“我说呢,正纳闷‘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原来是从‘小孩儿口没遮拦’就接了案了。”(见第49回)
在“互剖金兰语”后,薛林二人的关系进展迅速。“薛姨妈素习也最怜爱他的,今既巧遇这事,便挪至潇湘馆来和黛玉同房,一应药饵饮食十分经心。黛玉感戴不尽,以后便亦如宝钗之呼,连宝钗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宝琴前直以妹妹呼之,俨似同胞共出,较诸人更似亲切。贾母见如此,也十分喜悦放心。”(见第58回)黛玉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说与姐姐,不用过来问候妈了,也不敢劳他来瞧我,梳了头同妈都往你那里去,连饭也端了那里去吃,大家热闹些。”(见第59回)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状况是发生在“慈姨妈爱语慰痴颦”(第57回)之后。可见,宝钗当日那“认不得娘”的话,不过是玩笑而已。
在“金兰契”一节中,宝钗戏黛玉:“将来也不过多费得一副嫁妆罢了,如今也愁不到这里。”(见第45回)脂批道:“宝钗此一戏直抵通部黛玉之戏宝钗矣,又恳切、又真情、又平和、又雅致、又不穿凿、又不牵强,黛玉因识得宝钗后方吐真情,宝钗亦识得黛玉后方肯戏也,此是大关节大章法,非细心看不出。二人此时好看之极,真是儿女小窗中喁喁也。”那么,第57回中的宝钗戏黛玉,大约亦同此意了。
到了第62回,薛林二人“分茶”的举动,更令读者们大跌眼镜:“宝玉正欲走时,只见袭人走来,手内捧着一个小连环洋漆茶盘,里面可式放着两钟新茶,因问:‘他往那去了?我见你两个半日没吃茶,巴巴的倒了两钟来,他又走了。’宝玉道:‘那不是他,你给他送去。’说着自拿了一钟。袭人便送了那钟去,偏和宝钗在一处,只得一钟茶,便说:‘那位渴了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宝钗笑道:‘我却不渴,只要一口漱一漱就够了。’说着先拿起来喝了一口,剩下半杯递在黛玉手内。袭人笑说:‘我再倒去。’黛玉笑道:‘你知道我这病,大夫不许我多吃茶,这半钟尽够了,难为你想的到。’说毕,饮干,将杯放下。”
宝钗的随意,令人惊诧;而黛玉的随和,则更是出人意料。此二人的行事,一反常态,令人纳罕。我们看惯了“梁鸿接案”,猛然间上演了这么一出“孟光接案”,一时间还真是适应不过来。
在我看来,宝钗此举,似有“争席”之意。《庄子·寓言》:“其往也,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晋郭象注曰:“去其夸矜故也。”唐成玄英疏曰:“除其容饰,遣其矜夸,混迹同尘,和光顺俗,於是舍息之人与争席而坐矣。”此时的二姝,已是毫无嫌隙,不拘礼节了。自此,宝钗对黛玉少了客套,黛玉亦不把自己当外人。其亲密之处,竟可稍胜二玉。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见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结契后的薛林,似乎也是“异于常交”的:由“分茶”,容易让人联想到“分桃”之典。山涛之妻亦曾有过这种疑惑,为此还亲自调查了一番。在我看来,黛玉的痴情,是现于外的;而宝钗的多情,则是隐于内的。敏锐的黛玉,发现了这一点,知道对方是自己一流的人。于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所谓“金兰契”,是一种内在的契合,又岂是“感激”二字可以了得?
以我的理解,黛玉以往的“小性儿”,其根源便在于“疑癖”。如宝玉所说,皆因“不放心”之故。到后来,“疑癖”既解,“小性儿”自然也就没有了;且凡事有宝钗提点,亦比前成熟、谨慎多了。至“分茶”一节,已经完全颠覆了那种目无下尘、刻薄小性的旧形象,竟似换了一个人。
在我看来,薛林一身并非不可能:林黛玉可看作其内在本质的一面,而薛宝钗则可看作其公开展示的一面。宝钗的作用,大致类似于心理学中的“人格面具”。出于自我保护,人们往往倾向于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而将真实的自我隐藏在面具后。老子说的“和光同尘”,便有随俗而处、从众求同之意。所谓“同尘”,不过是个壳子/面具,一种保护色而已。
不禁想起嵇康和阮籍(都在雨村的名单中)。嵇康为人,任性直道,世所难容。孙登评他:“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见《世说新语·栖逸》。“君性烈才隽,其能免乎?”(见《晋书·嵇康传》)而阮籍则不同。《晋书·阮籍传》评价他:“至慎”,“喜怒不形于色”,“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那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让人想起平素“罕言寡语”、“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薛宝钗。那阮籍虽放浪形骸,却因不议论朝政而得免嵇康那样的厄运。
“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能为青白眼”,是阮籍本性的一面;而“至慎”、“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终日不开一言”的特点,则是其另外的一面。看似截然相反的两面,却是集于一身。从某种意义上说,倒有些薛林合一的意思。
4 薛姨妈和“木石姻缘”
薛姨妈向宝钗道:“连邢女儿我还怕你哥哥糟踏了他,所以给你兄弟说了。别说这孩子,我也断不肯给他。前儿老太太因要把你妹妹说给宝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一门好亲。前儿我说定了邢女儿,老太太还取笑说:‘我原要说他的人,谁知他的人没到手,倒被他说了我们的一个去了。’虽是顽话,细想来倒有些意思。我想宝琴虽有了人家,我虽没人可给,难道一句话也不说。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的那样,若要外头说去,断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与他,岂不四角俱全?”紫鹃忙跑来笑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结果被薛姨妈取笑,红了脸去了。婆子们也道:“姨太太虽是顽话,却倒也不差呢。到闲了时和老太太一商议,姨太太竟做媒保成这门亲事是千妥万妥的。”薛姨妈道:“我一出这主意,老太太必喜欢的。”(见第57回)
可以看出,薛姨妈说黛玉和宝玉两个“四角俱全”的话,原是当“顽话”说的,不过是接着宝钗的那句戏言罢了。然而,经紫鹃这么一闹,婆子们也说:“虽是顽话,却倒也不差呢”,并建议她“到闲了时和老太太一商议,姨太太竟做媒保成这门亲事是千妥万妥的。”看来,婆子们比紫鹃明白:知道这事要找“老太太”,而不是“太太”。直到此时,薛姨妈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事,并给出了肯定的回应。
如果说,只有前面的几句“顽话”,那么薛姨妈不去说是正常的(这不过和前面凤姐、宝钗的戏语类似)。然而,最后的那句话却是认真的。若不去说,便是“假意”了。这一点很容易验证。别说黛玉灵慧无比,就算是常人,也是骗不了的。
在我看来,薛姨妈说自己“无人可给(宝玉)”,未必就是虚言:她虽有女儿,却并没有打算给宝玉。二玉自小青梅竹马,亲密无间,那是有目共睹的;而宝钗品貌俱佳,艳冠群芳,也不是非嫁宝玉不可。好好的,又何必拆散人家两个呢?这不近情理:别说她们是亲戚,就算不是,也没这个必要。
薛姨妈后来究竟对贾母说了没有呢?原文中没有写。在我看来,倒是有可能的。
对于宝玉的婚事,贾母初时似乎还没有太明确的想法。后来,看上了宝琴,却不想人家已是名花有主,只好作罢。到了第57回,紫鹃试玉,宝玉因急痛而发病。“黛玉不时遣雪雁来探消息,这边事务尽知,自己心中暗叹。幸喜众人都知宝玉原有些呆气,自幼是他二人亲密。如今紫鹃之戏语亦是常情,宝玉之病亦非罕事,因不疑到别事去。”显然,那时的贾母,也没有“疑到别事去”。她对黛玉,恐怕还只是对外孙女的疼爱而已。而到了66回,由兴儿之言,可知贾母那时已经属意黛玉了。这种态度,在贾府内已经公开、形成了舆论。倘若有人在贾母面前促成此事的话,那个人很可能就是“慈姨妈”。
宝钗送燕窝时,黛玉说:“东西事小,难得你多情如此”。显然,她是重情不重物的。对北静王的“鹡鸰香串珠”,她不屑一顾;而宝玉的几方旧帕,却让她感动不已。若无情意,再贵重的东西她也是看不上的;若是有情,最家常的物件也是珍重的。以黛玉的为人,是唯有真情/真心方能“征服”的。若是见着点东西、得着点照顾就感恩戴德、甚至连娘都叫上了,那不像是黛玉、倒像是秋纹了。
薛姨妈说:“我一出这主意,老太太必喜欢的。”她可能会寻个机会提示贾母:不必远寻,本地风光就已很好。那贾母心疼二玉,亲上做亲,自然是喜欢的。而王夫人呢?如前所说,结契后的黛玉,已经“改”了。如此,从前种种,便可解为年幼时的“淘气”而已(“品格端方”如宝钗者,不也曾是如此么)。这样的黛玉,王夫人就算是不甚中意,也不至(如晴雯般)难以接受吧。再者,经这么一闹,为心疼儿子起见,且又是老太太的意思,也不好反对的。于是,便默认了。故此,贾府上下才可能有那样的舆论。当然,黛玉的多病,那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连贾母都虑到了。且因二人还小等缘故,故而打算先等上两、三年再办婚事。
从原文看,贾母的确没有明确发过话。然而,黛玉对薛姨妈亲近异常、那兴儿敢说出“再无不准”的话来,应该不是无缘无故的。以我的理解,大约就是“不明说”的道理了。这和暂时不给袭人过明路是类似的。贾母对黛玉,倒有点像王夫人对袭人。
5 黛玉之劝
对宝玉妻妾的人选,贾母和王夫人都采取了“不明说”的态度:尽管早已有了人选,却迟迟不给他娶妻纳妾。其原因,便是贾母说的,深知他将来是个“不听妻妾劝”的。那贾母并不是一个俗气的人。以我的理解,所谓“劝”,未必就是功名利禄、光宗耀祖,无非是因他“性情乖僻”,恐他过于不合时宜、以致“见弃于世道”而已。
脂批也说:宝玉恶劝,是其“三大病”之一。
“湘云笑道:‘主雅客来勤,自然你有些警他的好处,他才只要会你。’宝玉道:‘罢,罢,我也不敢称雅,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并不愿同这些人往来。’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袭人道:‘云姑娘快别说这话。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的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见他走了,登时羞的脸通红,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提起这个话来,真真的宝姑娘叫人敬重,自己讪了一会子去了。我倒过不去,只当他恼了。谁知过后还是照旧一样,真真有涵养,心地宽大。谁知这一个反倒同他生分了。”(见第32回)
“那宝玉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今日得了这句话,越发得了意,不但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了,而且连家庭中晨昏定省亦发都随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园中游卧,不过每日一清早到贾母王夫人处走走就回来了,却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充役,竟也得十分闲消日月。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众人见他如此疯颠,也都不向他说这些正经话了。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见第36回)
可以看出,除了黛玉外,“众人”(而非只有宝钗)皆劝过他这些“正经话”。在宝玉面前谈讲“仕途经济”,犹如在王夫人面前打情骂俏一般,那可是犯忌讳的事。就连可敬如宝钗、可爱如湘云,也是一说就崩、立马翻脸,更别说是其他人了。那袭人也知道:“若直劝他,料不能改”的。
李嬷嬷说黛玉:“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倒劝劝他,只怕他还听些。”黛玉冷笑道:“我为什么助他?我也不犯着劝他。”(见第8回)她究竟是“助”、还是“劝”呢?
那黛玉还是劝过的。“只见两个眼睛肿的桃儿一般,满面泪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堵,更觉得利害”,“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词,只是不能说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说道:‘你从此可都改了罢!【蒙侧批:心血淋漓酿成此数字。】’”(见第34回)“黛玉道:‘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说话,一面咳嗽起来。”(见第78回)此为“明劝”。
在“玉生香”一节,“黛玉因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钮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道:‘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宝玉侧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才刚替他们淘漉胭脂膏子,蹭上了一点儿。’说着,便找手帕子要揩拭。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口内说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庚辰双行夹批:又是劝戒语。】干也罢了,【庚辰双行夹批:一转,细极!这方是颦卿,不比别人一味固执死劝。】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奇事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吹到舅舅耳朵里,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庚辰双行夹批:‘大家’二字何妙之至神之至细腻之至!乃父责其子,纵加以笞楚,何能使大家不干净哉?今偏大家不干净,则知贾母如何管孙责子怒于众,及自己心中多少抑郁。难堪难禁,代忧代痛,一齐托出。】”(见第19回)
可见,黛玉并非不劝,只是劝得比别人巧罢了。她和袭人一般,深谙宝玉的脾性。“直劝”不成,便只好用巧了。当然,黛玉的段数要高些。小耗道:“我虽年小体弱,却是法术无边,口齿伶俐,机谋深远。”脂批道:“凡三句暗为黛玉作评”。那小耗偷得巧(不“直偷”),而黛玉则是劝得巧(不“死劝”)。小耗的偷法,“使人看不出,听不见”(脂批云:“直偷者可防,此法不能防矣”);而黛玉的劝法,亦是不着痕迹,难以觉察。此为“暗劝”。
然而,“宝玉总未听见这些话”。可知她以前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并不全是歪派。一个“总”字,一个“全”字,便可概括素日的情形了。昨夜袭卿之言,全然抛在脑后;今日颦卿之劝,亦是当了耳旁之风。可见,就算是黛玉袭人的话,那宝玉也未必就一定能听得进去的。
“宝玉笑道:‘你今儿还记着呢!’袭人道:‘一百年还记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夜里说了,早起就忘了。’”脂批道:“这方是正文,直勾起‘花解语’一回文字。”试想,若是“还记着”,她们也就不必如此辛苦了。看似拈酸,实则忧心。不独黛玉,袭人亦然。
“宝玉见他娇嗔满面,情不可禁,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一跌两段,说道:‘我再不听你说,就同这个一样。’袭人忙的拾了簪子,说道:‘大清早起,这是何苦来!听不听什么要紧,也值得这种样子。’”想当初,黛玉被看成是“小性儿”、“行动爱恼”、“会辖制”宝玉的人;而袭人的言行,亦不免此等嫌疑。在我看来,她们倒不是为了“辖制”宝玉(要他听自己的话),而是怕他真的落了那玉簪的下场。
面对“宝钗辈”的规劝,那宝玉便直接撑开大伞,滴水不进(直劝者可防);而黛玉的“巧劝”(或明或暗),则可能在无意之中渗入(此法不能防)。若还不能奏效,也只好随他去了。如脂批所言:“知天命而存好生之心,尽已力以周旋其间,不计其功之成否,所谓心安而理尽,又何患乎?”(见第13回)
再说“停机德”。对“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笔者更倾向于互文式的理解:“咏絮才”并非黛玉独有(在“咏絮”一节中,最出彩的,却是宝钗),而“停机德”亦非宝钗专属。所谓“停机德”,不过是“劝学”之意。那贾政是一个“酷喜读书”的“老学士”。虽然起初也想让宝玉读书科举;而在“名利大灰”后,便不再勉强他了。“又要环兰二人举业之余,怎得亦同宝玉才好,所以每欲作诗,必将三人一齐唤来对作。【庚辰双行夹批:妙!世事皆不可无足餍,只有“读书”二字是万不可足餍的。父母之心可不甚哉!近之父母只怕儿子不能名利,岂不可叹乎?】”(见第78回)。此时的贾政,对宝玉竟有些欣赏之意了。脂批说:“宝玉读书非为功名”(而“禄蠹”呢,则是为名利而读书的)。在我看来,贾政亦是如此。他天性“诗酒放诞”,且“素性潇洒,不以俗事为要,每公暇之时,不过看书着棋而已”,并非名利场中的“禄蠹”之流。即使在子侄辈中“规以正路”,亦是出于儒家的正统,而非“怕儿子不能名利”。那黛玉出身于“书香之族”,也是个“酷喜读书”的。在她的“潇湘馆”里,“窗下案上设着笔砚”,“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倒像是“那位哥儿的书房”了(见第40回)。贾政也说:“这一处还罢了。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不枉虚生一世。”(见第17回)。 “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甲戌侧批:盖云‘学海文林’也。总是暗写黛玉。】乃是前科的探花。”所谓“学海文林”,亦和“读书”密切相关。那黛玉虽未劝过宝玉读书,其行为却胜过一切言语(可谓“不言之箴”)。贾政和黛玉,一书蠹,一诗魔。从这一点上看,那贾政未必就不喜欢林黛玉。
6 结 语
“凭父母本人都愿意了,或是年年在一处的,以为是定了的亲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红线拴的,再不能到一处。”(见第57回)木石姻缘,便是如此:本人愿意,长辈认同。他两个又是“年年在一处”,是贾府上下诸人“以为是定了的亲事”。然竟不能成,只能说是天意了。薛姨妈此语,原是接着黛玉那句“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的话,却不想一语成谶。
探春给黛玉取“潇湘妃子”的别号时说:“如今她住的是潇湘馆,她又爱哭,将来她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见第37回)。想来那林黛玉,大约便是因着“林姐夫”而死的罢。“木石”二人虽未正式成姻,却是“父母本人都愿意”的,亦可算是未婚夫妻了。那湘妃乃是舜帝之妻,其泪洒湘竹,是因着舜帝之死(而非不能成姻);而黛玉的“泪尽而逝”,大约是因着宝玉之厄了。无他,惜玉而已。
薛林二姝,乃是至交,而非情敌。虽然黛玉曾有此疑,但很快就释然了。然而,天意难违,黛玉最后泪尽夭亡。她不忍宝玉为自己“孤守一世”,于是将他托付给了宝钗。和尚所言,就这样应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