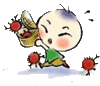旅美札记1
出乎意料的美国
初到美国的时候,经常被问及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最出乎你意料的是什么?
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通过网络、通过电视和电影,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风貌和居民们丰富多姿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美国这样的“首善之区”,其世界第一的硬实力与软实力,早就把它与众不同的各个侧面“灌输”给了我们这些以获取信息为生的媒体从业人员。即使之前从来没来过美国,在花几天时间把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Cambridge)新家周围的道路、公共交通、超市和饭馆搞清楚之后,我也没觉得这个小城市有比到处是工地的北京有多大的陌生感。
所以,我一般都会回答一些表层的观感:没想到美国街上的司机这么礼让啊(看见路边有人等候过马路,不管在不在路口、有没有红绿灯,路上行驶的大小车辆都会停下来示意你先走),没想到美国的中小学放学这么早啊(小学生有下午1:50和3:50两种放学时间,剑桥市唯一的高中更是下午2:50就放学了),没想到流浪汉这么多啊(剑桥市中心的哈佛大学Harvard Sqare,一个横竖长约200米的小广场,每天都散布着一二十号无家可归者),没想到美国人这么爱跑步啊(那些身穿紧身运动衣、塞着耳机沿着马路跑步锻炼的男女老少,在美语中有一个专门的词叫jogger,当然与此相映成趣的是,美国的大胖子也比比皆是),没想到这里的教堂居然也那么多啊(在我的概念中,美国是新教徒建立的国家,而新教的理论是信众可以直接在任何地方向神祷告和祈求,不需要借助教堂和神职人员,但无论是小小的剑桥市还是毗邻的大城市波士顿,每个街区怕都至少有一座教堂)……
在美国居住的时间越来越长,与哈佛的老师同学以及各色美国人交流日多,更主要的是带着疑问看书查资料,我大致理解了这些第一观感的缘之所起,随着而来的还有对美国人政治、经济和社会、精神生活中一些深层次观念的了解,我也发现了一个有着更多出乎我们外部观察者意料的美国。
比如,当前相当多的美国人对总统制的两党制感到失望,认为民主共和两党之间越来越难以达成建设性妥协,尤其是奥巴马第一个任期里保守派民粹主义的“茶党”重生,让共和党加速右转,原本我们概念中意识形态差异不大的美国两党政治,已经演变成意识形态两极化程度较高、政见分歧严重的分野,既是国家元首又掌握行政实权的总统,严重受制于议会中的两党对峙。这种失望情绪还表现在总统选举中,“胜者全得”的选举人团制度让少数摇摆州决定整个国家的政治格局,而占绝大多数的民众利益和诉求得不到呼应与关注,这种极端不合理现象却长期无法在国家政治层面上获得正视。
再比如,作为世界最大和最活跃的市场,美国国内除金融、信息通讯等少数行业外,其他行业的竞争能力乃至竞争氛围都相当疲软。以我的剑桥生活为例,满大街都卖一种矿泉水(雀巢的Poland Spring),麦当劳、汉堡王、肯德基这样的连锁快餐店几无觅踪,据说是当地的餐饮行业协会达成了拒绝连锁餐饮进入的市场保护主义“乡规民约”。初到此地居住,习惯了中国国内惨烈市场竞争和价格战的国人最盼望的恐怕就是淘宝、京东、苏宁入侵美国了。这种富足后的低烈度竞争固然可被视为某种有序,却由不得不让人想起今日遍地失业的欧洲——要知道,在接近0的超低利率保护下,美国的失业率虽然从2009年底的10%以上降至8%左右,但活力缺乏症不是靠印钞票医治的。
还有美国惊人的贫富差距以及其主要原因之一的教育差距。根据2013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2012年的基尼系数为0.474,不管这个数字是否有水分,但贫富差距巨大已成中国朝野共识。人们大多不知道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三个发达经济体的基尼系数与中国不相上下,一是香港(0.537),二是新加坡(0.482),还有一个就是美国,能找到的最新数字是2010年的0.46。走在大街上,喜欢慢跑锻炼的白人精英与喜欢可乐甜食的身躯庞大的拉美裔和黑人相映成趣;白人和亚裔大多将孩子送往郊区的私立学校,城市的公立学校里则挤满了拉美人和黑人……收入、教育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让以白人为主的中高收入阶层与拉美人、黑人形成了事实上的分区居住和生长鸿沟,而且这一社会分化随着白人老龄化与拉美移民大量涌入的同时发生而愈演愈烈,并滋生出高犯罪率的贫民窟这个美国社会“最黑暗的一面”。一些美国人的解决方案是严格控制移民,奥巴马总统则强调应该用教育和只是弥合鸿沟,但这谈何容易——美国的离婚率高达50%,而1/4多的孩子生长于单亲家庭,他们的父母多从事低薪工作,无力顾及孩子的教育。前黑人国务卿鲍威尔将军曾经忧虑地指出,很多出身贫寒的三年级孩子达不到三年级的阅读能力,“如果他们达不到,通向未来的就将是监狱之门”。
当然,呈现在我眼前的美国和美国人令人感佩之处远多于这些阴霾,只是我们总喜欢用理想遮盖现实,作为旁观者,我努力寻找这些光明与暗面并存的逻辑,并尽己所能,在今后的文字中向国内读者一一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