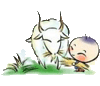周蕴仪
…………………………………
功夫在诗外
——2010-2011学年度秋季学期笔译课期末总结
彭雅琪
先说说我在上这学期的翻译课之前对翻译的认识吧。大二的时候去英语学院旁听法语课,法语老师叫陈玮,她当时正在准备翻译一本诗集。也许是她第一次带二外课,在心里往往把我们与研究生相混淆,时不时地想起一个事情来,就问我们“这个该怎么翻呢”?记得最清楚的是一道课后练习题,汉译法,原题大意是“尽管他们对旅游有着不同的态度,但他们还是相处愉快。”叫起来一位同学回答,这位同学照着参考书答案念了一遍。之后老师说,哪里用得着他这么麻烦,你就用一个malgre,后面接名词就完了!她还经常说,你们要接触最地道的汉语和最地道的英语,中间那些半成品看都不要看。不地道的东西,看到脑子里会起化学反应的。所以那种“改错题”坚决不要做。后来我看我们英语精读课本后面的汉译英联系,妈呀,那句子写得不是人话,一看就是根据英语回译过来的,以便我们可以不费脑子地再回译过去。她经常高兴了就讲一讲自己对翻译的体会,我觉得很有意思,同时用两种语言思维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呀。
同时用两种语言思维确实很刺激,但是对于两种语言都掌握得很不好的我来说,经常让人有崩溃的感觉,能听到无数词语在脑子里嗡嗡乱叫。我的第一个翻译作品是一首法语歌《星星之歌》,翻成了英语,向好朋友炫耀。为了使译文与音乐大体配套,我四句四句为一意群,每一意群在找到了感觉之后完全揉碎,用英语重捏,当时觉得很好玩啊。上个暑假放假之前,在书店信手买了一本书,叫《译道探微》,思果著,都是小短文,看看很有意思,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觉得很多译得不地道的东西,在今天已经广泛使用了。这是语言的自然变迁问题呢,还是我们对自己的语言不讲究了呢?(后来发现李长栓的《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就是这套书里的。)还记得那时去中文学院听一个古汉语讲座,一位研究汉语的老师说,现在的汉语来源乱七八糟,很多东西都弄不清是打哪儿来的,找不到一个一竿子插到底的研究方法,很是苦恼。我也觉得现在说汉语有时候都很不自信了,不知道自己说的是谁家的话。【汉语不像汉语,书写语言失范,实在让人忧心。】比如看翻译过来的理论书籍,一开始那叫一个痛苦,看着看着倒是习惯了,可汉语也变成那个调了,有一阵子写日记都是那个调,十分恐怖。暑假回家找了本地地道道的汉语小说,使劲看了一通。顺便说一句,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英语中的词词性大都很明显,是动词还是形容词很容易分辨,但是汉语就不是,要是翻译不注意,很可能搞得读者一句话里动词形容词副词分不清,要停下来掰扯半天。(倒是有一个例子,但那本书不在手头。)
这些都是前因。听了第一堂笔译课,我心中暗自庆幸,碰到了一个理论正确的老师。用点彩画派来比喻翻译,很恰当(以后可以学着看画,这学期在学着看现代舞)。通过这一学期的学习,我有两点明显的收获,一是要心存服务对象(读者),二是要从小事做起。这两点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是必不可少的,应当时时告诫自己。翻译的功夫远不只在语言层面上,翻译的功夫在诗外。
关于心存读者,记得最清楚的是Soo-NAH-mee。【按:他们做了一篇《大海啸》英译汉翻译,有一句是对Tsunami发音的解释。】对呀,这确实不用出现在译文里,由于英语的发音不规律,才需要给外来词注音,汉语里的每个字该读什么就读什么。我当时就是一点意识都没有。还有,在我随手翻看《非文学翻译》那本书的的时候,有一个例子给我很深的印象,是说中国的公交车站名怎么翻译,作者认为应该音译,但是怕外国人不懂拼音,又说应该在后面附一个汉语拼音的说明。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想过的。这些看起来是在管闲事,其实都是翻译分内的事情,要以读者能否准确理解为原则。(但有些翻译不是以读者理解为原则,而是以自己不要出错为原则。)我们在课堂里学习的文本,主要都是文学文本,加之阅历尚浅,这样就容易忘记“非文学翻译”的对象,忘记大千世界的参差多态,以为读者都跟自己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