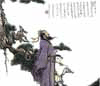在我国戏曲形成、生长之初被兼收并蓄进去的诸种艺术成分,如音乐、舞蹈、杂技、曲艺等,都随着戏曲艺术的发展成熟,在戏曲艺术的熔炉里,按照戏曲表现的需要,按照戏剧的结构原则溶化成戏曲艺术整体中的组成部分。但在长期的戏曲创作和演出中,还有一种大体独立于戏剧情节而存在的若干种艺术样式或者短剧的片断表演,也始终存在。我们姑且从宽泛的意义上把这种现象统称为“戏中戏”。
剧作中穿插“戏中戏”,是常见的现象,到了明末清初的传奇作品中,尤其是被称为苏州作家群的一些作家的作品中[1]出现频率尤高,从中可以发现他们对“戏中戏”这种编剧技法的运用水平,也可以一定程度地看到苏州作家群为戏曲艺术成熟所作的贡献。
戏曲穿插“戏中戏”这一现象既来自戏曲艺术形成的历史,不妨从现在可以看到的最初的戏曲剧本谈起。在元杂剧以及明初杂剧中,从形态上分约有四类:其一,从其母体宋杂剧、金院本中直接吸取的现成的片断。例如李文蔚的杂剧《破苻坚》第二折中有表现“谢安说棋”的大段宾白,即是《辍耕录》所载金院本名目中“打略拴搐”一项中的“著棋名”;李文蔚的另一个杂剧《圮桥进履》第一折中有“乔仙打虎”一段表演,即是院本名目中“拴搐艳段”项下的“打虎艳”;这折戏的开头,乔仙上场时所说的“清闲真道本”,也为金院本名目中“打略拴搐”一项中所有。此类来自金院本的穿插表演还有刘唐卿的《降桑椹》杂剧第二折中的“双斗医”,无名氏《飞刀对箭》杂剧第二折中的“针儿线”等;其二,穿插舞蹈表演。如史樟的《庄周梦》杂剧第一折后的楔子中,有在山里修行的道士跳朱顶鹤舞;其三,穿插杂技、魔术表演。如《庄周梦》杂剧第一折中,太白金星表演当场种花,倾刻结果的魔术六次,另外还有当场变脸、骑鹤上升等科范这些属于杂技的内容。其四,穿插短剧表演。如明初朱有燉的杂剧《吕洞宾花月神仙会》第二折中,有剧中戊演《献香添寿》院本。这和上面说到的院本片断表演的差异在于,它的表演手段不仅是说和做,还有唱段,可称作短剧。这些各色技艺的穿插表演,从效果上看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对于戏剧情节来说,大体上是游离的,从戏剧情境上看,也并不要求溶进特定的气氛中,例如,在《降桑棋》、《西厢记》中,在请医生为病人看病这件并不令人愉快的事情中,穿插了“双斗医”的滑稽表演;《飞刀对箭》中,在你死我活的两军阵前,有“针儿线”那样大段的轻松、诙谐的说白。与剧作中彼时彼地场景的气氛并不协调。这些穿插表演追求的效果只有一个,即轻松滑稽的逗乐。戏曲中的技艺穿插所体现出来的对于娱乐性的追求,实际上是戏曲艺术总体上的重要美学追求之一。戏曲的这种美学风格在它形成之时就溶进了它的肌体,是它生长和存在的环境所赋予的。
戏曲一开始出现,就和节日、婚嫁、酬宾、宴客等喜庆场合联系在一起。现今可见的最早的关于“杂剧”演出的记载就出于宋人所著的《东京梦华录》中的《中元节》目下,说的是中元节时的戏剧演出:“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演《目连救母》杂剧作为中元节的活动内容之一,在闹市中的构肆中连演七天,当时演出环境的热闹,以及杂剧演出为节日增添的色彩可想而知。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在宴客酬宾场合有戏曲演出活动形成一种习惯。明代万历以后,随着昆腔传奇的繁荣,家庭戏班十分兴旺,这种戏班多用于喜庆宴会。此外,赛社迎神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老百姓祭祀土地神的仪式,也是历史上戏曲活动的一种重要场合。社日演戏,敬神娱人,已成为习俗。早在宋代,陆游的诗中就有“太平处处是优场,社日儿童喜欲狂”;“黄北观神社,村东看戏场”;“空巷看竞渡,倒社观戏场”;“高城薄暮闻吹角,小市丰年有戏场”等关于社日演戏、万众欢腾的景象的描写。陈宏模《培远堂偶存稿》载:“秋成报赛敬神,还愿演戏,.原所不禁”[2]。其中还记载:“江南媚神信鬼,锢蔽甚深,每称神诞,灯彩演剧。……今日某神出游,明日某庙胜会,男女奔赴,数十百里之内,人人若狂”[3]。
因为戏曲在这样的环境中演出并生存,它在美学特征方面必然会打上和这样环境相适合的追求热闹、喜庆的烙印。而这一点必定会体现在戏曲的艺术构造上,而非仅仅表现在内容上。本文所讨论的各种技艺的穿插表演也即“戏中戏”就是戏曲在形式上体现崇尚娱乐性的美学追求的表现之一。
从观众的角度看,他们的看戏方式也即剧场形式,也是戏曲美学特点形成的重要决定因素。宋元时城市的戏曲演出场所勾栏、瓦舍都在闹市,观众可以就到集市办事之便看戏。元代杜仁杰的散曲《庄家不识勾栏》中,就描写了一个庄稼汉秋收后进城买货、同时到勾栏里看戏的经历。农村的戏曲演出场所多是寺庙舞台或者临时搭的戏台,这种演出场所属广场性质。庙会演戏时,观众可以随意活动。广场上买卖杂物、食品的,也都是观众。从陕西和山西两省现存的宋元庙宇建筑可知,这种演出形式宋元时就存在,一直延续到现在。城市中另一种演出场所是酒楼茶肆。在这种场合里,观戏者更是可以吃喝、聚会、看戏几件事同时进行。明代中期以后,社会上风行以演戏聚客作为交际手段,戏曲演出经常出现在官宦、文人的厅堂宴会中。陈维松《贺新郎·自嘲用苏昆生韵同杜于皇赋》词序云:“于皇曰:朋辈中惟仆与其年最拙。他不具论,一日,旅舍风雨中,与其年杯酒闲谈。余因及首席决不可坐,要点戏,是一苦事。余尝坐寿筵首席,见新戏有《寿春图》,名甚吉利,巫点之,不知其斩杀到底,终坐不安。其年云:亦尝坐寿筵首席,见新戏有《寿荣华》,以为吉利,巫点之,不知其哭泣到底,满座不乐。”[4]从这段叙述可见,当时,宴客演戏是经常的事,也可见在这样的宴会上,维持一种喜庆气氛是十分重要的。“酒以合欢,歌演以佐酒”[5]说明了戏曲演出的一项重要的功用。
这种观剧和演剧方式,同样是铸就戏曲追求娱乐性这一美学风格的因素,中国的古代的戏曲剧场从来没有追求“希腊剧场所具有的那种雕塑般的庄严效果,雄伟气概与崇高情调”[6],中国古代的戏曲观众,当他们走进勾栏瓦舍,面对广场高台,坐在酒楼茶肆,置身于府邸厅堂观看戏曲演出时,他们并没有象西欧古代的戏剧观众那样的习惯和欲求—在剧场体验一种庄严肃穆的仪式性氛围,调动一种集体性的、高度集中、昂扬的情绪,通过情感的渲泄达到心灵的净化。中国古代的观众在走进剧场时,主要的心理需求是快乐和放松,他们在看戏同时饮酒喝茶,就表示着一种闲适的心情,因此,他们到剧场主要寻求的是松驰和欢乐的气氛,并且希望通过欣赏舞台上的结局比现实中美满得多的故事使内心得到满足。
与戏曲独特的美学追求相对应的,是戏曲艺术独有的对社会人生的表现方式,也是独特的与观众交流的方式—表现手段高度技艺化。总体上说,古典戏曲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对诸种艺术种类的技艺一直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吸收、消化和改造的。但表现手段具有技艺性这一特点,始终未变。明末清初张岱所看到的《目莲戏》中,还有“度索舞维、翻桌翻梯、筋斗蜻蜓、蹬坛蹬臼、跳索跳圈、窜火窜剑之类”[7]。明显来源于杂技的技艺。直到当今的戏曲舞台上,打出手、翻台子、喷火、变脸等技艺还常常使用。有时甚至还添入动物表演的内容,如所谓真牛真马上台等。就总体上说,这些带有杂技艺术痕迹的技艺已经被戏曲化解成自己的一部分,得到观众的认可。
戏曲艺术对娱乐性的追求以及保持表现手段的技艺性,是戏曲中始终包含“戏中戏”的美学原则方面的依据和物质形式上的条件。
苏州作家群剧作中的“戏中戏”则已有发展,已经显示出了这一现象作为一种编剧技法的价值和作用,但同时仍然发挥着增强剧作可看性的功用。
苏州作家群剧作中“戏中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溶进了剧作的情节和情境。也可以说,有的“戏中戏”还不仅是溶进了剧作的情节和情境,而是在剧中人物关系的勾连、人物性格的凸现、戏剧情节的推进、戏剧气氛的渲染诸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剧作者们在剧中引入“戏中戏”的作用,已经不仅仅作为剧情间歇和调剂气氛,使人发笑的因素,而起到了促进、协调、展现全剧各方面内容的作用。例如李玉的《清忠谱》第二折中,正面展示了一个书场中的一场说书,剧本中有洋洋洒洒的一千六百多字的说书内容的正面铺叙。这段说书,在某些方面是剧作内容伸发的基础:其一,通过它勾连了人物关系。整部戏里所描绘的轰轰烈烈的苏州市民暴动中的领袖:周文元、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五人是在书场上认识的,并且由于颜佩韦被说书的内容激怒,闹了书场,与周文元等人由厮打而成为至交。其二,突现了人物性格。通过颜佩韦对说书内容的反应,对所说英雄报国故事的反应,刻划出颜佩韦的思想面貌和性格特点。其三.意义上的铺垫。这段说书所说的内容是,值宋朝国难当头之际,韩世忠父子忠心为国、英勇抗敌而遭奸臣陷害。这个内容虽然和全剧情节没有直接联系,但与剧中正直官员周顺昌被迫害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其四,气氛上相呼应。说书中忠臣被害激起听众义愤与后面清官被害、群情激愤的浓烈的戏剧气氛相映照。
再如李玉的《太平钱》传奇是一部神话故事剧,其中有这样一段情节:韦固外出归来,得知妹妹嫁了八十多岁的张果老,愤怒之下,离家出外寻找。他感觉离家三个月,实际上世间已经过去二+多年。当回到家时,他发现父母亲人均不在,不知其故。在听了说书人说他家的故事后,他才知道事情的原委,也有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这段书讲了
李玉的《万里圆》中,描写黄向坚万里寻亲途中历尽种种艰辛,在大年除夕,投宿一个客店。同客店的三位客商串演了《节孝记》中的“出淖泥”一出戏。《节孝记》是宋元时人作的南戏剧本,全名《黄孝子千里寻母记》,叙述宋末黄觉经因战乱与母亲失散后,为寻母四处奔波二十八年,终于达到目的的故事。其中黄觉经的艰苦经历和执着精神与万里寻亲的黄向坚有相似之处。这场“戏中戏”显然在意义上与全剧相映衬,烘托,渲染了主人公的孝义精神。
总的说来,“戏中戏”作为戏曲的一种表现手段,到了苏州剧作家手中,其艺术表现方面作用是大大丰富了。这说明在戏曲成熟的过程中,化解、融合、利用各种艺术成份、艺术手段的能力的增强,也说明剧作者们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增强剧作的戏剧性和增强戏曲的表现力的意识的增强。
然而,苏州剧作家们剧中的“戏中戏”,无论它们如何按照戏曲的构造原则,从最初“寄生”于戏曲的异己部分,变为戏曲的一种有机部分,无论它们在增强剧作的戏剧性上,成为多么得力的手段,它们始终处于戏曲艺术追求娱乐性、可看性的审美原则的支配下。由于追求娱乐性这种动力的驱使,这些“戏中戏”在具有聚合情节和人物凝聚力的同时,始终又有着使剧情具有间歇性、使戏曲具有一种独有的节奏的疏散力。它们总是多少和剧情具有一定的距离。就是说,它们总是会和全剧形成一种对比,这种对比有表演形式上的,有气氛情调上的。于是,“戏中戏”在全剧中总是一种具有独特的观赏性的存在,给观众提供新鲜感。
例如张大复的《重重喜》传奇第十一折,是一场表现婚礼热闹场面的戏。其中有个名叫贾全造的人,负责承办整个婚礼。于是,他一人有许多技艺表演。从扫地、做饭到各种乐器的吹拉弹奏,手脚忙个不停。励本中有多处舞台动作提示说明他的表演内容。如:“净(扮贾全造)脱衣、束腰、扫地、摆桌、挂画,一手吹喇叭、一手打鼓”。“净接茶下.即捧酒菜上、外安席,净忙穿长衣吹喇叭、打鼓、众坐介、净吹请酒又吹打”,当新郎新娘拜花烛时,“净念一句,吹打一回,生旦拜堂,净请外上受介”。这场戏描写的是四川间中地区的一个婚礼,可以想见,此处演员表演的吹喇叭、打鼓,甚至束腰,扫地等等,从内容到形式都会吸收当时当地的民俗成份,而且这又是生活动作的技艺化。这些技艺穿插在戏曲中,无疑与其它艺术成份形成鲜明对比,很可能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这折戏的前面一折是写男主人公长孙贵在赴任途中行李诏书被抢,住到当地一个大户人家家中,后面一折戏的情节、是安禄山和哥舒翰的阵前交锋。在两场紧张打斗的戏中,穿插婚礼上的技艺表演,剧情便产生跌荡,也就是使剧情更多了一种节奏。
剧作家们常常有意识的增加“戏中戏.的喜剧效果,这样,“戏中戏”所含的娱乐的成份增加了,而与全剧情节的距离拉大了。《重重喜》中,贾全造在表演送往迎来、做饭端菜、吹拉弹唱几个回合后,当他又一次手忙脚乱地开始吹喇叭、打鼓时,新郎长孙贵笑了起来,说:“罢罢,不劳你了,你去罢。”贾全造便停止了表演。实际上,长孙贵先出了戏,又把另一位表演者拉出了戏,这使这段表演更富于喜剧效果,也使“戏中戏”并不完全溶合到剧情中去。
《万里圆》中,除夕夜相遇在荒村野店的几位客商选择表演《节孝记》,这个“戏中戏”里的主人公的经历与《万里圆》中的主人公黄向坚的经历相映照,强化了黄向坚寻父的艰难困苦和决心找到父母的坚定信念,尽管如此,这个“戏中戏”的穿插,仍然让人看到中国戏曲追求娱乐性的美学传统。几位客商表演《节孝记》时,按剧情规定轮到某人上场时,这位演出者忘了。于是,正在场上表演的人演不下去了,便大声呼叫:“鲍冲天,你来救俺者”,这人赶忙答:“阵,忘记了,我来哉,我来哉。”这样出戏再入戏,无疑是喜剧性的,会引来观众的笑声。这个“戏中戏”一方面是剧作情节、人物情感的强化因素,一方面是全剧悲凉气氛的调剂因素。这样处理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会增强演出的娱乐性,可看性。也就是说,苏州剧作家运用“戏中戏”增强剧作的戏剧性的同时,把握了戏曲的一种美学特点。
这样看来,古典戏曲中的“戏中戏”实际上不可能严密地、完全地编织进剧情中去,达到牵一发动全身的地步,像其它民族戏剧中出现的“戏中戏”那样。东方和西方其他民族的戏剧名著中也有运用“戏中戏”作为手段,推进戏剧情节发展的例子。印度古典名剧、薄婆普提的《罗摩后传》中有这样的情节:罗摩继承了王位后,因百姓怀疑其爱妻悉多不贞,便决定顺从民意,遗弃了悉多。十多年过去了,罗摩一直思念妻子。一次,蚁蛙仙人召集罗摩王室和全城人到恒河边看戏,由天国仙女演出了罗摩休妻的故事,戏中再现了悉多的贞洁与不幸。罗摩看戏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后来在女神的帮助下,夫妻团聚。这里的“戏中戏”演剧中人物的故事,它使剧情出现巨大转折,掀起人物情绪的高潮,导致结局出现,它与全剧情节连系之紧密是显而易见的。
英国托·基德的《西班牙悲剧》是一部复仇悲剧。剧的结尾,复仇的人物和被报复的人物都参加一出复仇悲剧的演出。在这出“戏中戏”中,复仇者假戏真做,手刃了他们的敌人。这出“戏中戏”最后解决了戏剧冲突,并把全剧推上了悲剧的高潮。可见,《西班牙悲剧》和上面所说的《罗摩后传》中的“戏中戏”都是解决戏剧矛盾、推动结局出现的决定性手段。
印度另一个古典名剧、迎梨陀婆的《优哩婆湿》中也有一段“戏中戏”,天国歌妓优哩婆湿爱上了人间的一位国王,陷入深深的思念中。一次,她在天宫演戏时,错把剧中人物的名字念成了国王的名字,被戏班师傅一怒之下罚下人间,而后敷衍了她与国王间一段动人的人神爱情故事。这里的“戏中戏,出现在全剧开始后不久,是全剧情节铺排的关键和基石出。
英国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组织演出“戏中戏”是因为他从亡父的鬼魂那里得知了叔父害父夺母的罪行。他要复仇,但又担心:鬼魂到底真是父亲,还是恶魔装的,想引诱他去干杀人的可怕勾当。于是,他叫)、演了一出与父亲被害情节相仿的戏,以便察看叔父的神色,在复仇前得到更切实的证据。通过“戏中戏”,他达到了目的并经过痛苦的犹豫后复了仇,这场“戏中戏”对哈姆雷特决定复仇起了关键作用,并由此为契机展示了复仇过程中哈姆雷特性格和心灵的巨大矛后和痛苦,是剧清展开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综上所述,其它国家和其它民族剧作中的“戏中戏”都对剧中主要人物的命运直接发生作用,要么是全剧铺排情节、展开冲突的重要契机,要么是解决冲突、引出结局的紧要手段,在全剧情节的链条上不可或缺。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把它们与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戏中戏”作比较的话,它们仅仅是在剧作方法的角度上,成为铺排情节、解决冲突的手段。中国戏曲中的“戏中戏”却呈现不同,即使是像上述苏州作家群剧作中的“戏中戏”,尽管与全剧情节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但仍然明显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特的艺术功能:调剂全局的气氛和节奏,强化演出的娱乐性和可看性。这种“戏中戏”的独特功能,是被戏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所规定了的,也是中国戏曲的美学精神所规定了的。
中国古典戏曲发展到苏州作家群时,已经接近了它的尾声。苏州作家群在“戏中戏”创作技法运用上所取得的成就,显示了中国古典戏曲文学创作的日趋成熟。这一成就的取得,一方面来自于对这一技法的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中国戏曲美学精神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不断地提高戏曲剧作的戏剧性,同进又保持着中国戏曲强调娱乐性、可看性的美学传统,这是戏曲保持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并且不断寻求发展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一点上,苏州作家群在“戏中戏”创作技法上所取得的成就,有着更为普遍、更为久远的意义。
与元明杂剧中穿插的金院本片断和其它
技艺比较,苏州作家群剧作中的“戏中戏”里,社会的、民俗的内容也丰富得多。也就是说,这些片断在为观众提供技巧的美感的同时,还表现出社会生活的、社会风情的美,显示出展示社会生活状态的功用和能力。在探讨过“戏中戏”在戏曲的艺术构架方面的价值与意义后,不妨同时来探讨一下“戏中戏”内容表现功能方面的特点。
苏州作家群笔下的“戏中戏”使读者(观众)看到了当时某些地方的某些民俗活动的场景。李玉的《永团圆》传奇中,描写了一场各村坊联合举办的“庆丰盛会”。剧中这样描绘这一盛会上群情沸腾的热闹景象:“足如云,争狂跳,语如雷,争狂叫”,到处“人海人山”,“笙歌缭绕,旌旗隐隐飘”。街中间,大家争相观看并为此“挤得个胸箱背嵌鞋都掉”的“戏中戏”是一支装扮成各种动物和戏剧人物的队伍。这些戏剧人物分别出自《昭君怨》、《千里送京娘》、《钟馗戏妹》、《白兔记》、《西厢记》、《牡丹亭》、《玉簪记》、《破窑记》等三十个戏剧故事。观看的人赞不绝口:“好盛会,好盛会”[8]。这无疑是当时社会现实中民俗活动的艺术表现,在全剧中,这显然是好看、热闹的一场戏。
马佶人的《荷花荡》传奇中,有关于
这类“戏中戏”中展现的民间风情和民俗活动给剧作带来了浓郁的文化气息。
前文我们说到过苏州作家群的作品中穿插说书这种艺术形式,这实际展示了当时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主要的娱乐活动。当时社会中,说书这种说唱艺术形式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听说书是当时人们的一个重要的娱乐项目。正因为如此,说书在当时除了娱乐作用外,还可以成为民间的主要传播手段。叶时章的《琥珀匙》中就有这样的情节:贾瞎子为了帮助桃佛奴找到父母,把桃佛奴编写的唱本《苦节传》拿到闹市中唱,以传播消息[10]说话艺术作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到苏州作家群生活的明末清初,说书艺术更是繁荣兴旺,出现了柳敬亭这样杰出的说书艺人。再往后,说书出现以地域性特点为标志的不同类别,如南京、苏州一带有扬州评话和苏州评话等等。《清忠谱》、《太平钱》中穿插的书场说书场而和听者趋之若鹜的情形绝非偶然,它和杂剧中保留过时的院本片断不同,它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写照。这些穿插的说书片断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还不仅于此,它还表现出说书艺术本身的生存状况,商业化性质以及有关人的生活状态。《清忠谱》中,李海泉《岳传》说得好,周文元便请他在李王庙前开设书场,周文元每天能收入一二千钱。李海泉以说书为生,自称“兴来舌战词坛上,赢得腰缠作酒钱”。李海泉在李王庙开讲前,有一帮商人出高价请他去寒山寺讲。剧本有众人当场付钱的舞台动作提示[11]。这些构成了一幅细致传神的世俗生活画。
苏州作家群时代,人们娱乐生活的另一主要内容即是看戏。《荷花荡》中有场戏写扬州一位富商蒋宝生请一位名妓和一班艺人在他家里演戏的情景。这场演出的目的是蒋宝生招待他的亲家赵孝廉。剧中的男主角李素因进京会试路过扬州,也赶到蒋家看戏。在所演的“戏中戏”《连环记》中李素还上场扮演了一个角色。像这类“戏中戏”的确表现了当时的富贵之家的闲情雅趣、生活情态,可以使人较为直观地、形象地了解当时文人士大夫们重视宴会演戏,娱己应酬,几乎无日不赴宴、无日不观剧的生活状况。
我国传统戏曲在形式上有一整套程式化的交流手段—身段、唱词、唱腔等等,内容上,它有模式化的人物形象,理想化的人物命运,这都形成通向现实感受的间隔,与观众切实的生活感受形成反差。但另一方面,戏曲艺术构造自身,又有着促使观众产生另一种亲切感,即对剧作家和演员创作的亲切感的机制,例如,传奇的可长可短、可合可分的结构方式,演员可以不时出戏,和观众进行直接交流的表现方式,这也正是“戏中戏”在戏曲中始终存在的结构方面的基础。苏州作家群剧作中的“戏中戏”.又增加了民俗色彩,实际上增添了当时观众所熟悉的、容易引起观众共鸣的现实文化内容,这些内容自然会唤起观众对剧情和人物的亲切感。这种亲切感的唤起,缘于观众对剧中情境的似曾相识,对剧中人物经历和处境的感同身受。这种以“戏中戏”为代表的(当然远不仅仅是“戏中戏”)具有现实性、日常性、普遍性的内容的存在,正是构成苏州作家的剧作:'本色”风格的因素之一。
本来,文学艺术的本质精神是既依赖又距离开现实,是产生于与现实的抗衡、与现实的反差、与现实的距离中,但同时,文学艺术又永远离不开或浓或淡的具体的生活的蕴含,摆脱不了对现实的依赖、与现实的一致和贴近。也就是说,它也难以离开接受者的亲切感这一审美的基础。“戏中戏”的存在,从一个方面说,增强了戏曲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这些贴近生活、平实自然的内容和戏曲艺术审美追求的主流—超越现实、崇尚理想的一面形成对比,或者说是交融在一起但并不改变其主流。
应该说,苏州作家群的剧作表现出来的具有较强的现实感以及“本色”的风格,远不止是“戏中戏”带来。不过,如果把“戏中戏”作为一个窗口,从中可以较为直观地感受到苏州作家群的一些剧作家为传奇艺术的成熟、为传奇从雅走向俗、从文人士大夫阶层走向民众,增强传奇艺术的生命力作出的努力。苏州作家群的一些剧作家比较热衷于描写“戏中戏”.其出发点也许正在于此。指李玉、朱素臣、朱佐朝和张大复等一批活跃在苏州地区的剧作家,习惯上称之为“苏州作家群”或“苏州派”作家。
注释:
[1]指李玉、朱素臣、朱佐朝和张大复等一批活跃在苏州地区的剧作家,习惯上称之为“苏州作家群”或“苏州派”作家。
[2]陈宏模《培远堂偶存稿》卷十九。
[3]《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四十五。
[4]陈维崧《迎陵词全集》卷二十七。
[5]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
[6][英]阿·尼柯尔《西欧戏剧理论》第二章第五节。
[7]张岱《陶庵梦忆·目莲戏》。
[8]《永团圆·会衅》。
[9]《荷花荡》第八出。
[10]叶时章《琥珀匙·关守》、《琥珀匙·传歌》。
[11]《清忠谱·书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