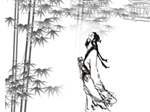本文转载自微信公号“财经十一人”
王宇|文
科学牵手经济?这句话如果让科学家看到,或许他们会冷笑一声,因为这俩遵循的完全不是一个逻辑。
对于实验科学家来说,只要不断地有科研经费进来,让自己可以用敏感度更高的仪器,不断地做实验就好;如果能赶在同行前面发一篇响当当的论文,那就快意无限了。相对来说,理论科学家们就比较好养活,给些纸笔就好,能有台超级计算机就更好;当然,如果做实验、或者造实验仪器的同行不给力,自己的理论就进入漫漫平台期了。
去年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希格斯粒子,人们称为上帝粒子,就是个典型例子。早在1964年,英国物理学家希格斯(Peter Higgs),以及由比利时物理学家恩格勒(Fran?ois Englert)和布绕特(Robert Brout)所组成的小组,就分别独立的提出了新的理论,用以解释为什么其他的粒子具有质量,而这一理论进一步预言了新粒子——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但是近50过去了,才由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以99.99994%的可信度,探测并确认它的存在。不算运行的支出,单单这项大科学工程的造价就高达80亿美元。
也只有在人类科学技术以及国际科研合作达到现在的水平,这样的项目和发现才能成为可能。否则希格斯只能继续锻炼,方有可能获奖,因为诺贝尔奖只颁发给在世的科学家。(据说,希格斯自做出这个理论,就每天坚持锻炼身体。想想也是醉了。)
当然,不能指望发现这种“上帝粒子”,人类就能瞬间喜大普奔。因为从理论走向实际应用,并进一步造福人类的生活,这是一项仅靠科学家无法完成的任务。例如,20世纪初量子理论的提出,更新了科学家在物理理论方面的知识体系,进而得以在此基础上实现的量子通信,或者量子计算机。虽然工程师们已经造出了量子计算机的实物,但它距离我们的生活仍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然而政治家们可等不及。毕竟当代的科学,已经不是像笛卡尔、麦克斯维尔那样的传统贵族们可以玩得起的了,它的背后是国家科研体系。因为理论的分叉很多,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梧桐树,每一个分叉上都有工程学突破。也就怪不得,政治家们急着把他们用于科研的财政预算变现,否则长期打理着这些梧桐树的枝枝叶叶,却不能经济收益,政治家们就不干了。
新近的科幻大片《星际穿越》倒是把这种困境,描绘得淋漓尽致。环境恶化造成粮食锐减,进而导致民意无法容忍宇航事业,甚至给科学探索打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但如果不是NASA的秘密计划,女主角也不会从她那个已经进入高维空间的父亲那里,得到更多的数据,从而给理论研究带来重大突破,最终解决人类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
现在的欧洲也是如此,制造业转移、人口老龄化、政府财政赤字高筑;更糟糕的是,似乎各种逆周期的经济干预手段都失了效。就连被誉为欧洲火车头的德国,也在上个季度露出停滞的态势。宏观经济数字的糟糕,很快就能通过工资和物价的齿轮,让居民体验到生活的艰辛;也能通过利率和汇率的齿轮,让投资和企业乏力;最终环环相扣的经济会越转越慢,失业率与通货紧缩步步紧逼,并赋予走上街头的人更多的政治权力。停摆,只是时间的问题。
因此,政治家们希望能动一动总产出公式里面的技术系数,让同样的人力、资金与土地,办出更大的事情来。所以,便提出一句口号,科学与经济的合作。从逻辑上来说,是科学带动技术进步,再带动产品创新,最终带来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国家科技投入产出的闭环。
然而,科学与经济就像是一对陷入虐恋的恋人,没有人知道他俩的路会怎么走。
比如说,松下电器的赤崎勇从1973年开始研究氮化镓半导体晶体的生长。16年后,才和他的学生天野浩在名古屋大学把它做出来,并实现微弱的蓝光。尽管如此,这与产业化应用之间,还相去甚远。又过了4年,日亚化学的中村修二才突破材料装备工艺的难题,研发出大量生产氮化镓晶体的技术。后来又传出美国人过来挑拨中村和日亚关系的传闻,中村也因专利权益问题,远走美国。再后来,东亚政府大力支持本国企业购买晶体生长设备,最终使得蓝光LED得以产业化。
正是基于这种技术,才出现了白光LED,以其廉价、节能、长寿命等特性进一步推动了照明,以及平板显示业的发展。使我们也有幸因此摆脱了白炽灯的所带来的种种不便,更享受到了高清电视,平板电脑等显示行业发展的红利。
有了产业,自然也有了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或是经济政策的研究。在这些理论之上,也论证了FDI的溢出效应、东亚经济奇迹的原因、以及拉丁美洲曾经的进口替代政策的失败。然而,这些理论谈得更多的是现有技术周期上的问题。
虽然经济学也算是一门研究市场不确定性的学科,但是对于从科学理论到技术研究,再到产业发展和市场分析,我们对于这个系统里非线性关系的探索才刚刚开始。如何让科研体系与经济体系之间,能够自行转动起来,不断产生创新的课题,这可不是养一支科技间谍队伍,再配上不差钱的产业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越是到如今,研发突破越是分散。它或是通过研究所的转制企业,或是创新型小公司,或是大公司的研发部门,逐步地把技术往能够被产业化生产的方向发展。然后小公司们在风投和私募的牵线搭桥下,或者被大公司收购,或者相互兼并重组,最终成为有资金实力和市场能力的高科技公司;而大公司的研发储备,也会根据市场的发展,逐渐发展为成熟的产品线。
分散是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形态,它能够最大程度地低降系统性风险。每一条单独的鱼,汇聚起来就会构成蔚为壮观的鱼群,并形成鱼群的逻辑。这正是受政府管制最少的互联网产业得以蓬勃发展的原因。
一套经典的产业模式,就是美国模式。政府出于国防安全,这项美国最大的政治议题,
从而对科研进行大量投入,与此同时,通过立法对专利转化、企业行为以及资本市场进行规约。之后,就是逐利的行为主体,在市场竞争下自求多福了。这便造就了美国没有产业政策的产业发展。(对于开放经济体来首,贸易与投资政策也会产生很大影响,这里先不做讨论。)
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像新生的美国,有着伴随着美国梦,所生长出来的愈挫愈勇的企业家精神;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敢于像美国政府那样,大尺度地放开自己的资本市场;即便是泡沫破灭,也是给泡沫里的每个人带来或技术或市场的经验。更何况,每个国家最大的政治议题不同,就使得从利益集团到政策制定的传导模式迥异。
而信奉社会市场经济的德国,就是另一种典型,他们更相信系统性解决方案。被誉为德国经济脊梁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往往盘踞在产业链的中上游,难得能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进入大众传媒的视角,便也不被众所周知。但是,如果终端产业乏力,比如汽车因为经济疲弱而卖不出去,他们就有大麻烦了。所以,德国人思考的是,如何能够让市场运行模式得到系统性的优化,从而让经济和科技能够形成闭环。
然而,不论是哪种模式,都离不开坚实的理论与基础技术研究体系,以及行之有效的专利制度,从而保障技术的市场转化。否则,自主研发也好、引进消化再吸收也好,最终都会成为绑架科技的产业政策,或是绑架产业的科技政策。
南洋理工大学物理与数学学院博士生王子龙对此文亦有贡献---
这是《财经》杂志公司产业报道团队建立的微信公号,聚焦商业,尤其科技、能源,道、技并重,推动阳光商业。查看公众号(caijingEleven)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