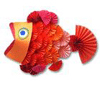|
一
2001年冬天,我第一次见到诗人西渡。他来中央民族大学做讲座,题为“时代的弃婴与缪斯的宠儿——论1960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从那时起我们结下师生缘分。拿起西渡的诗学论集《灵魂的未来》,我耳边就回响起他那天讲课的声音。这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听诗人谈诗。西渡的讲座,差不多成了我的第一堂诗歌启蒙课。后来七八年间,西渡每有新作诗文,我都是比较早的读者之一。作为一个有私密性的、成长中的晚辈读者,我不但从书中看到了我身上的阿多尼斯如何死去,更看到其中编织着的纯粹的、在尘世中追慕神性的劳作——一如里尔克倾心的travailleet travaille 1。
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本书所收文章风格、语境都十分多样。西渡大学毕业后长期在一家经济出版社上班,每日要处理大量繁琐的工作。这些文章都是他在有限的业余时间中完成的,其中有些是即兴写下,有的则一年半载才完笔;有诗歌史论、诗人专论、作品细读、对话等,内容涉及古今中外诗歌,显示了作者宽广的视野和纯正的趣味。不同于许多学者职业性的批评工作,西渡的批评写作纯粹发乎喜好。书中几十篇文章,无论篇什长短,观点如何,却一定是他心中涵咏许久,体悟最深的。每读完西渡的文章,尤其是那些鸿篇巨制,我常纳闷,西渡如何在繁忙的非文学工作中酝酿它们?疑惑中想起瓦莱里的话:“如果每个人不了解自己生活之外的生活,他就不能了解自己的生活”2。写作亦然?不能透彻地体悟不能写作的处境,就不能透彻地理解写作。西渡大概就是深谙不能写作的处境的写作者。
西渡的写作处境和姿态,让人想起曾担任保险公司副总裁的美国诗人斯蒂文斯,和曾为银行职员的诗人艾略特,他们的日常工作基本上与文学无关。而正是这种无关,让他们对诗的渴望更加纯粹——对现代诗人来说,诗歌是一种可能的生活,这大概也属于席勒早已感觉到的现代诗的“感伤”气质:古典诗歌本身就是自然,而现代诗寻求自然3。西渡在谈论现代诗人与古典诗人的区别时也曾说:“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诗人坚持对生活的权利,那么他的诗就不能不是对生活的梦想。普希金的诗是从生活本身生长出来的,为我们歌唱生活自身的魅力,而我们的诗却是从对实际生活的否定中长出来的。”4这呼应了史蒂文斯多年前关于现代诗的谶语:“这一天会来临,诗歌 加载中... 内容加载失败,点击此处重试 加载全文 一如天堂,看上去就像一个悲凉的装置。”5西渡的诗学文章一如他的诗歌,是他对日常生活的否定性劳作。这种劳作铸就的纯粹性,将有力地揭示诗意阐释容易错过的空白,抵达批评的严肃性。
说到西渡批评写作的纯粹性,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常坦陈批评写作的困难6。这是因为,诗歌写作面对的是语言的存在,是在孤立的语言体验中与语言一起新生的过程。诗歌面对的是象征之难。诗人瓦莱里曾经讲过一段发生在诗人马拉美与画家德加之间的逸事:德加一心想学写诗,屡屡请教马拉美。有一天,他扔下绘画,整天在家写十四行诗,直到脑袋生疼,但仍然没写出好诗句。他无耐地找马拉美诉苦:“我弄不懂,这首小诗,我怎么就写不成,其实我脑袋里装满了思想”。马拉美同情地安抚道:“不过,德加,写诗靠的是词,而不是思想啊”7。诗人的批评,却是要唤醒自己身上沉睡的德加,以“思想”来澄清诗歌的神秘性——这同样困难,也是一个诗人的散文写作面临的首要悖论。事实上,这也是文学写作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必然沟壑,要跨越这一沟壑,按照罗兰·巴特的话说,理性的逻辑与象征的逻辑必将扭成一团8。
在柏拉图《伊安篇》中,苏格拉底与诗人伊安有一场精彩的对话。苏格拉底想让伊安回答的问题之一是:一个创作者如何把自己的经验及经验之外的事物绘声绘色地“挪”到诗歌中?这就是诗的禀赋——要么是写作者所有的,要么是神助的。中国古人对此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描绘:“如有神助”。文学批评也有类似困境:如何描绘和解释文学中最动人的部分?按照布鲁克斯的说法,文学以各种悖论和隐喻说出最难言说的事物隐蔽性,“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冯至语),这种言说的光晕不断地应合和充实我们的灵魂。理想的文学批评,就是要发现文学作品中最为尖端的悖论和隐喻,发明一种与象征匹配的阐释性。亦即批评必须创造自己的悖论和隐喻技艺,以批评之姿再现文学的动人。而常见的批评,总是板结于抽象和理论的面具——歌德早就发现其灰色的面孔。正如劣质的文学作品让经验顽石般凝滞于语言的拥堵中一般,拙劣的批评也往往也让马拉美理想中源泉般涌动不止的艺术鲜活性,沦落为缺乏内心感的文学常识,按诗人钟鸣的话说,就是把脸做成面具9。成功的批评,正在于打碎凝固的常识所构成的文学意识形态,从中离析出高级的文学事理性,消除文学作品与其所处时代、与灵魂的隔阂,超时空、个体、文化、民族地呈现灵魂的杰出性。批评的这种理想,正与西渡强调的“诗歌作为理解的力量”10相同——杰出的批评接近诗的愿望,正与词接近物的渴念一样。
在《灵魂的未来》一书中,我们可以具体地看到,作者是如何出色地完成这些任务的。由于一个多世纪的多灾多难,中国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理性的新诗阅读传统,新诗中的“新”被恶性强调,而新诗中的“诗”则常常被忽略。汉语新诗的革命性及其特殊处境,使得它成为近百年来遭误解最多的文类。由此类误解累积而成一套关于新诗的文学意识形态,不断败坏普通读者的诗歌趣味。因此,当代新诗批评首要的任务之一,仍是为新诗正名。虽然完成这个任务在当代有更充分的底气,但新诗,尤其是近三十年代来当代诗歌的成就,与主流文学意识形态对新诗的评价之间依旧存在巨大落差。八十年代,诗歌因其特定的政治针对性而受到误解,当时公众对诗歌的狂热,带有鲜明意识形态倾向,因为大众关心的,更多是诗歌的意识形态针对性,而很少关注诗歌本身。随着诗歌所针对的对象的瓦解、重构和诗歌自身的变化,公众对诗歌也由追捧转为冷漠。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在一个发育的消费社会的氛围下,诗歌因缺乏实用性而常常遭受误解和诟病。与这种情况互为表里的,是批评面对诗歌的失语。然而,依旧有一部分优秀诗人和批评家,通过其言说廓明了新诗的丰富内容,阐扬新诗的精微和高妙。诗人西渡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十多年来,作为批评家的西渡基于自身的写作经验和对当代诗歌进程长期的观察思考,力图疏通新诗与旧诗、与外国诗之间沟通的渠道,在阐明古今中外诗歌之间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其内在一致性,以建立一种更为普遍的诗歌的基础。在梳理新诗传统、汉语诗意阐释和新诗批评话语建设等诸多方面,他都有许多独到的贡献。
二
如何理解新诗传统,不仅是现代文学史或新诗史需要处理的一个敏感课题,而且事关如何理解包括旧诗在内的整个汉语诗歌。在百年新诗写作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追寻新诗传统,乃至重新理解新旧诗之间的关系,必将有利于优化新诗写作和促进汉语诗歌精神的丰富。就此,西渡首先通过梳理和释读废名、林庚、孙大雨等诗人的诗观,多维度地考察了新诗人自我思考过程中的得失;又以现代以来几位诗人兼翻译家的翻译和创作之间的关系,就新诗的写作资源和可能性提出独到的理解。
西渡认为,废名是胡适以来最重要的诗歌理论家。他归纳出废名四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总结了到1930年代为止的新诗的成功实践,对诗歌和散文的性质进行了区分。某种程度上提出了新诗的诗歌本体论。第二,废名从理论上论证了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其他有规律的形式,只是这种自由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废名正当其时地指出,新诗应该用散文的写法。第三,在写作方法上,他提出写实、即兴和自由表现作为新诗根本的写作方法。第四,废名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对汉语新旧诗之间的区别和关系做出了新的有效论述。11
废名关于散文和诗的区别的谈论,是西渡解读废名,解释“新诗到底是什么”、“新诗不是旧诗,但新诗是诗”的出发点。西渡将废名的核心诗学观点归纳如下:“新诗不同于旧诗,但这个不同不在于是否用白话文写作,也不在于其形式是否符合格律,而在于诗歌的内容;新诗的内容是诗的,其诗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内容;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诗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形式。这是第一次从性质上对新诗和旧诗做了严格区分,可谓一举为新诗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废名的观点表面看来没有那么激进,却从根本上清除了旧诗借助其文学史优势对新诗构成的威胁,为新诗的发展拓出了广阔的空间。”12关于散文性与诗性的区别,废名曾以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为例论证:“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废名认为,这里“大约真是诗人之实感了”,然而苏词却不能够将这个完全的诗感坚持到底,它“一定还要写下别的被悲欢离合的事情才其为一首词”。从这里,废名见出旧诗的一个重要性质,即它的诗的特性是靠它的形式来维持的:“旧诗之所以成为诗,乃是因为旧诗的文字,若旧诗的内容则可以说不是诗的,是散文的。”13为了阐明废名的上述观点,西渡对废名提出的“诗的内容”、“完全”、“实感”、“即兴”、“自由”等诗学概念进行了解析——西渡遗憾地指出,由于废名论诗的随意性,这些废名诗学中的关键词被新诗研究者忽视了。通过解析上述关键词,西渡归纳出散文与诗的区别所在:“散文寄生于现实,从现实中获得存在的力量,诗歌则投身于可能性,倾心于尚未诞生的现实。”14因此,“诗的好坏及意义,是由诗歌内部的因素来决定的,而无须依赖其他外部标准。……诗歌是一个特殊的自足的世界,和自身以外的世界不发生直接关涉。对自身与现实关系的这一特殊态度,正是诗歌和散文握别的地方。”15
在西渡看来,废名对新旧诗中的散文性与诗性的关注,正是因为新诗恢复了诗与诗人的生命体验之间的直接关联,解除了旧诗中修辞势力对感性的压抑,强调对个性和心灵的戏剧语言表现。旧诗可以用来应酬唱和,可以用来歌颂“圣德”,而新诗重新面对现实,又不以现实为指归和依赖,成为“自己完全”的诗和意义的来源。因此,“旧诗的形式既是公共的,难免千人一面,内容更是彼此雷同,可谓万众一心。新诗的形式既是千姿百态,各呈其妍,内容也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形式问题,归结到最后却也涉及人的解放问题。”
沿着以上逻辑,西渡对汉语特性对写作的影响提出了反思。他认为,中国旧诗采取的意象的方法,是模仿和表现以外的第三种文艺方法。他从汉语和汉字与西方语言文字的不同特征论证这个问题:西方文字是一种抽象性的文字,字母本身没有意义,因此,在字、词、句、篇之间,组织和结构在语言的意义构成中起着关键作用。而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观念,包含着对世界的一种观照,它是一,但同时也是全体。所以,中国文字总要突破全体的限制,单独表现自己。基于这种特征形成的意象化写作方法,往往导致写实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缺失,所以在中国旧诗中,杜甫《北征》式纯粹写实性的诗不多见,李贺、李商隐式的纯粹想象性的诗也不多见。旧诗“意”与“象”之间形成的关系越到后来越固定下来,导致了对“象”,也就是对“经验”本身的忽视,从而使表意的方式渐趋模式化。“而新诗要求每一事象都带着经验的体温”16,“对于新诗来说,几乎不存在可以公约的意象”17。
西渡因此看到了废名对白话新诗的思考的根本意义:“废名言倡白话,实际是从语言上恢复诗歌和经验的联系;从意象写法恢复为写实的方法,则是从方法上恢复诗歌与经验的联系。”18西渡认为,废名不但纠正了胡适“作诗如作文”的新诗观念和新月派追求的新诗普适形式的妄想,更把新诗置入汉语诗歌史视野中,建设性地释清了新诗的内在合法性。新诗要从旧诗“诗的文字、散文的内容”变而为“散文的文字、诗的内容”,实际上是把诗歌的标准从以“修辞”为核心的古典诗学,转向以“表现”为核心的现代诗学。19旧诗中表现的传统何在?新诗如何与之续接?废名找到六朝文章,温、李作为新诗的前身。他认为其中既包含了“诗的理想”,也包含了“中国诗人所缺乏的诗人的理想”:诗人人格和诗歌伦理的独立性。而“新诗严格地成为诗人的诗”,如果你不是诗人,你也便休想做诗。西渡认为,废名以上论述对新诗的写作方法、新诗与旧诗传统的关系、诗人身份等一系列问题的回答,都对新诗批评的建设和重新理解新旧诗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西渡给废名前所未见的评价:“新诗在理论上的自我完成正是通过胡适、废名和袁可嘉这三个人实现的。而废名在这个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环。”20。
关于新诗的形式,西渡主要以林庚、孙大雨两位诗人对新诗格律的思考和实践为例,表明了自己的思考。在谈论废名时,他也曾有过一段集中的论述:“旧诗的音乐是通过一个程式获得的,是用语言去模拟音乐的效果,因为是外在的、人为的,也是公共的。新诗的音乐则是通过自然的音节来表现诗人内在的生命节律,它不依恃外在的韵脚和平仄的安排,而是依靠口语自然灵活的节奏来形成一种充分个性化的声音图式,这个声音图式是诗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诗人人格和个性的表现,因而绝不可能用一个公共的格式来范围和限制。”21与此对照的,是西渡对林庚的新诗格律观念的看法:“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写到许多写新诗的学生在上过旧诗的诗选课后纷纷改写旧诗。林先生由此感叹‘这文化遗产真有着不详的魅力’,‘像那希腊神话中所说的Sirens,把遇见她的人都要变成化石’;并举胡适提倡研究国故为例,‘说到故纸堆里只是为了打鬼,但是胡先生从此就没有回来。’不幸的是,林庚先生也并没有逃脱者‘不祥的魅力’的魔咒,被‘民族形式’这个暧昧的黑洞吸了进去。”22西渡不无遗憾地指出,林庚先生寻找汉语新诗民族形式的理想,反而阻碍了新诗的自由表现。相比林庚,西渡认为孙大雨对新诗音韵性的思考更具有灵活性,故在新诗历史上对格律理论建设贡献最大。他的“音组”理论,“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一种既符合诗歌普遍的格律原则,同时又适应现代汉语自身特性的格律设计方案”23,为新诗音乐性预留了足够的变化空间,孙大雨自己在诗歌创作和翻译中的形式努力,也超越了闻一多、朱湘、郭沫若等同代诗人的水平。可惜他忽视意义和声音的联系,忽视了语调和“音组”之间的配合,因此限制了这种设计在创作中的有效性。
通过对林庚和孙大雨诗歌格律思想的思考,西渡得出一个开放性结论:“格律诗的危险程度应该和自由诗陷入的形式涣散相等。所以,无论是自由诗和格律诗,都没有先在的成功保证。这又回到我们的一个信念:诗的成功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奇迹。”24对新诗格律问题,西渡有个值得重视的文学史观察:“新诗史上几次关于格律的讨论都正好处在诗歌创造力的衰退阶段——新月时期对诗歌规范形式的追求落在以《女神》为代表第一次新诗创造力高峰落潮以后,1930年代中期林庚提出格律设想虽然正处于现代派创作的高峰期,却没有得到现代主要诗人的响应,1950年代关于格律的讨论更处于诗歌创造力全面枯竭的阶段。”25按照西渡的逻辑,当代诗人对诗艺的卓有成效的多元探索,正是他们在诗歌形式上达成多样化和个性化默契的根本原因。
新诗内容和形式的自省和进步,都与外国诗歌的翻译成就密切相关。西渡《翻译、创作、民族性一文》对此有透彻的思考。他以冰心、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罗洛的创作和翻译成就来阐述自己对现代汉语新诗之“新”的看法。在谈论上述诗人的翻译成就时,西渡重点分析了上述诗人写作成就与翻译成就之间的不同呼应关系,西渡观察到一个充满谬误,却流布甚广的文学常识:一般认为,汉语翻译成就与译者的文言水平成正比。通过充分例证,西渡认为现代汉语翻译外语诗歌的能力,恰恰与现代汉语,更确切地说,是与新诗语言的成熟同步的,古汉语在许多时候会妨碍诗歌翻译的精确和细腻。比如,西渡敏锐地指出,戴望舒早期的翻译受到了旧诗语言的伤害,而后期翻译的成熟,则得益于新诗语言的成熟。通过对翻译与民族性关系的辨析,他对诗歌的民族性做出了精到的分析和定义:如果一定说文学有一个传统的话,那么一种伟大的文学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以背离传统的方式将传统发扬光大,以远行的方式实现新的回归。无论旧诗还是新诗中的优秀之作,都必然等待着另一首诗作为自己可能的未来,穿越不断变幻的意识形态的拦截,相互依恋,相互砥砺,以前所未有的语言之光,重新激发汉语之甜。因此,二十世纪外国诗歌进入汉语,不是取消,而是丰富了汉语诗歌的民族性,这正与新诗照亮旧诗中的别样诗意一样。
三
旧诗和外国诗是新诗的父母,正是通过艰难的背叛和远行,新诗才最终获得独立,创新和拓展了汉语的诗意空间,同时,旧诗和外国诗因新诗光芒的返照和激活,也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西渡从新诗出发,对汉语旧诗和汉译外国诗的思考和批评,正是这种生命力具体而微的体现。
西渡在《读旧诗札记》中表明了对整个旧诗传统的通盘看法。也许会有人以为,这是新诗人偏颇的性情之谈。但就笔者所知,这组文章是西渡潜心研读旧诗多年的结晶。尤其在近几年,他花费数年功夫,独自编辑八卷本“名家课堂”26,长时间集中阅读了大量的古典诗文和杰出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见证了这一劳作的友人张桃洲曾说,这套书完成的,不只是一个选本,而是一个庞大的诗学工程。事实上,新诗对旧诗的理解和通融早就开始了。比如,在现代诗人关于旧诗的阐释中,闻一多、废名、林庚、梁宗岱等都有过卓越的贡献,他们开辟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旧诗阐释传统。西渡对旧诗的理解,别具一格地发扬了这一杰出的诗歌批评传统。
关于从诗经时代到唐宋时期汉语诗歌的评价,对西渡来说远不只是一个鉴定其怎么伟大的问题,他想做的是通过自己精微的批评工作揭示其背后的秘密。作为一个新诗人,西渡主要从创作体验展开观察,他尤其强调经验性和虚构能力在其中的贡献,前者正是诗歌的生命感,后者则是诗歌所蕴涵的灵魂的自由。宋以后旧诗的渐趋衰落,实际上是一个逐渐丧失生命感和灵魂自由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旧诗日益沦为一套渐趋封闭、近亲繁殖的修辞体系。新诗取代旧诗的必然性正在于现代中国人需要表达新的生命感和灵魂。质言之,新诗是新诗人面对新的时代和经验处境,追求自身生命的诗意性的结果。作为当代诗人,西渡在六朝诗歌中找到了共鸣,他多次表达了对先唐诗歌,尤其是六朝诗歌的倾慕,因为那个时候诗歌的光荣与梦想,正与新诗一致。西渡多次说,今天正是新诗的六朝时代,因为对于汉语新诗来说,当代诗人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可能酝酿着一个伟大的未来。正如六朝诗歌中孕育着伟大的唐诗一样。在《〈西洲曲〉叹赏》这一绝好妙文中,西渡既表达了对六朝诗歌中的健康生命力和自由灵魂的缅怀,同时,也散发着一个当代诗人与一个古代佚名诗人的灵魂相遇时激起的超越新旧诗之不和谐的、浑圆的阐释之光:“南朝文采风流,声歌繁响,士人心灵自由,情调超逸,以及由之而来的深情高致,都在这一首诗里获得了不可摧毁的完美的形式——《西洲曲》用自身的不朽教育诗人为形式献身,因为世俗的繁华无非过眼烟云,形式的胜利才是最后的胜利——它是祭奠那个时代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它照亮了《诗经》,照亮了汉乐府,也照亮了它同时代的民歌。不单如此,它也照亮了整个南朝,照亮了中国的中古,并携带自身耀眼的光芒置身现代,置身我们之中。”27这种相遇,并不只发生在西渡这里。在描述当代诗人与古典诗人之间的关系时,西渡指出,由于他们这一代诗人大多很晚才接触中国古典文学,他们一方面通过勤奋获得了古典文学修养,另一方面,他们对待旧文学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距离感和反思能力,这让他们比前辈诗人从旧文学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在一种崭新的意识的烛照下,他们重新发明了古典文学的伟大传统:肖开愚、臧棣发明了一个新的杜甫,黑大春发明了他自己的陶渊明、李白和王维,陈东东发明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东方传统……”28当代新诗与旧诗传统之间的这种前所未有的、穿越文学意识形态的、纯粹的对接方式,正是新诗创造性和生命力的表现。
与无数伟大的古典诗歌一样,带着自身耀眼的光芒置身于现代,置身于我们中间的,还有无数伟大的外国诗人和诗作。一切时空、一切语言中的诗歌,组成了令人永远向往的、天堂箴言般的大写之“诗”。在西渡笔下的圣琼·佩斯、弗罗斯特、惠特曼、茨维塔耶娃正是组成这一永恒之诗的一部分,面对佩斯,西渡惊异于诗跨越词与物之间的鸿沟的那种永恒追求:“语言的魔术在佩斯这里抵达了它的极致。他的语言在滔滔雄辩和不尽的赞礼中,一不留心变成了他所礼赞和倾诉的对象本身。……佩斯重新唤起了文字所能具有的最崇高、最神秘的力量,亦即统一世界的力量。这些诗如矿藏般潜伏于世界之体中的力量的实现:诗人带来了今日的光之宇宙,并重新树立起了过去的、业已被深埋了的宇宙。”29面对弗罗斯特,西渡读出了现代诗人角色的变化:“弗罗斯特对现代诗歌的贡献之一是降低了对诗人身份和诗歌题材的要求。在弗罗斯特这里,诗人成了一个普通人,某种程度上结束了他作为先知和预言者的角色。”30面对惠特曼,西渡读出了惠特曼的文学民主意识,更读出现代诗歌“自由”的面孔中含有的精微灵活的音乐性:“以往那些貌视精致的格律模式为我们提供的,不过是对音乐的机械模拟,它只具有表面的音乐效果,实际上背离了诗歌音乐的本质——它和情感的内在联系。”无论是词对物的梦想,还是现代诗人的角色意识、文学民主性,也是新诗生长过程中要直接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面对茨维塔耶娃,西渡被她“不是任何人的同代人”的诗人人格写照感动:“诗人在公众生活中体验到的那种异质性,那种难容于团体、社会和时代的异质性,就像蚌壳中的珍珠。珍珠在蚌壳中孕育,它却不属于蚌壳;不但不属于蚌壳,而且它恰恰孕育于蚌壳的排异性。珍珠天然向往并属于某个闪亮的脖子,对于诗人来说,这闪亮的脖子就是永恒。”她那超越语言民族主义的诗人形象,为现代诗人树立了另一种典范。西渡还指出了诗人多多和海子在创作上与这位诗人中的“女性铁匠”之间的师承关系。这么多共鸣,恰恰证明中外现代诗人之间超脱语言、民族、性别的共同感,让不同时空中的灵魂结缘,这正是诗歌的伟大所在。
四
理清新诗的历史处境和美学处境,才可以说清新诗自身的诗意性。常见的新诗批评,宏论颇多,却多不得要领,缺乏细读作品的能力。这与新诗对自身处境一直认识模糊有关。在认清新诗处境的基础上,西渡对戴望舒、穆旦、江河、海子、戈麦、多多、张枣、王寅、臧棣等诗人的作品进行了细入肌理的释读,以情理混融的动人批评之姿,充分地演绎出众多新诗杰作在事理和情理上的精确、清晰、饱满和玄妙。这些细读式的批评表明,超越文学史逻辑地理解一首杰作,正是杰出批评能力之所在,也是新诗作为诗的孤绝的体现。正是少数傲压群芳的杰作,使文学史有了坚实而开放的依据。
在《爱的可能与不可能之歌》中,西渡对穆旦的名作《诗八首》进行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细读。这篇长文在与前辈批评家对话的基础上,将此诗字里行间充满悖论和暗示的多义性修辞元素细腻清晰地呈现在批评语言中,无论从整体还是细节上,都澄清了此前诸多论家盲视或回避了的谜团。西渡还指出此诗中的两个新诗中此前罕见的特征:在意义层面上,全诗充满了对主体统一性的质疑和分解;在声音层面上,这首诗的声音是一种内在的声音,一种无法依赖人类嗓音复制的声音。穆旦给新诗的声音和思想之间,寻得了一种少见的和谐,大大拓展了新诗表现的疆土,发明了汉语抓住事物惊异性的新技艺。西渡看到的上述两种特征,恰好近似后朦胧诗内敛而多样化的主体呈现方式。不同于朦胧诗中坚强统一的主体性,后朦胧诗在声音上多体现为语言的内在语调,而不借助于一种外在于诗歌的声音。二者加起来形成的自我的紧张感,正是我们这个多变的时代造成的个体的分裂性的杰出写照。西渡在解读张枣《镜中》、臧棣《新建议》时,都对不同诗人对主体内在紧张的杰出呈现方式进行了充分的阐释。
在解释《镜中》时,西渡读出了此诗通过发明一种陈旧感而呈现的新鲜主体性,正是当代诗歌的杰出性所在:“在与古典诗歌的对话中,何其芳是仰视的,有一种浪子回头的悔恨;而张枣的姿态是平等的,显示了一种创造的自信。从新诗诗艺的传承来看,张枣可以说是何其芳的合法继承人。不同的是,作为1980年代的诗人,张枣在心理上已经化解了何其芳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的对古典诗歌的迷信,因而开拓了更多的创造的空间。在何其芳那里,传统是一笔有待继承的遗产,诗人和传统的关系是单向的;而在张枣这里,传统是我们汇入其中的河流,诗人和传统的关系式双向的、互动的。”31在解读臧棣的《新建议》时,西渡指出了此诗包含的双重隐喻:“它既是关于人的存在的一个隐喻,又是关于诗歌本身的一个隐喻”32,事实上,这正是一种由灵魂存在和语言本身出发的诗歌气质,它表明,历经工具性伤害的新诗,终于具备了一种由自身出发的纯粹性,当代诗歌灵活而有效的形式特征正是这一诗歌气质的外化。正如西渡以此诗为例指出的,通过众多诗人的努力和尝试,当代新诗在建立新诗普遍形式上已经有成熟的方向:“现代汉语诗歌的音乐不一定以押韵和字句的绝对整齐为基础,而应该以一种流动的口语节奏为基础,辅之以形式(一定长度的字句、韵)的配合,最终形成一种半规范性或规范性的诗体”。西渡上述针对不同作品的阐释,从不同方面重现了当代诗人驾驭现代汉语的熟练能力,而当代诗歌的杰出,最终体现为它可以每一种诗绪找个独属于它自己的杰出形式,来承载灵魂的丰富和纯粹。
另外,值得细说的是西渡对海子的理解。作为受过海子诗歌哺育的诗人,西渡在关于海子的一组文章中对诗人海子及其诗歌有许多独特而体贴的看法,这组文章,是理解诗人海子的丰富性和悲剧性的重要角度。比如,西渡分析了海子《弥赛亚》中的老人形象的经验源头和多重象征意义;分析了海子的修辞暴力及其命运与红色暴力之间的关系。西渡还根据自己早年的海子作品手抄本,对流行的海子诗歌版本进行了勘误。这些工作,不但有利于读者重新理解诗歌和诗人,同时也在不被重视的新诗朴学方面树立了很好的学术典范。
五
在领略西渡各色批评作品中旁逸斜出的精妙、拆分语言的形而上学快感、还原支撑想象力的经验骨架的巧致之后,我们发现,这一切都关乎诗歌对灵魂的未来的关心:面对以往一切人类的伟大灵魂,作为文明的孩子的诗人,我们的心灵是否已做好准备?“当灵魂的电流通过我们传递向未来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否已经足够强大、足够坚定?它会不会骤然熔断,不是给后世带去温暖和光明,而是黑暗和恐惧?”33里尔克早就道出现代诗人的这一困境:“美,只是恐惧的开始”。当然,也正是它,催迫出现代诗人前所未有的理想——史蒂文斯说:“天堂与地狱的伟大诗篇都已经写下,而尘世的伟大诗篇仍有待写下。”34
新诗正是“尘世”的奇迹。在纪念戈麦的一次演讲上,西渡以戈麦为榜样描绘出一种现代诗人的“尘世”化典范:“他必须在不降低诗歌的敏感性的同时,具有更加成熟和健全的心智,以胜任一个现代人日理万机,错综复杂的日常生活。一个现代诗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一个圣徒。在一个宗教上的圣徒逐渐销声匿迹的时代,诗人要成为众人生活的楷模”。西渡认为,只有这种因地制宜的坚强,诗人才能担负起看护脆弱而高贵,永恒而稀薄的灵魂的责任。因为“放眼四周,我们看到人正在沦为数字的奴隶;甘心忍受阴险的银行家的奴役;信念像气球一样垂直飘离,不带任何压舱物;爱情遭放逐,友谊被背叛、被蔑视,孤单无助、流落街头;电视、电影、报刊、互联网争先向资本献媚……在我们的时代,李白的身影已经变得越来越缥缈,杜甫瘦损的身躯更加瘦损,歌德在图书馆忍饥挨饿,莎士比亚的舞台上空无一人……灵魂的处境正变得日益困难。”35
对灵魂的“尘世”处境和未来,西渡以歌德式的命名与史蒂文斯达成了默契:惊讶是现代生活中最稀有的经验,诗歌因而成了“制造惊讶的艺术”36。西渡的诗歌批评术,正是从另一端解开或创造这关乎灵魂未来的“惊讶”。面对灵魂的永恒困惑,磨砺和推动着他的阐释之犁,让它以一种清晰而炫目的锋利,划开汉语诗歌永恒的惊讶腹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