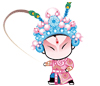X X在全真道发展历史上,全真七子名下各创有一派。其中,宗郝大通(1140~1212)的一支称为全真华山派。北京白云观收藏有道教《诸真宗派总簿》,李养正先生编著《新编北京白云观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时将其收录,其中有全真“华山派”的传法谱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找到史料证明郝大通驻世时,自己曾亲自开创以“华山派”命名的这么一个道派。那么,郝大通的后传法裔们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开宗立派;《诸真宗派总簿》所载全真“华山派”传法谱系形成于何时;郝大通后裔法徒为什么要将自己这一系命名为“华山”派,与历史上居华山的高道陈抟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一、郝大通后传法裔们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开宗立派的? 关于郝大通所授弟子情况,综合《道藏》之《甘水仙源录》、《云山集》,陈垣先生编《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王宗昱先生编《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有关史料,我们略叙其传承情况如下: 第一系: 郝大通——范圆曦——高道宣——徐居仁 第二系: 郝大通——王志谨——姬志真 徐志根——孙履道 第三系: 郝大通——李志实(开玄真人)——李志柔——石志坚(石廷玉)——董道弘 从有关历史资料来看,虽然那个时期,全真七子的弟子们在礼本师之外,有机会一般都还参礼其他宗师,如郝大通门下的范圆曦、王志谨、李志柔等皆曾礼丘长春祖师。但郝大通在当时弘道传教,已有自己一系的传承法脉。下面,我们以郝大通传王志谨、姬志真、徐志根、孙履道这一系承传情况为证: 《甘水仙源录》卷四收录有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王鹗撰《栖云真人王尊师道行碑》①,对郝大通高足王志谨(1177~1263)生平、入道及传教事业有一个说明。王志谨祖籍东明之温里,为逃婚而径往山东,得郝大通亲炙、口传心授,大蒙印可。金元禅代,王志谨又跟从丘处机北游燕、冀,徜徉 于盘山西涧之石龛,草衣木食,隐居修道,后至汴京重阳升遐之所修朝元宫,汴之朝元宫因此成为该系之祖庭。王志谨之后,其弟子姬志真(1192~1268)、李志居、徐志根(1213~1304)先后执掌本派教事。从王志谨《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以及他的弟子姬志真所著《云山集》来看,他们的全真心性论思想受丘处机的影响更为明显,故樊光春先生曾将王志谨、姬志真这一系视为丘处机所传②。但王志谨的另一弟子徐志根则明确以郝大通为法祖,以王志谨为师父,以姬志真、李志居为师兄,自觉归宗郝大通门下。陈垣先生《道家金石略》载元代学者程钜夫作《徐真人道行碑》③,对徐志根的传教事业有一概要说明。徐志根为弘教所做的重要一件事,就是远绍其法祖郝大通,请嘉议大夫、岭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徐琰撰《广宁全道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此《碑》以范圆曦、王志谨为郝大通门下两大弟子,其云:“师(指郝大通)逝之后,弟子行缘四出,能世其业者甚众。高弟范玄通与栖云王宗师,又其尤者。当中原板荡,国朝隆兴之初,一居东平,一往来乎燕汴,建琳宇,开玄坛,聚徒讲说,贵贱钦仰,宗风大振,道价增崇,不减太古。”④徐琰乃儒生,对全真道发展情况可能并不十分清楚,徐志根为此《碑》文提供资料,故此观点当出于徐志根。徐志根为什么选择归宗于郝大通门下?首要原因当然是王志谨从郝大通入全真之门,他们之间本有师徒授受之事实;其次则与当时释道纷争,全真道遭两次焚经之难、受到沉重打击有关。徐志根于元至元年间制授为王志谨一系掌教真人,他选择归于郝大通宗门之下,于其时更有利于保存本派之实力。王志谨所传姬志真、徐志根一系,在法脉承传上有其重要特点:其一,以汴之朝元宫作为本宗祖庭,朝元宫在当时有不少下院,祖庭对其所属下院,有权任命其主持人,决定其重大教务事宜。这可以从《玉清观碑》⑤所载陈志昂、耿道明道业相承之事反映出来。卫州西北的玉清观为清真大师陈志昂所建,是河南汴梁朝元宫之别院,陈志昂丁卯岁(1267)无疾而逝,由其法弟烟霞子楚志云继其事,不久楚志云引退,状请于朝元本宗掌教崇玄诚德洞阳真人徐志根,徐命志昂高弟耿道明来主是观。故朝元宫可以对其所属子孙庙施加重要影响,当属事实。如果结合朝元宫自行任命其下院主持一事,则至于徐志根掌教时,郝太古一系已经开始较为自觉地明宗立派。其二,汴之朝元宫有本宗掌教宗师的传承制度。此宗以栖云大师王志谨为首任掌教,其后为姬志真、李志居、徐志根,三人皆为王志谨门下弟子。徐志根之后,其徒孙履道继掌教门。他与当时的玄教大师吴全节友善,得吴全节举荐,曾作为全真掌教大宗师主持教事⑥。孙履道执掌全真教时间是元泰定元年(即1324),这可能是郝太古一系执掌全真教门的第一例。孙履道掌教至1368年明朝建立约有四十余年时间,因资料不足,这段时间郝大通一系传承法脉不是很明确。但因其门下自有师徒传承之惯例,故可以推知其传承当一直有所延续。如明代山西永乐的一些碑刻资料,就反映出明代郝大通一系的门弟传承情况。
因此,从金之中后期开始,至于元之前期与中期,郝大通的后传法裔们便已经自立宗派,并奉郝大通为宗祖,弘传全真教法了。但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还不见其以“华山派”自称者,亦未出现《诸真宗派总簿》所载“华山派”传法字派与谱系。
二、《诸真宗派总簿》所载全真“华山派”传法字派与谱系形成于何时?
考察《诸真宗派总簿》之《宗派源流目录》,郝大通所开创的全真一系称为郝祖华山派,位列第十三;在演变的
过程中,又出现郝祖分支华山派和宗丘、郝二祖的一系道派,分别位列第七十四与第七十二。在此之外,则另有位列第五十六位的陈抟老祖华山派和第八十四位南方所传来之华山派。
《宗派源流目录》所载第十三郝大通之华山派,其宗派系谱拜广宁祖师郝大通为开宗立派先师,其后,谱系承传之秩序为:“至(志)一无上道,崇教演全真;冲和德正本,仁义礼智信;嘉祥宗泰宇,万里复元亨;清静通玄化,体性悟诚明;养素守坚志,虚灵慧业生;希贤遵秘法,慎修保纯贞;敬谨规良善,默功毓秀英;勤能扶世运,积久大丹成;永建根基厚,仙瀛书盛名;圆满光华照,去天庆上升。”⑦
从郝大通所授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等的情况来看,《诸真宗派总簿》所载“华山派”承传谱系在金后期、元朝前期和中期尚未形成。我们通过郝大通传王志谨,王志谨传徐志根,徐志根传孙履道(公元1324年任全真掌教宗师,其盛年当在此时期),以及郝大通传范圆曦(1177~1249),范圆曦传高道宣(1201~1276),高道宣传徐居仁(盛年当在公元1292年前后),其法名皆不以《诸真宗派总簿》所列“华山派”承传谱系之字派命名,即可以证明此问题。
元末是否有此“华山派”承传谱系,目前尚无资料予以证明。那么,此传法谱系是否形成于明朝?为了回答此问题,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诸真宗派总簿》所列的“龙门华山派”承传谱系。龙门华山派是宗奉丘处机、郝大通两位宗师的一个道派,有可能是在道教全真龙门派和华山派形成后,从这两派中分出的一个支派。“宗派源流目录”云:“邱、郝二祖在山东济南府长清县东南十里五峰山。留传第七二:龙门华山派”,其传派谱系为:“通玄全真冲和德,正本恒成位尚仙;仁能贞心传义纪,世见生前浩太元;子阳遍转归至道,盈宿守静保丹田;情高悟开复天理,自然长颜如松年。”⑧按此谱系,大约从华山派“至一无上道,崇教演全真”之“全真”开山立派,下接“冲和德正本”,将之分成两句“通玄全真冲和德,正本恒成位尚仙”;“世见生前浩太元”,“太元”当作“太玄”,改“玄”为“元”,乃清朝避康熙帝玄烨之讳而为,前一句“通玄”之“玄”未改,则有可能是其抄本至民国时期,抄写者不避清之讳所为。李养正先生在《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八章“诸真宗派志”中说:“北京白云观收藏有《诸真宗派总簿》(手抄本)。在《宗派源流目录》之下注明:‘民国丙寅年(1926)迎宾梁至祥抄,于丁卯年(1927)冬至后之日送交客堂存。周礼鹤记。’”⑨这种有避、有不避的情况,在前代经书中亦有见者。如储华谷注《周易参同契》,经文“天道甚浩旷,太玄无形容。虚寂不可睹,匡郭以消亡”一句“匡”字缺笔⑩。当然,其他几处,如“坎离匡郭,运毂正轴”之“匡”⑾,“隐藏其匡郭,沉沦于洞虚”之“匡”⑿,储华谷注则不缺笔。我们仅以储注一处“匡”字缺笔,判定储华谷此注为宋代的注本,是能够成立的。因为有时注书时间和刻书时间并不完全相同,刻书时间可能比注书时间要晚很多。如果注书与刻书为不同朝代人所为,那么,在刻书时,往往对注书时之避讳的遵守就不那么严格。如被陈国符先生认为是唐注本的托名阴长生著《周易参同契注》,是一宋刻本,其经文“坎离匡郭”之“匡”缺笔,避宋太祖、宋太宗之讳,而经文“真人潜深渊,浮游守规中”之“渊”字,则不避唐高祖李渊之讳。⒀而由华夏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新修《中华道藏》,对于上述避讳,则一概未予遵循。我们认为,龙门华山派谱系中既有“太玄”作“太元”之避讳,亦有“通玄全真冲和德”之不避讳,究其原因,在于“写本”为清本,“抄本”为民国本所致,“写本”避讳,“抄本”则根据抄写者个人的习惯、喜好,有沿袭前朝而避讳者,亦有不沿袭前朝习惯而改定之者。但由此可知,龙门华山派的传法谱系可能源出于清朝
郝大通华山派“清静通玄化”,“玄”却未改作“元”,这意味着郝大通华山派传法谱系不避康熙之“玄”讳,故有可能出于康熙之前,或是明朝的可能性为大。而且,如果“龙门华山派”是从华山派宗谱排行第九、十字之“全真”开始分支立宗的话,既然龙门华山派谱系出于清,那么郝大通华山派之宗门谱系可能出于明朝。为进一步说明此问题,我们举《诸真宗派总簿》“宗派源流目录”第七十四位所记郝祖岔派之谱系以佐证之。其云:“(此派)在武当山。开基于明朝,留下此派,即名为郝祖岔派。”其传派谱系是:“道铃治明惠,建贞一亨嘉;莫哗纯翠景,兆裔永流传;至虚无上理,澄清定宁基;冲和德正本,仁义礼智信。”⒁此谱系明确郝祖此岔派开基于明朝,以武当山为中心,由此可知,郝大通一支于明朝时传入湖北武当山,并于此开宗立派。比较其与郝大通之华山派谱系,华山派谱系前二十字为:“至一无上道,崇教演全真;冲和德正本,仁义礼智信”;而郝祖岔派之谱系为:“道铃治明惠,建贞一亨嘉;莫哗纯翠景,兆裔永流传;至虚无上理,澄清定宁基;冲和德正本,仁义礼智信。”可以看出,岔派谱系的的首字“道”,在郝大通华山派谱系中,为第五代。其后,郝大通华山派经五代传至“冲和德正本,仁义礼智信”,而岔派谱系则另加入二十五代,至于“冲和德正本,仁义礼智信”,又有最终合流之势。如果郝大通华山派从第五代开始岔出武当山一支的所谓郝祖岔派,则此岔派的形成,与正派形成时间相距不会太远。岔派形成于明代,则正派较岔派为早,至少也应该是出在明朝,因此,郝大通后传法裔们在明朝时已经基本确定了其正派的传法谱系。
张广保先生在其《明代全真教的宗系分化与派字谱的形成》⒂一文中,考察了明万历年间山西永乐纯阳宫的华山派承传情况,为全真华山派传法谱系形成于明朝的观点,提供了重要证据。他据陈垣先生《道家金石略》所载《纯阳万寿永乐宫重修墙垣记》⒃、《重修丘祖、吕真二殿碑记》⒄、《永乐镇纯阳宫肇修善事碑文》⒅等金石碑文,找出《诸真宗派总簿》郝大通一系全真华山派字派谱系中“(崇教演)全真。冲和德正本,仁义”长达九代在山西连续传承的珍贵资料,提出《诸真宗派总簿》所载全真华山派字派传承谱系之形成可上溯至明初中期左右。为此,我们来看一下陈垣先生《道家金石略》所载《纯阳万寿永乐宫重修墙垣记》所载郝大通全真华山派弟子承传情况。此碑为“崇祯九年岁次丙子(公元1636年)仲冬望日郡庠生严广大正吾甫撰”,碑末文列:
本宫道正司道官李正□、住持王正□、陈正□、吴正义、李正春、马□良、赵□荣、□本顺、□本□、李本善、杨本从、杨仁福,张仁才、孙仁□、相仁慰、王仁慈、张仁洛、王仁裕、杨义祯、曹义路、王义明。?⒆
又陈垣先生《道家金石略》所载《重修丘祖、吕真二殿碑记》⒇,此碑为“崇祯十六年岁次癸未(公元1643年)正月谷旦郡庠生柴奎芳沐手敬题”,碑文列:
化主张和气,徒道官张德印,孙张正宾、刘正喜,重孙张本位。
祖师李全周、爷李真宁、师伯尉冲贵、吉冲修、曹冲祥。弟寇和仁、曹和忠、蔡和成、李和孝。道侄吉德食、杨德宝、宁德敬、杨德晓。道孙李正庚。
在这两通碑文中,《诸真宗派总簿》所载郝大通全真华山派“(崇教演)全真。冲和德正本,仁义”在明朝长达九代连续传承的情况就一目了然了。不过,道教各派是先有完整的字派谱系并依此承传,还是本没有字派谱系,而由后人根据前人法名再编成此字派谱系?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则虽有明代的金石资料,亦不能完全证明此字派谱系就出于明朝。对此,我们来分析一下《诸真宗派总簿》所载郝大通全真华山派字派传承谱系。此谱系第一句“至(志)一无上道,崇教演全真”,将无上之道看成是宇宙之本体,演全真为复归无上之道的根本途径;第二句“冲和德正本,仁义礼智信”,为信众提出了在世俗生活中应遵循的原则;第三、四句“嘉祥宗泰宇,万里复元亨;清静通玄化,体性悟诚明”,以泰宇为天道之常,宗泰宇为法天道而行,由此才能嘉祥而复元亨,清静而通玄化,得悟自己所具诚明之本。在此基础上,谱系认为修道者之修持其要有四:一是要通过养素而坚守其志,才能生虚灵之慧业,即所谓“养素守坚志,虚灵慧业生”;二是要通过希贤获得修行之秘诀,即“希贤遵秘法,慎修保纯贞”,通过遵秘诀慎修,保其本性之纯贞;三是要规良善、毓秀英,广开教门,弘法利善,即所谓“敬谨规良善,默功毓秀英”;四是强调出家人亦要扶世运,积功而累德,才能得大丹成就,所谓“勤能扶世运,积久大丹成”。在此基础上,全真之教基才能厚实,修道者才能得圆满之功,去而上仙,名籍仙瀛,即所谓“永建根基厚,仙瀛书盛名;圆满光华照,去天庆上升”。
因此,郝大通全真“华山派”字派承传谱系中蕴含有其宗门修持的根本大纲与具体方法、步骤,这很难说是后人根据前人法名随机编成的,而应该是先制订此完整的字派谱系,再依此承传法脉。故《诸真宗派总簿》所载郝大通全真华山派字派承传谱系在明朝就已经开始承传,就是可以基本确定下来的事实。
三、郝大通全真华山派与陈抟有什么关系?
关于陈抟(生年不详,公元989年仙逝),正史见载于《宋史·隐逸传》,道教的仙传史话,如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和张辂《太华希夷志》等,也有关于陈抟的专门传记。从陈抟所交往的朋友情况来看,介于陈抟之道侣和师友之间的人物,《宋史·隐逸传》中有孙君仿、鹿皮处士,这两人史志评价为“高尚之士”,曾指点陈抟至武当山九室岩隐居,当为陈抟之老师辈;华阴隐士李琪、关西逸人吕洞宾等,世人皆以为是神仙,亦多次来陈抟斋中,与陈抟应为师友之关系。魏泰《东轩笔录》述陈抟曾游蜀,从邛州天师观都威仪何昌一学锁鼻术(即睡功),“或一睡三年”。(21)《宋史·朱震传》:“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敦颐作通书,程颐著易传,载造太和、参两篇。”《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七《陈抟》也说:“先生明易,以数学授穆伯长,穆授李挺之,李授康节邵尧夫;以象学授种放,种授庐江许坚,许授范,为此一枝传于南方也。”(22)
上述文献关于陈抟的易学传授体系,当然皆不及郝大通。而且,金元时期,住华山修行的全真弟子中与郝大通一系有关者也不多见。以下几则材料都说明了此问题:一是尹志平执掌全真教事后,对遭连年战火破坏的华山道教有所恢复。“若华山之云台、骊山之华清、太平宗圣等宫,悉择名重耆宿以主之,兴完皆逾旧。”(23)二是陈抟所居华山之云台观曾在金元时期毁于战火,后由刘柴头弟子刘道宁修复,刘道宁亦师事丘长春(24)。三是《甘水仙源录》卷之七《颐真冲虚真人毛尊师蜕化铭》称毛养素“贞佑初,适一羽客见过,风神萧爽,师一见乃知其为异人,谨奉之久。羽客曰:此子可教。授以秘语。师问仙号,曰:我华山陈希夷也”。(25)按此记载,毛养素虽然不好说得陈抟所亲传,亦可以算是得陈抟一系之真传,但毛养素在全真七子中为马丹阳之弟子,而不为郝大通门下。
各种关于郝大通的传记资料皆言及他遇神人授“易”之事,一次是郝大通西礼重阳墓东归,在陕西岐山遇神人授“易”;一次是在河北滦城遇神人授“易”。这两次遇神人授“易”,其内容皆不得而知。不过,对照郝大通《太古集》与陈抟“龙图易”的内容,却又存在一脉相承之理,如《太古集》卷二有所谓“河图”,“河图”由“天数奇象图”与“地数偶象图”组合而成,此与陈抟“龙图易”所谓“龙图三变”而得“龙马所负之图”的说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不能不使人产生联想,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什么承传关系?
从陈抟与钟离子、吕洞宾、刘海蟾的交往,我们可以得知其与钟吕金丹派关系密切。钟吕金丹派采“易”学以论还丹之理,见诸其所属多种丹经,如《秘传正阳真人灵宝毕法》等。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认为,唐宋时期,《周易参同契》之学流传,其学引“易”论内丹修炼之理,钟吕金丹派之学、陈抟龙图易之学,张伯端的内丹之学,郝大通之《太古集》,皆与《周易参同契》有密切关系。由于张伯端偏重义理,不喜欢“泥象执文”,故其《悟真篇》虽用易图、易象之理,却没有明确将之图画于书中。而将《周易参同契》之理以易图的形式来表达之,此中的关键人物,应首推居华山修道的北宋高道陈抟。郝大通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表明其与华山陈抟之间有何直接的师徒承传关系,但其后学将郝大通一系的全真派称为“华山派”,究其原因,可能就在于郝大通的学风与陈抟的学风相近,皆以易图来阐发《周易参同契》的内丹之意。
我们认为,郝大通的道教易图学与陈抟的“易龙图”在内容上有相承袭之关系,基本属于同一个传授系统,同出一源的可能性相当大。故郝大通一系的全真“华山派”与陈抟应存在某种较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更多是一种易理上的相承关系,因其如此,故郝大通的后裔弟子们以“华山派”命名自己这一宗,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
 X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