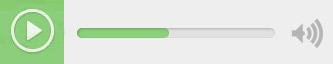百姓作家
亲情的述说
秋 天
爷爷
一位年愈古稀的老人坐在老屋的炕上,全身沐浴在暖暖的夕阳中,眯着眼睛,摇晃着身体,吚吚呀呀地唱着“人之初,性本善”。这是爷爷留在我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
受那个时代的影响,爷爷很重男轻女。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他对我疼爱有加,有求必应。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家里非常清贫,有时突然来了客人,父母都会为手头没有五元钱买菜请客而窘迫万分,更别说给孩子一些零花。然而爷爷每月尚有近30元的退休金,当时一个普通双职工家庭每月不过60元左右的工资,还要养活几个孩子。而爷爷能有这样的固定收入已经很阔绰了,所以我总是缠着爷爷要零花钱。
爷爷的双耳在参加抗美援朝时被炮弹震聋了,一开始向他要钱时我总是扒着他的耳朵大声喊叫。爷爷则用一只手搭在耳廓上侧过头细致地听我叫完,然后从怀里掏出那个用了多年的黑钱包,慢悠悠地抽出一张新崭崭、板板正正的两角票笑迷迷地递到我手上,再拍拍我的小脑瓜说声别乱花啊,我就拿着这张带有爷爷体温的角票以极大的满足感蹦跳着走了。天长日久习惯了我不再费劲地大叫,只需冲着爷爷伸出两根手指,爷爷也就心领神会地掏出他的钱包。
现在的孩子也许理解不到两角钱的价值,在当时拿着两角钱、四两粮票到任何一家食堂(那时的国营饭店大家都称做“食堂”)都可以买到一碗雪白的大米干饭和一个汤菜,饱饱地吃上一顿。
虽说不让乱花,但3分钱一根的冰棍、1分钱两颗的糖球、2分钱一卷的山楂片、9分钱一个的大面包对于一个贪嘴的孩子来说都有着极强的诱惑力,往往两角钱不到半天就一干二净了。回头再向爷爷伸手时,老人家就会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慈祥地望着我说,今天没有啦。
那时,小镇里有一个农贸市场,离我家步行不到10分钟的路程。说是市场,其实也只不过一圈破土墙围着比蓝球场大不了多少的一块土地。虽然当时全国上下割资本主义尾巴之风正盛,但在夏日里,还是有近郊的一些满脸菜色的农户挎着一蓝半筐的蔬菜瓜果来这里交易,然后换回一些日常杂品和油盐酱醋。到了香瓜熟了的季节,爷爷每日里就会穿戴整齐,胸前端端正正地戴上那只他视若珍宝的抗美援朝纪念章,背上一只小筐,雄纠纠、气昂昂地逛市场去了。爷爷常给我讲这枚纪念章的来头,讲在朝鲜时的经历,讲那些课本上没有的战斗故事。他说自己虽然没有立功授奖,但也不曾贪生怕死,打鬼子还是很勇敢的。于是,我就为他而自豪,在小伙伴和同学面前提起爷爷,便会拍着胸脯,声音也不自觉地大了许多。
每天放学的时候,爷爷也满载而归,他的筐子里永远装满了各色菜叶和人家扔掉的歪瓜劣枣之类的战利品。爷爷只偏爱我一个,每次回来,他会背着两个妹妹,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去,然后变戏法似的从身后摸出一、两只比鸡蛋大不了多少的香瓜。瓜虽小,但是熟透了的,很甜,很甜。爷爷总是吧嗒着嘴看着我香香地吃完,又贪婪地舔着手指时,摇摇头叹息说,别急,别急,明天爷爷还给你弄啊。那时香瓜才不到一角钱一斤,也不是任何人家天天买得起的。
整个小学的那几年,就在爷爷的宠爱下悄然渡过。上中学的时候,懂事了许多,我不再向爷爷讨钱了,心里却暗暗存下一个誓愿,等自己长大了,工作了,一定用第一个月工资先给爷爷买一大堆好东西,让他老人家吃个够。可惜,爷爷没能满足孙儿这个小小的夙愿。就在我参加工作的前一年,他平静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这事也便成了我终身的一个遗憾。
奶奶
爷爷去逝后,奶奶总唠叨说一个人很害怕,我就陪着年逾古稀的奶奶一同住在原来的那所老屋里。老屋就在我家房后,隔着一条3米宽的小巷,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院落,我最喜欢的就是院中那棵有十几年历史的大葡萄树。夏日里,奶奶常常坐在那浓浓的绿荫下给我们讲嫦娥奔月和牛郎织女之类的古老故事。
爷爷在世时,每年春天,他就把盘封在土中一冬的葡萄藤刨出来,引到架子上,再细致地用红布条把伸展开的枝条绑好。浇足了水之后,用不上半月,嫩嫩的绿茵就覆盖了整个小院。我就时不时地拿张小板凳坐在葡萄架下读书,写作业。闲下来时,仰头就可以看到葡萄的小小果穗从芽苞中拱出来,再开花、长大,直至挂满枝头。

毛主席逝世那年,我还只是一个二年级的小学生。那天下午,广播里低沉的声音刚播完这个噩耗,老天就好象很懂得人们心思似的,漫天飘下了细细的雨丝。当时奶奶正在葡萄架下缝补着什么,听完广播根本不敢相信,就大声问我,我说的确是他老人家去世啦。奶奶呀地一声,盯着我又问,是真的?我说是真的。奶奶呆了一下,马上转身回屋,从厨房里拎出菜刀“铛”地一下扔到院子里,接着就坐在地上流着泪数落起来,大救星没啦,天塌了,咱的大救星没啦。我吓了一跳,不知道奶奶为什么要扔菜刀。只是在幼小的心灵中隐约感受到毛主席在那一辈人心目中至高无尚的地位。按照他们最朴实的想法,毛主席的逝世无疑于百姓失去了吃穿的靠山一样。
八十年代中期,我家也终于买上了一台当时最时兴的进口索尼14英寸彩电。老奶奶平生第一次看到这么稀奇的东西,惊讶不已。她常自言自语地叨咕,这么多人还有大楼都是从哪儿来的呢?她还时不时地绕到后面扒着电视机上的散热孔左瞧右看。当然那里面除了电子元件以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更让她老人家迷惑不解。我们跟她解释了一通,可说来说去还不如不解释,结果她更糊涂了:这么丁点个盒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东西?

终于有一天,奶奶的一句名言诞生了。那天晚上7点,照例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这之前奏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占满了整个荧屏。这一过程每天都在重复,奶奶也渐渐耳熟能详。可偏巧那天色彩不大好,爸爸就过去拧微调旋钮。正调着,聚精会神观看电视的奶奶满有把握地发话了,你不用动,这旗子是风刮的,刮一会儿就不刮啦。立刻全家人都开怀大笑起来,小妹更是笑得弯着腰,好半天没站起来。正这时,镜头转到天安门的画面,老奶奶则依然一本正经地说,你看,我说的嘛,这不是不刮了吧。从此,“刮一会儿就不刮了”这句话成了我家的经典段子,每每提起来大家就忍俊不禁,至少让我们当做话题笑了有半年多。
奶奶是大家闺秀,富商的家庭、严厉的家教让她真正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生中居然没有走出家乡的小镇看看外面的世界,就连家附近当年新建的两层的百货大楼也没有去逛过,她总说怕走丢了找不着家。家道中落后奶奶嫁给了并不富有的爷爷,于是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守在爷爷身边,一心一意地操持家务做贤妻良母,精心地侍候爷爷的生活起居。从我记事起,奶奶就一直是那么慈祥。爷爷的脾气不好,动辙张口就骂,奶奶总是逆来顺受,天天让爷爷过着饭来张口,水来洗手的“大老爷”生活。因为在她的心目中爷爷是上班挣钱的,而自己只是一个裹着小脚围着锅台转的家庭妇女,一根依附着大树生存的小藤。
爷爷去世后,奶奶突然间没什么事可做,就常常和邻居大爷大妈们“摸纸牌”。奶奶去世的前一天,她照例和邻居玩牌,可总是不“和牌”。不知玩了多少圈,突然,风向大转,手气异常地好,而且是坐庄一连“和”了5次,最后一把牌还是满贯。据说奶奶当时异常高兴,手捧着牌笑了好半天,却突然口吐白沫晕了过去。大家慌忙招救护车送医院,医生说是脑溢血。

刚躺到病床上时,奶奶清醒了几分钟,还来得及看一眼及时赶来的她的三个儿子,但很快就神志不清了。等到我和妹妹放学回来到医院看望时,奶奶只是闭着眼睛气若游丝,在耳边大声叫喊也不应。就这样,奶奶在昏迷了一天一夜后安详地去了。这天,距爷爷辞世还不到百日。邻居一位老人说,爷爷这辈子根本离不开奶奶,在百日内将她接走到天国过好日子去了。也有人说,这一对老人才是真正的生死相依。
奶奶常说有我陪着她在老屋里才不害怕。可她发病的前一天下午,我去一个好同学家祝贺生日喝了些酒,回来后就一头栽到家中的小床上昏昏睡去。妈妈说,那天晚饭后,奶奶一连过来几次,见我睡得香,就没忍心叫我。后来,大人们讲就因为我那天没有去陪奶奶,爷爷的灵才敢在那天夜里飞回到老屋把奶奶的魂接走了。虽然知道这只是无稽之谈,但可以想象奶奶是在怎样的恐惧中渡过了那惊魂一夜。所以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好内疚,总是觉得奶奶的死都怪我。因为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啊,老奶奶还没有享受到更多的福。
奶奶去世那天,天气异常。当时已是5月初的艳阳天,大田里的玉米苗才从土中拱出一寸高,各种果树花儿刚刚绽放。可突然天降大雪,足足下了一夜。据老人讲,这可是百年未遇的事情。第二天,雪后初晴,绿的嫩叶,白的树挂,粉的花瓣,一幅奇景突显眼前。湿湿的雪把果树的枝条压得弯弯,花儿也冻坏无数,以至于那年的果树大减产。
老奶奶就在初夏那一片特别的银白世界里安祥地走了------
爸爸
坐在爸爸面前,蓦然发现年已古稀的他精神矍铄,依然不显老。这应该和爸爸即使身处逆境仍然能够经常保持一个良好心态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有很大关系。
爸爸出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那时,爸爸已经有了两个兄长,一家人住在海龙镇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生活异常艰苦,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
爸爸命途多舛,刚一降生就面临着生死考验。那是那年冬月东北最寒冷的一天,外面滴水成冰,当时奶奶怀着爸爸已近临产。就在那个月圆的夜里,奶奶独自一人出去上茅厕,偏巧这时爸爸降生了。仅仅是那一瞬间,他顺着农村简陋厕所的冰溜子滑到了菜园子的破栅栏边。孩子微弱的哭声和血腥气惊动了邻家的一只大黑狗。当时,这家伙大概正饿着肚子到处搜巡食物,刚好遛达到这里,爸爸滑了下来。已经饿红了眼的大黑狗当然不会放过这送到嘴边的美餐,眼看着它把脑袋伸过来,张开了血盆大口。
据说奶奶当时急红了眼,她连滚带爬地扑过去,顺手捡起一根玉米桔杆连哭带喊地打跑了大黑狗,硬是从狗爪下抢回了自己的孩子。
由于缺少柴草,冬天的老屋里冷得象冰柜,四周的墙壁上结了厚厚的霜,炕上也总是湿湿的,连块象样的席子都没有。奶奶能做到的只是每天从灶坑中扒出点草木灰来铺在炕头,再把又瘦又小的爸爸放在上面的破棉絮中。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爸爸活了下来。
几年后,全家搬迁到梅河口,爷爷又在镇医院里找到了做厨师的差事,生活的景况才逐渐好了一点点。
爸爸18岁那年冬季,又是最寒冷的时节,爸爸生命里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那时镇里的第三中学院中有一口大井,全镇百十户人家的吃水都靠它。那天清晨,爸爸照例去挑水。当时井口已经被冻成了一个仅容两只水桶进出的大冰窟窿,井沿光滑无比。爸爸到井边的时候,有一位中年妇女在汲水,她吃力地摇着辘轳,体力渐渐不支。爸爸一向热心肠,他二话没说,放下水桶上前帮忙。岂料就在爸爸刚一搭手还没用上力的时候,那女人却突然滑倒在地,重重的摇把狠狠地打在身材瘦小的爸爸肩头,他失去重心,随着下坠的井绳滑进了10多米深的大井中。

爸爸突然扎进冰冷刺骨的井水中,几乎晕了过去,那一瞬间棉衣棉裤浸透了冰水重如千钧,周围黑乎乎的。呛了几口水后,他挣扎着让脑袋露出水面,手扒着井壁略突出的石头,喘息了好一阵,冰水迅速消耗着身体的热量令他颤抖不止。后来爸爸摸索着找到了垂下的井绳,但根本无力攀爬。他只好紧紧抓住那根救命绳,绝望地看着井口那一小块灰蒙蒙的天,连喊救命的力气都没有了。
井台上的那位中年妇女,眼见爸爸掉进了冰洞,吓得哭喊起来。哭声惊动了周围的邻居,几名大汉跑来,合力摇辘轳把爸爸拽了上来。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爸爸仍然尽力汲上两桶水,挣扎着挑回了家。仅仅这两百多米的路,到家时,爸爸全身上下已经冻成了冰砣。
1975年秋,爸爸只因为背后谈了几句有关“文革”的小道消息,就被朋友告密,以恶毒攻击伟大旗手的罪名抓进了拘留所。在那里,爸爸受尽了折磨。为了能够见到妈妈和自己的孩子,在一次强迫劳动中,他装做失手故意用镐砸伤了自己的脚而获得了就医的机会。第二年春的一天,我们在医院见到了爸爸,仅仅相隔几个月,爸爸已经变得不成样子,他拖着缠满绷带的脚,步履艰难地向我们挪过来,我和年幼的两个妹妹扑向他身边,抱着他的腿放声大哭。爸爸挨个抚摸着我们的头微笑着说,好孩子别哭了,爸爸这不是回来了。其实那时,他仍然在监管之下,没有自由,这样短暂的见面机会也是多方争取来的。但他依然笑对人生,仍然告诉我们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强。好在不久后的金秋十月,我们一家又重新团聚了。

爸爸总是那样乐观向上,而且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特强。那是刚刚在年轻人当中流行迪斯科的时候,父辈中几乎没几人能接受得了,说那是扭屁股舞、流氓舞。可爸爸很开通,说这个舞也没什么不好,跳起来全身的大部分关节都活动,对锻炼身体有好处。他还在家中开小型舞会和我的那些同学、小伙伴们一起跳。大家玩得都非常开心,纷纷说你爸爸真开事儿。可爸爸有自己的原则和标准,他循循善诱,引导我们对待事情要看积极的一面。决不允许我们象社会上的一些年轻人那样,提着录音机,戴着蛤蟆镜(大墨镜),穿着花衬衫、喇叭裤到大街上招摇。
爸爸工作态度非常严谨,绝不允许有半点差错。七十年代末,爸爸在生产资料公司做会计工作。有时单位的人借出差之机多报销几角钱的旅差费。爸爸一一审出,态度坚决地要求重新填写。有时甚至为丁点小事与人家争得面红耳赤,常常弄得对方在众人面前下不来台,因此而记恨爸爸。可爸爸就是这么个人,这种性格。吵过争过之后,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他依然如故热心地帮这忙那。久了,大家也都理解了爸爸,说他是脾气酸急,古道热肠。
乐观的爸爸在对待我们学习上一向非常严格且有超前意识。在六、七十年代多数家庭都没有意识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而我只有2岁时,他就开始教我识字和单字组词。上小学三年级时他又给我请来了同单位的一位从前的老师教我英语,而那时也只有中学才开简单的英语课。可惜,我辜负了爸爸的一片苦心,英语一直学得不好。

爸爸不仅重视学习,其它的各方面也从不放松,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毛主席说的那句,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我小时候,他在家中的小院里自制并安装了单杠、吊环、秋千等简单的体育器材,使我们在学习之余的玩耍中锻炼了身体。以至于上中学后,我在单杠上可以单腿挂杠后回环连续转50圈而面不改色,引体向上标准姿势连做30个没问题,常引起同学们的佩服。
退休后,爸爸还是为儿女、为孙辈操心着这事那事。有时也应人邀请去帮助有些企业做些老本行的财会工作,在他看来,钱不钱的无所谓,重要的是天天有事做,别闲着。
如今,爸爸还在家里的封闭阳台上栽种了盆葡萄、小柿子,还有一箱箱的韭菜、大葱、小白菜什么的,时不时的给家人或者朋友奉献些绿色食品,怡然自得地享受着生活的情趣。
看样子,爸爸还是不老,我也希望他永远不老。

妈妈
走在大街上,猛然看到鲜花店前“献上儿女的情,献给妈妈的爱”的大字广告,才意识到母亲节的来临。慕然想起半生操劳,如今已鬓染白霜的妈妈,从没有涉足过鲜花店这种浪漫之地的我却毫不犹豫地为妈妈买下了一束康乃馨。
当我把这束鲜花捧回家,恭恭敬敬献给妈妈时,妈妈却一个劲地埋怨说,花这个钱干啥,不当吃不当穿。可是,妈妈从我手中接过花的一刹那,我却分明捕捉到了妈妈眼里那闪现出的惊喜。火红的康乃馨映着妈妈的脸,妈妈显得精神焕发。我知道,这束小小的花不足以表达儿子对母亲生养之恩的回报,但年逾古稀的妈妈更需要精神的慰藉。

妈妈是一个农家姑娘,六十年代农村贫困的生活环境养成了她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品格。15岁那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城的幼儿师范学校,成了那个偏僻小山村第一个上中专的佼佼者。那时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家家户户连野菜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然而学校每天尚有两个玉米面的大饼,妈妈舍不得吃,每天攒下一个。等到周日就跋涉20多里山路,把这六个玉米饼连同一小罐节省下来的咸菜带回去给家中唯一的一个棒劳力,我的外祖父。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妈妈和爸爸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吵个不休。也许是上天有意捉弄他们,还是前世有什么恩怨或是某种巧合,他们结婚的时间居然选在八一建军节,谁都知道这是一个打仗的日子。多年以后,当他们的青春在不断的“战火硝烟”中悄悄溜走,当儿女们在他们的唇枪舌剑中战战惊惊长大成人时,老俩口也终于停止了长时间的内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些年为什么吵架,吵得有何意义,恐怕自己都弄不十分清楚。
妈妈嫁给父亲的头几年,父亲正深入农村搞“社教”,几个月甚至半年才回来一次。这样,生活的重担全落在妈妈柔弱的肩头。她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孝敬公婆,还要照看年幼的我们兄妹三人。

记得有一天早晨下大雨,妈妈背着只有1岁多的小妹,用自行车载着3岁的大妹和5岁的我去上班。道远、雨大、路滑,她只好推着车子艰难地行进在风雨中,雨衣、雨伞根本遮不住肆虐的风雨。等按时到了单位,大人孩子浑身上下都无一处干爽。坐在幼儿园的长椅上,妈妈双手搂住三个孩子,泪水拌着雨水顺着脸颊无声地流淌下来,我们也都跟着号淘大哭。然而妈妈没有一句怨言,擦干眼泪毅然走向她的工作岗位。
几十年过去了,妈妈依然是那样的勤劳,即使是在生病卧床时仍惦念着儿女,操心着家中的大事小情。平凡的妈妈是那种纯粹的贤妻良母式的人,为了丈夫、儿女们的事业,她默默地甘愿牺牲自己,提前退休在家,洗衣、做饭、干家务、照看孙辈,把一切料理得井井有条,让我们这些奔波在外、已经成家立业的儿女们毫无后顾之忧。出门在外也会时常想起亲爱的妈妈温柔臂膀精心呵护下的那里,还有一个人世间最最温暖的家。

妈妈为家、为儿女付出的太多了,岁月的年轮在她曾经美丽的脸上无情地刻下了条条刀痕,她的身体也不再挺拨。望着妈妈斑驳的白发,儿女们又能为她老人家做些什么呢?一切都微不足道。而这几十年涓涓的母爱又岂是一束鲜花所能表达得了的?
在母亲节里献给母亲一束花,心中默默祝愿妈妈健康长寿,今后的岁月里永远有份好心情。有妈妈健在,也是天下做儿女的一个最大的福份。

作者简介:
邱红天,男,笔名 秋天。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通化市作家协会理事。多年勤于笔耕,在《中国电力报》、《吉林日报》、《城市晚报》、《通化日报》、《读者》文摘、《中国保健》杂志等媒体发表文字及篆刻近千篇,曾获得吉林省电视专题片、电视散文一等奖和优秀奖。著有通讯、纪实文集《秋天的品味》和散文、小说集《秋天的红叶》。业余时间喜欢琴棋书画,但浅尝辄止。对周易八卦六爻、四柱预测兴趣颇浓并积极研究姓名学。
公告:2017年莫然文学优秀作者选拨即将开始,我们将选择投稿超过十篇,阅读量大的作者六名,颁发证书给予鼓励,奖励名单将于5月1日公布,请各位老师积极参加,为莫然文学的发展添砖加瓦。
责编:朱进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