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生于贫瘠的土地,却拥有丰盈饱满的灵魂。  谁也想不到,一位来自八百里秦川的农妇,会因一袭话震撼全国。 甚至,因此改变别人的人生。 2001年。 刘小样身穿一件红色呢子外套。 坐在院子里的矮凳上,接受央视节目《半边天》的采访。  主持人问她:“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她顿了下。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 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 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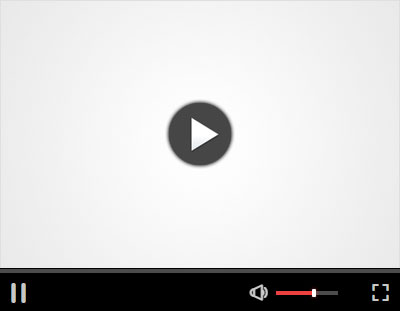 人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 她就做饭,她就洗衣服,她就看孩子,她就做家务,她就干地里活。 然后她就去逛逛,她就这些,你说做这些要有什么思想,她不需要有思想。 我不接受这个。 说这段话时,她泪光泫然,几度哽咽。 这一刻的倾诉,实在等太久了。 过去的三十余年内,她一直处于失语状态。 人生经历,与其他农妇并无二异。 早早地嫁人、生娃、相夫教子。 终日在斗室里洗衣做饭,一遍遍嚼着寡淡温吞的人生。 如此生活三十年……  没有人看见她的内心。 也没有人愿意拨开生活的表层,触摸她的灵魂。 哪怕她的灵魂,炽热而滚烫。  如果把2001年的这场倾诉,当成她的觉醒。 那在觉醒之前,更多的是不甘与挣扎。 她出生在陕西省咸阳市兴平村。 初二时被迫辍学。 1991年,她23岁。 认识了隔壁村,一个叫王树生的男人。俩人经媒妁之言结婚。  虽说是媒妁之言,但她是满意的。 她好读书。 王树生的爷爷,曾是私塾先生。 家中祖宅的门楣上,刻着四个大字——“耕读传家”。 嫁到一个读书人家,倒也是一种慰藉。  婚后,育有一儿一女。 王树生是个勤快人。 务实忠厚,常年在外连轴忙碌。 很快便攒下一笔钱。盖了房。买了彩电。 左邻右舍艳羡不已。  一年四季,刘小样只需干2个月的农活。 剩下10个月,都赋闲在家。 生活看似还不错。 一方院、三餐足。饱食暖衣。 可没问题,恰恰等于“有问题”。 就像她说的,“一切,太平了。” 平得不对劲,平得可怕。  居住的地方,离娘家仅5公里。 而她,永远在做饭。 “一天三顿,永远在和面、擀面和煮面,唯一能变的只有面的形状。”  田垄一望无际,却感觉四面皆墙。 精神层面的赤贫,让她痛苦。 她想要的,是知识,是跃过这个“圈”,绝非困在方寸之地,甘之如饴。 出走之心,开始萌芽。 后来,王树生带她去了一次西安。 钟楼下人头攒动,车马往来不绝。城市的霓虹灯在眸中跳跃,照得她的脸颊滚烫发红。 那感觉,亦真亦幻。 美好。但也残忍。 她说,她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把她和世界分隔开来。 从家到西安往返的路费,明明只需要9块钱,但条路看得见,却摸不着。 她失声痛哭,近乎崩溃。 回到家后,出走的欲望越甚。 蠢蠢欲动着,日日翻腾着。  可,这种欲望在这片土地上,太不合时宜。 村里的人,都认为农妇就该洗衣做饭。 不能有思想。更不能有自我意识。 在这种无形的“规矩”之下,她只能深埋那份热切,任由它翻腾。 转而用一种极为隐晦的方式继续抗争—— 她抄古诗。 在便利贴上写:“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她看电视。 把《读书时间》和《半边天》当做书来读。  她听书。 学收音机里的普通话。听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 她穿红色的衣服。 因为红色代表鲜活,代表热烈,代表生命力。 每个行为,都在悄然抗争。 就这样。 她小心翼翼地戴着镣铐做梦,维持了很多年。  又是一年秋。 落叶满地,萧瑟一片。 她立野眺望,倍感荒凉。心想:人生就该如此了吗?儿女已经上小学了,难道不该追寻些什么? 内心争斗几个回合之后,她终于觉醒。 回到家,照着《半边天》节目的地址,写了一封信。  然后,骑了十里地的自行车到县城将信寄出。 这封信,震撼了《半边天》的节目组。 信里,刘小样说: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 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西安。 不可以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 这里有很多约定俗成的规矩。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这里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可是我就是不喜欢,因为它太平了。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不相信这些饱蘸自由意志的文字,出自一个农妇之手。 他们想深挖这个女性背后的故事。 很快,节目组扛着摄像机,找到了刘小样。 刘小样却生出了退意,一逃再逃。 她说:“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个异类,在农村,心思不放在家里,整天想入非非,这可不是好女人该干的事。” 没办法。 主持人张越只好在与她同吃住,试图建立信任感。 三天后,采访正式开始。 刘小样与张越面对面交谈,将自己一层层剥离开来。  对话中,张越察觉到了刘小样内心的隐痛。 对此,刘小样却说:“我宁愿痛苦,我不要麻木。” “痛苦只是一种蜕变,生活就是要不停地蜕变,它才能前进,才能有力量。”  “人向往的时候,眼睛里会有光泽。” “我就怕我失去那些激情,怕我失去那些感动,所以我不停地需要更多的知识,需要知道更多的事情。”  坐她对面的张越震撼了。 与她同床共枕十几年的王树生,也震撼了。 他从不知道,原来妻子的灵魂是如此丰盈。 节目录完后,刘小样抱着张越哭了很久。 “你们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就像一场梦一样。你们走了,我就又一个人了。” 是的。 节目组没有到来之前,她是孤独的。 如池中鱼,笼中鸟。 蜷卧在乡村一隅,日日经历思想鏖战。 好在,这样的煎熬并没有一直持续。  节目播出后,全国上下为之震惊。 她的话,像是一记猛锤,击中了电视机前的无数个“刘小样”。 她们暗自笃定,要走出大山,到更广袤的天地去。 其中,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女孩,被她影响终生。 她在听了刘小样的话后,努力读书,出国留学,在欧洲做了一名纪录片导演。 而刘小样自己,也开始了她的出走与突围。  她开始帮邻居种田,体验上班的感觉。 2006年,又去县城商业街做售货员。 学做账。学搭配。 那是她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出走”。 可,好景不长。 两年之后,商场倒闭。 再之后,她坐上绿皮火车去了贵州。 依旧不顺利。 干了没多久,便折返当地县城,在一个小学当起了生活老师。 期间,她坚持每日读书看报,不停地汲取知识。 两年后,儿女考上了大学。 相夫教子的任务终于完成,她开启第三次“出走”。  43岁的她,前往江苏昆山。 在一家工厂的食堂,找了份厨师的工作。 她虽然跨越山海,去向了远方。 心,却始终没有觅得归处。 工友们不懂她。 她和谁都聊不到一起。孤独感与日俱增。  2011年年底。 在家人的劝说下,她无奈返乡。 离开前,专程去了趟昆山市立图书馆。 在那里,默默完成告别。  三次突围的失败。 把她的不甘,彻底连根剪断。 她终日怨怼,自我怀疑。 为何自己始终平静不下来? 为何自己无法拥抱这片土地? 她怀疑自己病了。 2016年,她到西安一家心理医院看病。 治病期间,婆婆病倒。她回到家,照顾婆婆的衣食起居。 自此,不再蠢蠢欲动。 烧了以前写的文字。 收起了王小波、鲁迅、毕淑敏的书。 像是要扼杀掉那个曾“清醒着做梦”的自己。  从前,她讨厌村里那些,每天竖着耳朵等待是非的老妪们。 现在,她尝试接受。 从前,她看电影只愿去电影院,她认为那样有仪式感。 现在,她不再“苛刻”。 她开始打麻将。 开始承认自我局限,拥抱脚下那片土地。 并用莫言书里“晚熟的人”来自嘲。 她说:“接受吧。如果我还年轻,早就待不住了。可我老了,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我必须待着。”  是啊。 她踮着脚去够了,够不到。 “内心的充盈”与“生活的贫瘠”两者之间的对冲,给她带去太多痛苦。 她只能极力稀释,让一切如昨,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 劳碌半生,几经辗转。 如今看来,似是大梦一场。  她终究回到了原本的轨道上。 安分守己,按部就班。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 那只与无性、无智、无趣为敌,跨过沉沦的一切向平庸开战的猪,在叛逃之后,长出了锋利的獠牙。 莱辛笔下的家庭主妇凯特·布朗,在出走之后,又折返了家庭。 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刘小样。 格子间的女孩。厨房里的母亲….. 她们出走之后的结果,无非以上两种。 但绝大多数,属于后者。 这群人心中都住着一座巴别塔。 囿于现实,无法完全漠视生活的设置。这才是“刘小样们”的集体困境。 回到刘小样本身。 没能走出关中平原,就等于被现实放倒了吗? 答案绝不是肯定的。 2019年。 刘小样的婆婆离世。 从那时起,她开始种花。 在前院和后院,种满了雏菊、月季、郁金香、鸡冠花...... 朵朵娇艳。雨摧不凋。  小小的庭院,是她的理想国。 在那里,她不被形塑,不怕桎梏。悄悄叛逆,自由生长。 2021年,她接受采访。 有人问她,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悲剧吗。 她淡然回答。 算悲壮吧。 毕竟,悲壮这词,本身就有美在里头呢。 是的。 “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 三次突围,三次失足。 刘小样的出走,还在继续。 庭院里的那一抹红,也不会荼靡。 它会一直对抗干瘪与枯槁,荒芜与庸常。 会一直灿烂地开,向远方开。千里奔袭,直至燎原。  参考资料: 人物 https://mp.weixin.qq.com/s/aGLE93s5vgyWDletOnmqRQ 半边天 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26582773/?dt_dapp=1  PS: 应广大读者朋友的要求,在此公布一下我的私人微信,欢迎大家前来。👇 可能无法天天聊天 但我还是期望你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