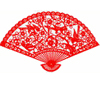他心不在焉,不以为然的,嘴唇闪动着,自言自语道:“为什么垃圾站说撤走就撤走呢?” “这是真的吗!
他对他的技校同学,说了他的一些心事儿。他说,话还是从他租住的楼房紧挨着垃圾中转站说起—
要说他住的那栋老式楼房,从一层到楼顶是准七层的(地下室未算)。为方便起见,他租房时,选了楼的第二层,还是同一楼层三套房中中间的那套。每层仅可住三户人家。房号从里往外排,如101、102、103,层层如此。但每层的序号又是有分别的,都要根据楼层数的不同,把房号数字的第一个“数”,改为该楼楼层数。这种排序,是绝无二法的。
初开始,他老感觉楼房有点怪怪的,但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反正,怪不习惯的。
“咋不习惯?”
“看上去,楼房显得不规正。”
“那是什么个不规正法儿?”
“你自个儿去瞄,管它是个啥形貌!”他在心里自问自答着。
他瞄呀瞄——无论是从楼房正前方看去,还是从楼房前左侧右侧看去,或是从前方高处低处看去,楼房的形貌,像似一种“斗口叉开状”或“手风琴拉开状”。虽然从前面看时,楼中间的那部分因藏于后面看不见,但楼房还是显得很有轮廓的:因楼的正面,形状与其它楼房绝然不同。
他居住的小区,大小车辆是从城中主大道、经小区中间门岗进来的;可朝南行,也可向北驶,还可折拐朝东行。他所租住的楼房,与门岗有三四百米之遥。当车从门岗进来时,左拐朝南行就到了小吃街,右拐向北行就上了凤凰路。然而,车要从他所住的楼下经过,须在楼房左侧边右拐,才可到达楼下铁栅栏门边停车——若车再向东走,径直可通往城中主大道。
他因所住楼房紧挨着垃圾中转站,心底里像罩上了一层灰蒙。他很纠结,但又说不出口。
周五,他想到东山坡转转,这是他上东山坡的第一天。他在东山坡的高处,望着居民小区,心里说:“小区咋还能呈长方形四正的状态呢?”他还是闷闷不乐的。
虽然快周末了,他的心里还是琢磨了很多事儿:
比如一日三餐,涉及的是千万、亿万人的事儿;一日三秋,涉及到的只是甲或乙两个人的事儿;而三餐四季,仅涉及一年的光景;岁岁年年,却涉及的是万古不变的时空星辰……一会儿,他想到了老家清凌凌的河水;一会儿,他仿佛看见碧绿碧绿的江水正向北方流去。他还想的有:诸如儿女们的事业发展、收入高低、压力轻重,以及孙儿孙女、外孙儿外孙女的学业成绩……和乡村的振兴与发展,等等。
“什么乱七八糟的。想多了想远了。闲操心做啥子咧!”他拍拍后脑勺说。
他又思忖着——
其实,小区长有三千米之余,宽在四百米以内。从东往西排,建有四列楼房;从南向北数,立有十四五列楼房。不论纵排横排,小区拢共起建有五十多栋楼房,居住有千余户人家。行车道横向一字排开,通南走北;而纵向一拐,则只能行止于西边楼房下所架设的铁栅栏边缘。
在小区,花圃里分别植有柿子树、香樟、云杉、桂树、枇杷,等是。而小区西边的楼房、铁栅栏边缘外更有行车道、人行道、休憩园和设置有序的健身器材——再往西边延伸,是那被一株株广玉兰、香樟和四季桂所蓬护着的河岸走廊,以及园中低矮葱郁的鲜花与草木。
他想到小区周遭的景致,心里不禁平添了几分悦喜。他转念又一想:
在其所居住的小区楼房里,人们每天都能听到斑鸠“咕咕、咕咕”的叫声。有时,从不远处又传来“换窗纱、换纱窗”的嗡声。在季春的夕落或清晨,还能听到一种不知名的鸟,从楼房后面香樟树上、楼房右侧柿子树上、或房中客厅窗前垃圾站背后的广玉兰树叶中,发出一串“去琴琴儿曲几略、去琴琴儿曲几略”的叫声。声音清脆悦耳,像一首歌。
第二天,是周六。他早早地吃了一碗牛肉面,又上了东山坡。当他尽兴赏景后,从东山坡高处往回走,穿过小区小广场边边时,却有人对他说:
“知道不,好多年了!设在小区里的垃圾中转站,今天已经正式撤走了!”他不以为然,紧接着又说:不可能,不可能!
第三天,才真正是周末。早上,当他从菜市场往回走、正欲穿过所住楼房的一楼防护大门时,猛然看到大门上贴有“通知”,落款署名为某某物业服务中心,开端第一句是:“某某小区垃圾中转站已正式撤离。”……文末还缀了一句:“感谢您的配合!”
他说:“这——这,这难道是真的嘛!”、
第四天,又是周一。清晨,他在休闲区晨练晨读。但今天这个大清早,好像有些不一般,仿佛奇迹就要发生。读着读着,他突然站起来,张开双臂,对身外的人和物大声地说:
听听吧——
远处,有斑鸠“咕咕咕——咕咕咕”的叫个不停;近处,有小小鸟“叽叽——叽叽叽”的啁啾;还有从不同方位绿树上发出来的“去琴琴儿曲几略——去琴琴儿曲几略”如诗般的歌唱,像不像是给咱小区配成的一首歌谣!他还哼着小曲:“哎哎哎哟,哎哎哎哎哟!”
在场的人们,见他如此这般情态,多半以为是:他在给自己心理上找别扭。他不管别人心里怎么想,但他认为:那确实是一首清脆悦耳动听的歌谣。
接下来,他像似换了新妆一样,像似变了一个人一样。邻居们都说,他越发显得年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