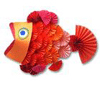情字何解?
或许无解。
它来。如春风拂柳。
它去。如秋叶零落。
心,曾为它悸动。
也为它,碎裂。
古人笔下,爱是蜜糖。更是苦药。
五首诗。五段情殇。
读懂它们。也就读懂了,爱情的千回百转,万般苦楚。

《暮秋独游曲江》
唐 · 李商隐
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
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李商隐的诗,总是带着一种朦胧的美,和一种化不开的愁。这首《暮秋独游曲江》,便是如此。
曲江,长安名胜。曾是唐人游赏胜地。李商隐独游于此,时值暮秋。秋日本就萧瑟,更何况是独游。
开篇两句,就将时间的流转和情感的绵延写尽。“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春天,荷叶初生,本是生机勃勃。诗人心中却已有了恨意。这恨,或许是相思不得,或许是情路坎坷。到了秋天,荷叶枯萎,春日的恨意非但没有消散,反而“成”了。这个“成”字,用得极好。它不是简单的累积,而是积淀、凝固,成了心中无法磨灭的印记。从春到秋,从生到枯,恨意始终相随,与季节一同轮回。
“深知身在情长在”。这一句是全诗的眼。诗人深深明白,只要自己还活着,这份情,这份恨,就会一直存在。这是一种清醒的绝望。不是不知道痛苦,而是知道痛苦将伴随一生,却无力摆脱。爱得有多深,执念有多深,这痛就有多长久。他没有抱怨,没有呼天抢地,只是用一种近乎平静的语调,述说着一个残酷的事实。
最后,“怅望江头江水声”。诗人怅然远望。江水滔滔,奔流不息。这江水声,是背景,也是心声。它单调,重复,如同诗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愁绪。它宏大,永恒,反衬出个体的渺小与无奈。那一声声江水,仿佛在应和着诗人内心的叹息,又仿佛在诉说着世间多少无尽的离合悲欢。李商隐的痛,是绵长的,是融入骨血的,是伴随生命始终的。

《赠去婢》
唐 · 崔郊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
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崔郊这首《赠去婢》,背后有一个曲折而又幸运的故事。但诗本身,却写尽了身份悬殊下爱情的悲哀。
故事很动人。崔郊爱上了姑母家的婢女,婢女却被卖给了显贵于頔。两人寒食节偶遇,崔郊写下此诗。于頔读到后,被诗中真情打动,成人之美。但我们剥开这层幸运的结局,看诗本身,那份痛楚是真实而尖锐的。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起句便设下对比。一边是权贵们追逐美色,如苍蝇逐臭。另一边是无助的美人,如绿珠一般,只能暗自垂泪。绿珠是魏晋石崇的爱妾,貌美善舞。石崇失势,权臣孙秀欲夺绿珠,绿珠坠楼而死。这里用绿珠,暗示了婢女的命运可能同样悲惨,身不由己,如玩物般被人争夺。那滴落罗巾的泪,是无声的抗议,是绝望的写照。
“侯门一入深如海”。这一句,千古流传,道尽了阶层壁垒的森严。那高门大院,进去之后,便如同坠入深海,再难回头。海的深邃,海的隔绝,海的冰冷,都成了婢女命运的象征。外面的人望不进去,里面的人也出不来。这“海”,隔断了她与过去的一切联系,也隔断了她与崔郊的爱情。
“从此萧郎是路人。”这是何等决绝,何等无奈的哀叹。“萧郎”,泛指女子的意中人。曾经的甜蜜,曾经的山盟海誓,在“侯门深似海”的现实面前,都化为泡影。从今往后,你我便如陌路人,再无交集。这七个字,字字泣血。它不是不爱了,而是爱不起了,爱不能了。幸运的是,于頔是个“解风情”的。但若非如此呢?这首诗,便是这对苦命鸳鸯的墓志铭。

《寄人 其一》
五代至宋 · 张泌
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
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
张泌的这首《寄人》,没有激烈的冲突,却有一种幽长婉转的悲戚。
“别梦依依到谢家”。诗人与心上人分别后,魂牵梦萦。梦中,他又回到了“谢家”。“谢家”可能指代恋人所居之处,或许是东晋谢安、谢玄家族那样的名门望族,也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代称。那“依依”二字,写出了梦境的缠绵,也写出了诗人情感的缱绻不舍。
“小廊回合曲阑斜”。这是梦中所见的景象。小小的回廊,曲折的栏杆。这些景物,寻常却又充满了回忆。它们是昔日爱情的见证。诗人对这些细节记得如此清晰,可见用情之深。然而,梦终究是梦,醒来之后,更添惆怅。
“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这两句是点睛之笔,也是最令人心伤之处。诗人说,这世间仿佛只有天上的月亮还带着几分“多情”。它默默地照着庭院。照着谁呢?照着“离人”,也照着“落花”。“离人”自然是诗人自己,也可能是他思念的远方之人。而“落花”则意蕴丰富。它可以指凋零的春花,象征着逝去的美好时光,逝去的爱情。也可以指代孤寂的女子,在月下独自飘零。月光本是清冷无情的,诗人却说它“多情”,这正是反衬出人间的无情,或至少是所爱之人的“无情”——因为分别,因为无法相见。月亮尚且为这分离的苦楚、为这凋零的生命而停留,而人却只能承受这分离。张泌的痛,是思念的痛,是物是人非、好景不长的惆怅。

《沈园二首 其一》
南宋 · 陆游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陆游与唐琬的爱情悲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令人扼腕的故事之一。这首《沈园》,是他晚年重游旧地所作。
此时的陆游,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距离他与唐琬在沈园被迫分离,已过去了数十年。但时间并没有冲淡一切。
“城上斜阳画角哀”。开篇便奠定了悲凉的基调。斜阳西下,残红如血。城头传来悲凉的号角声。这景象,这声音,都透着一股迟暮的哀愁。诗人带着这样的心情,走进了沈园。
“沈园非复旧池台”。沈园的池台楼阁或许依旧,但在诗人眼中,它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因为,物是人非。当年那个赋予此地无限美好的女子,已经不在了。没有了她,再美的景致也失去了色彩。这是一种深沉的失落感。
“伤心桥下春波绿”。沈园的桥,因为承载了太多的伤心往事,所以在诗人心中,它就是“伤心桥”。桥下的春水,依然碧绿,荡漾着生机。这盎然的春意,与诗人心中的悲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春光越是明媚,越反衬出诗人内心的凄苦。那绿色的春波,仿佛映照出诗人破碎的心。
“曾是惊鸿照影来。”这是对往日最痛彻心扉的回忆。“惊鸿”,喻指唐琬体态轻盈,容貌美好,如同惊飞的鸿雁,在水面留下一瞥倩影。当年,她曾在这里,她的身影曾倒映在春波之中。那惊鸿一瞥,成了诗人心中永恒的定格。如今,春波依旧,伊人何在?“曾是”二字,包含了多少的甜蜜与辛酸。越是美好的回忆,在失去之后,就越是伤人。陆游的痛,是生死相隔的痛,是往事如刺、触景生情的痛。

《写情》
中唐 · 李益
水纹珍簟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
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
“水纹珍簟思悠悠”。夜深人静,诗人独卧在饰有水纹的珍贵竹席上。思绪悠远,绵绵不绝。这思绪,自然是关于那份逝去的爱情。一个“悠悠”,写出了失眠,写出了愁思的漫长。
“千里佳期一夕休。”这是何等沉重的打击。曾经满怀期待,不远千里去赴一场美好的约期。然而,这美好的期盼,却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一夕休”,三个字,干净利落,却也残酷无情。所有的希望,所有的憧憬,都在这短短的一夜间破灭。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变故,诗人没有细说,但那份失望与痛苦,已然溢于言表。
“从此无心爱良夜”。这是诗人情感的宣泄,也是一种决绝的姿态。经历了这样的打击,诗人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失去了兴趣。连“良夜”——这本是情人约会、诗人感怀的美好时光,在他眼中也变得索然无味。心已死,情已绝,再美的夜色,也无法再打动他。
“任他明月下西楼。”月亮,在古典诗词中,常常是相思、团圆的象征。但此时,诗人对月亮也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冷漠与放弃。“任他”,随它去吧,我不在乎了。明月也好,西楼也罢,都与我无关。这是一种近乎麻木的绝望。当一个人对曾经珍爱的事物都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时,他的心,该是受了多大的伤害啊。李益的痛,是希望彻底破灭后的心死,是对世间美好事物都失去感知能力的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