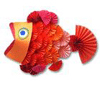如若我们光从概念上去说视觉思维,困难很大。有关“视觉思维”的书已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我们如何择取?何况,我们早过了读书的年龄,还想把知识台阶往上搬一步么?我想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诚然不错。但读书这件事,如说用在“活到老学到老”这句俗语上,那我只能理解为只是为了渡日戒厌气而已了,与混在麻将馆里唱和分别不大。如今,大家讨厌凭口白话说道理。当然,从哲学的角度去看,这样做在某种语境之下总含有一个目的。这个我们就不去管了。
端起相机,往往给人的感觉,就是摄影练功。这样,我们就很少去在意拍的内容。记录却从相反方面去看待摄影,相机成为一种摄取场景资料的手段。尽管很多人依然在怀疑一张照片的客观真实性有多少,但它还是被认为有文字所替代不了的功能而被普遍接受,而且,在很多方面的确比文字记录要可靠的多。如今,除了确认图片视觉比文字更直接且先入为主之外,我们已把它当作主要的阅读方式了。
这里,想谈的是摄影者在摄影行为中与被摄影者所发生的交互运动,这种动态活动与简单摄入有很大出入。场景从确定性转入对未来的不可捉摸。诚然,我们可以说,拍一个人物是确定的,他的表情不确定性刚好给了我摄取的机会。摄影者也可引导他的表情和行为,导演场景。此时,照片就成了摄影者主观的东西了,或者说,摄影者通过一张照片表达了自己一种态度。这态度也就因人而异。这样,照片纪实就不再置信不疑。
的确,当代摄影,由于更加特出摄影者主体性,强调艺术,反映论则留给新闻报道。这些老话不是我们现在所感兴趣的。
倘若过去注重摄影的结果如何,现在我们更愿意去体察摄影活动过程将会呈现何种未知的艺术原素。这样,摄影者的地位便降下来,他同样成为这个过程中的活动原素,与摄影对象发生相互作用(比如,如今男女之欢早就不再是男人单方面的乐趣了,这个变化是由平等互助现代观念所决定的。)从而,在这个活动场所里,真正的摄影原素或符号出现了,且如波浪,变化莫测。即时场景呈现的思维不用(不在)思考,相反,思考反而会造成视觉耽搁自身的活动,导致活动分子停顿或中断,遁入理智思维模式。这种情况下,思考在现场有可能成为视觉活动的障碍物。我们深有体会,现场拍摄并没有想的那么多,检片时却意外惊喜。事实上,视觉思维在现场拍摄活动中,很难意识到,似乎先于理智在场了。
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爱好的视点,它们与他(她)天性和后天学历经历相关。因而,在经过一段时期拍摄练习之后,这些先天的因素会渐渐浮现。大多数人并不重视这一点,去回顾和分析所看到的东西,理出原素,进而纯化,故而不再前进,难成艺术。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以下这组照片的实际拍摄过程。
那日天阴近黄昏。我走出AT CAFE,打算结束这天798影像的记录活动。出了AT CAFE,前面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往左转便是“798”路,一直往外走,就出798工厂了。就在此刻,前方往706工厂去的马路左边,地上坐着一群民工。于是,我没有转弯,径直走过马路。走近民工时,他们身边走出一个女孩,往我这边走来。我立即端起相机按下快门,此时她已走到跟前。
“喂,等一下,你可以坐在他们中间让我拍张照吗?”我手指那群民工,赶快把相机单色转为色彩。
“刚有几个人也拍了,说好给我的,可拍完就走人!”她看了我一眼说。
“不,我可是个守信用的人,保证给你!”我赶忙说。她转身回到民工中间。
这段对话陈述了以下这次活动这样一个事实://我提出建议,她愿意,民工不拒绝。//
第二张拍完,上述事实成立。
我不舍此景,想靠多拍从中取舍,便自然会延长那个女孩坐在那边的时间。其实,我的技术就那么点,加上套机镜头短,纵有九头六臂,也难有回天之力。不过,这个当口,竟有意想不到的事悄然而起。我们可以从第三第四张照片看到当时现场所发生的一切,我毫不迟疑按下快门。
这两张照片证明://当时有两个民工积极参与了这场活动。而这件事我事先未料。民工从被动转入主动。//从中我们不乏看到,俩人相争,事后一人稍有失落及另一人略显得意的场面。
拍摄本应就此结束。我卷起带子,把相机放进包。女孩走过来。此间,我身边观者很多,转眼看到两个男人在用心瞧我。
“你走到他们身后,再来一张!”我冲着女孩说,回头赶忙又对那两个男人说道,“就这样子,站着别动!”我拿出相机,对镜。“对,并排不错,俩人再分开一点。”说着,我按了几下快门。
当时,我确实有点紧张,不知他们会如何反应,本能的焦虑起来。还好,他们非常乐意,很配合。于是,我胆子大起来,继续让他们按我的主意再拍一个景。因为,我低头看到一堆细沙,堆放的尖,非常动人。我给戴墨镜的家伙做了个示范,他马上领会了。显然,此景之前早就有了存档,此时脑海闪现出来。这叫做触景生情吧。
第五第六张现在看来,的确使这组照片有了核心力量并且作为中间环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玩沙游戏”的后果将使其中一个男人出局,与最后一张照片绝缘,这不能不赞他们俩接受挑战决一雌雄的勇气。我要说,当时,我为何要拍这二景根本没考虑到这个结果,只觉得这样拍很有意思。人们可能不会相信这一点,但它是事实。我没有颠倒整个拍摄程序,把后面的片子编辑到前面去,尽管我把不好的删除,最后留下七张。
增拍最后一张是因为那时始终坐在原地不动的民工在我眼里瞬间突然多起来了。我便干脆叫女孩做好事做到底,回到那边坐下,让我再拍一张。她没话走了过去。但我没叫那个墨镜先生也一块过去,他却大摇大摆跟了过去。
他们坐下后,我察看一下情景,觉得队形呈两个半弧状态。我走过去,叫女孩走出来,坐在前面,并把她垫在身下的一只白色塑料袋抽去,扔到一边。接着,赶快退出来,对镜按快门。我回忆不起,那时我有没有在意墨镜先生就在她身后。现在想来,纯属天意了。因为最后这一张使本组照片前后相扣有所看头系列成立。我把这组放在“精神支柱5”栏目的最后,作为这一栏结束语。
这组照片拍的好坏这里并不重要,但它陈述了这样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参与者包括摄影者本人在精神上都有某种需求。那么,这组照片的观者呢?
附图:现场拍摄过程(二)
1
2
3
4
5
6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