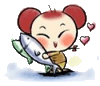——关于当前宋史研究的一点浅见
张邦炜
近40年来,宋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是个不争的事实。常言道:“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尽人皆知,良好的评论机制是学术进步的动力。本世纪初,包伟民等一批宋史学者力图掀起一股自我质疑、集体反思之风,有《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一书问世 [①] 。虽然引起重视,但风声还算较大,雨点似乎较小。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积习难改,有的学者近年依旧感叹:“学术评论之难”,“许多学人不愿意从事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②] 。愚见以为,当今宋史研究确实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主观片面性便是其中之一。问题虽属浅层次,但不可小视,最难防避。前辈史家翦伯赞生前所著《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且针对性极强。《初步意见》一文几乎通篇讲的都是如何避免片面性、防止简单化。翦老强调:“全面看问题是我们写历史的原则”,“必须用两只眼睛看历史”[③]。当今宋史研究中主观片面性的主要表现或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下面仅粗略举些实例。
其一,各走极端。宋代“积贫积弱”论与“理想社会”说、士大夫“高尚”论与“龌龊”说、富民一概“为富不仁”论与“社会中坚力量”说,看似针尖对麦芒,其实都是各执一端的偏颇之论。从总体上说,宋代士大夫既非纯属一堆肮脏龌龊的粪土,亦非个个都是品格高尚的谦谦君子。笔者尤其不赞成宋代“富民是主要纳税人”一说。众所周知,传统时代的分配体制是:佃户交租,田主完粮,粮从租出,租为粮本。田赋分明是地租的分割,田赋来自地租。不能把劳苦大众排除在外,片面地将富民视为宋代社会的中坚力量。翦伯赞当年告诫我等:“不要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而今我们怎能见士大夫就反,见富民就骂?反之,也不能见士大夫就赞,见富民就捧吧!这些,笔者在《不必美化赵宋王朝》 [④]等文中曾言及,这里不再多说。为了表达对宋代农民欢乐说不予认同,我曾较多引用钱钟书《宋诗选注》中反映农民疾苦的诗篇,诸如《前催租行》《后催租行》等等,于是被视为宋代农民苦难论者。《选注》编写于上世纪50年代,受到时代与体例双重局限。如今我们肯定可以从72册之巨的《全宋诗》中找出若干反映农民欢乐的诗篇,而且数量不会太小。然而宋代农民绝非时时欢乐、人人欢乐。丰年多欢乐,灾年很痛苦;形势户、上户欢乐多,下户、客户苦难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前代相比,宋代农民生活确有改善。但对宋代农村不能理想化,绝非处处充满欢声笑语的美好田园。宋人程颐有句惊人之语:“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以致从前人们普遍将宋代视为妇女社会地位急转直下的时代。笔者30年前撰有《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 [⑤]一文,认为宋代妇女再嫁者并不少于唐代,旨在说明宋代妇女社会地位处于下降的过程之中,而非急转直下。或许与此有关,于是出现宋代妇女幸福说:“做宋朝的女人是相当幸福的。”宋代妇女再嫁多,显然不能引以为据。传统时代,妇女另嫁绝非幸福,往往悲痛欲绝。听听宋代一位“弃妇”对亏心汉的声讨:“功名成遂不还乡,石作心肠,铁作心肠!红日三竿懒画妆,虚度韶光,瘦损荣光。” [⑥] 那位为赋税所逼而被迫改嫁的老妇,更是“行行啼路隅”,“欲死无刑诛” [⑦]。我当年将妇女再嫁与社会地位联系起来一并讨论,虽然事出有因,现在看来有一定的片面性。
其二,只知其一。任何社会都是个复合性的整体,总是死的抓住活的,新的旧的同在,多种现象并存。我早年所著《试论北宋‘婚姻不问阀阅’》一文 [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