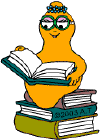策划 | 杜扬
策划 | 杜扬
采访、撰文 | 陈樱丹、丁彦心
今年三影堂摄影奖开幕的当天,北京五环外的一块儿草地上,集合了一群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他们会一起见证第九届三影堂摄影奖大奖作品的揭晓,同时,此次入围的作品也将第一次与大家见面。
 三影堂创办者荣荣在过去的采访中曾表示:“其他的任何展览都可以不做,但是如果三影堂摄影奖不存在的话,那么三影堂也就不存在了。”
三影堂创办者荣荣在过去的采访中曾表示:“其他的任何展览都可以不做,但是如果三影堂摄影奖不存在的话,那么三影堂也就不存在了。”
站在这块飘散着艺术气息和漫天柳絮的草地上,我们听到也参与过了太多有关艺术的分享,这一次,我们准备聊些不一样的。
下午3点整,大奖准时揭晓,本届摄影大奖花落艺术家良秀,获得奖牌及8万人民币奖金,张之洲获资生堂优秀摄影师奖及奖金2万人民币。(本届作品由评委团成员西蒙·贝克①、冯博一②、蜷川实花③、荣荣④、托马斯·鲁夫⑤共同选出。)

三影堂是国内首家民间专业摄影艺术中心,由它创立的摄影奖旨在选取具有独立精神和艺术潜质的艺术家及作品。
我们顺着人潮涌入了展厅,浏览了一遍参展作品之后,开始好奇:布这样的展,需要耗费多少精力和财力?
于是,我们试着不拘泥于理论和意义,更多地从“动手”的角度,跟这些摄影师们聊聊布展过程中“鲜为人知”的那些事儿,尝试以更直接的方式,去了解这一场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的展览。
但问题来了,如何在众多的观展人群中寻到作品的作者?我们咨询了一位曾经入围三影堂摄影奖的“老艺术家”,他说:“作品旁边最有表达欲望的那一个。”
于是,我们随机锁定并迅速找到了这几位摄影师:
“做照片大概用到了假纸”
做照片大概用到了假纸,很便宜,一千块钱吧,加上装裱的话一共两千多块钱,mp3买得特别便宜,被偷了也没关系的。

这是一组关于恐怖主义和非人道主义袭击的作品。除了冰冷的伤亡数字,对于天灾人祸,我们能了解的其实还有很多。
何博选取了各事件中受害者的头像作为基本元素,以拼贴的手法整合事件加害者的肖像,肖像上覆盖着受害者的嘴部特写,它们构成了一句与事件相关的话语。并以摩尔斯码形式呈现。展览现场的耳机设备辅助观众理解图像中密码所示的内容。
我们每天都被爆炸式的信息包裹着,这些信息里面包括了日复一日的天灾人祸,而我们已经习惯于每天面对变成数字的死伤者,这也应了苏珊·桑塔格多年前的论断——苦难的照片让人越来越适应,越来越麻木。
所以,何博试图在经过他作品的人中寻找那些愿意停下脚步,借助规则、图像、密码和音频重新与这些死者(包括死去的凶手)建立沟通的“少数派”,即便这种沟通依然是暂时的、浅表的。

——何博,作品《从此没人和你说话》
“最贵的就是照片了” “布展大概耗时为7天。”
我在美国上学,照片都是在美国输出后带回来的,整个作品的成本可能要8000块钱。最贵的就是照片了,照片印刷用了非常好的纸,带有细致纹理,这样会使皮肤的纹理会非常清晰。
展览中红线的装置是由三人完成的,把照片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工作是由六人完成。悬挂的照片是一个整体,需要两个人站在梯子上同时作业,剩余的人要托住照片,保证照片不会有折叠。
这是一组完全用“红线”联结的作品。
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的复杂性和强制性,还有它们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的形成,促成了王佳的艺术选择。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关于月老的传说:他用一根红线将男人和女人系在一起,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家庭。在这个作品的表现中,家庭作为一个个的点,红线作为关系的连接物,在家庭繁衍的过程中,家庭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如同交错复杂的红线。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关于月老的传说:他用一根红线将男人和女人系在一起,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家庭。在这个作品的表现中,家庭作为一个个的点,红线作为关系的连接物,在家庭繁衍的过程中,家庭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如同交错复杂的红线。
摄影师王佳想通过作品去表现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把平常说不出来、看不见的东西转变成可以被感知的实物。把家庭关系这种非常私人的事物以公开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并试图与观众产生共鸣,是作品想要塑造的效果。

——王佳,作品《家·叙述》
“花费最多的是运输和制作运输箱。”
如果算上制作、运输和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成本大概在6000块钱左右。花费最多的是运输和制作运输箱(笑),作品是订做了一个大的运输箱送过来的。
 这是一组以“世界末日”为核心命题的作品。
这是一组以“世界末日”为核心命题的作品。
我们离末日究竟有多远?2015年1月22日,由芝加哥大学的《原子科学家公报》杂志于1947年设立的“末日之钟”被拨快了2分钟,距离“象征世界灾难末日的”午夜时分仅剩3分钟,这也意味着人类面临的生存威胁上升到冷战结束后的最高水平。诺斯特拉达穆斯的“1999年7月世界末日”预言曾让亿万人心神不宁。如今,1997年已经远去,但我们是否就此太平?从冷战到最近作出的一个个末日预言,诸如大陆陆沉、文明消亡等。现代的人们一直都处在旷世浩劫的阴影下。无论后人将怎样看待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都堪称一个焦虑的时代,并且我们今天要比过去的半个世纪承受着更为泛滥的恐惧。
这是一个多媒介的作品,胡兆玮认为,单单靠摄影作品去呈现不够完整,比如地球仪本来是拍摄的照片,但最后在展览中以实物的形式展出,使得它能够从图片的二维平面里面跳出来,能够让观众看得更直接,也能帮助观众更进一步了解作品想表达的意图。
——胡兆玮,作品《23:47》
“所有人的劳动都要付费的”
整个作品连上书、音频的话花费了将近3000块吧。花费最多的应该是画这个地图吧,是朋友帮忙画的,他不收钱,但我还是给了钱,因为所有人的劳动都要付费的。
 这是一组自带图片定位功能的作品。
这是一组自带图片定位功能的作品。
王攀用了一座城市的地图轮廓来存放照片。城市的轮廓属于临潼,那里有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兵马俑,它背靠秦岭的支脉骊山,脚踩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水,照片所贴的位置就是拍摄照片的区域。
王攀想要叙述的是他跟这片土地的关系,也是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之间的情绪。而像王攀这样的人在中国还有很多,他们如王攀一样远离了故土,怀揣着复杂的情感背井离乡,这种情感也许是仇恨也许是思念,但说到底,这些都是离家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
——王攀,作品《小城碎戏》
当我们谈到“撤展”这件事……
从精心准备展览作品,到亲自参与展区布置,再到最后在作品旁看作品与观众产生反应,这样的过程,是漫长却值得期待的。
此次三影堂的作品展览活动将持续到五月底,这段时间里,还会不断有观众来到展厅内,参观由多位艺术家布置的展厅。而一个月之后,这里又将一点点褪去喧嚣,或是迎来新一批的展览作品,或是保持一段时间的空旷宁静,这样的过程,对这些艺术家来说,却是残忍又稍带痛苦的。

“在整个撤展的过程中,都是很失落的。因为这个创建的空间以及作品对于我来讲,是建立了一个我与我的家人,我与我自己能够进行平和沟通,并且能够安抚我们的一个空间。所以,看着这个可以提供抚慰的空间被一点点的拆掉,是很失落的。”
——王佳
 “我自己尽量不参与撤展的过程,我喜欢顺其自然的结果”
“我自己尽量不参与撤展的过程,我喜欢顺其自然的结果”
——王攀
这种从期待到兴奋,再从失望到平静的过程,是艺术家们每参加一次展览都会经历的循环。何博说,通过经历这样的过程,更多体会到的是一种身份的转换,从一个纯粹的旁观者转变成“参与者”和“观赏者”的双重状态。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浸入一个事情的同时,让自己尽可能地“跳出来”去观察、体验和思考,会比纯粹的旁观更加全面和客观。
作品会随着展览漂流。摄影师们,则会继续带着他们想法重新上路。
但我们知道,展览永远不是终点。
①西蒙·贝克(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摄影和国际艺术高级策展人。
②冯博一(中国),自由策展人、美术评论家、何香凝美术馆艺术总监。
③蜷川实花(日本),摄影艺术家、电影导演。
④荣荣(中国),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创办人及总监、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联合创始人及总监、摄影艺术家。
⑤托马斯·鲁夫(德国),德国摄影艺术家。
*本文首发于图虫网【摄影书房】,转载需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