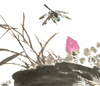李犁:本名李玉生。上世纪八十年开始写作诗歌和评论。2008年重新写作,评论多于诗歌。出版诗集《大风》《黑罂粟》《一座村庄的二十四首歌》,文学评论集《烹诗》《拒绝永恒》,诗人研究集《天堂无门——世界自杀诗人的心理分析》;有若干诗歌与评论作品获全国和省政府奖。任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副秘书长、辽宁新诗学会副会长、《深圳诗刊》执行主编,《猛犸象诗刊》特约主编。
关于诗的情感、思想、技术和本土化
——著名诗歌评论家、诗人李犁先生在第七届扎龙诗会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
李犁
非常荣幸参加扎龙诗会研讨会,刚才大家发言我听的很激动,因为我参加研讨会很多,北京、广州、江浙等地都有,很多金碧辉煌的会场,但是从发言的态度上看,咱们是最好的,都准备了发言稿。很多研讨会上,很多人讲的基本都是一样的。不是没有水平,而是态度没有我们在座的好,没有我们对诗歌的这种敬仰、敬畏、虔诚。我们的发言都非常完整、系统,让我非常感动。我是在龙江县读完中小学、在克山师专学习,然后回到辽宁。我的受教育时期都在齐齐哈尔。过了五十,心就变得有点儿脆弱,无论多忙,每年必须得回来一趟。今年到齐齐哈尔是两次。从黑龙江来讲,绥化的活动最多,我一年能去两次,哈尔滨能去两次,其他地方偶尔也去。来齐齐哈尔参加这种全神贯注谈诗的会还是第一次。大家说得都很有水准,而且现代性都很强。扎龙诗会做了七届,怎样把它做得更大、在全国能有影响力,我想可以把奖做得更大一点,可以叫“扎龙诗会征文奖”、“扎龙诗歌奖”,全国范围评,两年评一次,请全国著名诗人、评论家组成一个评委会,让他在全国推荐,可以列个主题写自然的,写鹤的,写天空白云的,总之环保的。每两年评两位诗人,没钱不要紧,可以做一个廉洁的奖,不给奖金,可以找画家赠送一幅以扎龙为背景的画,丹顶鹤什么的。找合作单位如“中国诗歌万里行”、“全国诗歌网络报刊联盟”等,跟他们联合颁奖,可以在中诗网上设常规专栏,就叫扎龙诗会,这样传播得就更广、做得更有意义。
至于诗歌写作的现状,我觉得正在走向共和,无论是知识分子、民间、口语、叙事等,界限越来越模糊,互融性、互助性增多,包括知识分子写作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他们也用口语。口语者们的诗里也有很多比喻、形容词。现在整个写作就是各种流派互相包容,各取所长、共同生长。我个人觉得诗歌应该越来越简单越直接越透明越好。就象金庸笔下的剑,刚出道时是青铜剑,刚猛、锋利,且金光闪闪,锋芒毕露。到三十岁左右是紫薇软剑,剑体渐渐变软,锋芒稍隐,削铁如泥,在向前,接近四十岁时使用的是玄铁剑,重达七八十斤,剑锋已钝,曰“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在五十岁的时候,使用的是一把腐烂的木剑,其文字说明为“四十岁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自此精修,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重在无剑胜有剑,这时重在剑术,而不在工具,或者说人剑合一,简练直接。这个过程的剑就是收敛锋芒,也不再追求表面的锋利,浑然朴拙,大智如愚,大道至简,最后变成随心所欲。把它弄得诗上就是真诚、简单、朴素、自由。也就是说能脱口而出的诗,肯定是最好的。冥思苦想的,毕竟有痕迹。我们能记住的各种流派的金句,往往是顺口说出来的。所以流派不重要、主义不重要、方法不重要,重要的还是真正的能达到一语中的,看似漫不经心却能一剑封喉。这就是最大的技巧。
真正的好诗,第一是情感动人,看了之后能流泪。有一个女诗人颜梅玖,写过一首《哥哥》:“你说你恨极了我高傲的样子/哥,不是我有意抬高视线/哥,我一低头/ 眼泪就流出来了”这就是顺口说的,感人的东西没有是冥思苦想、日思夜想的那种。还有余秀华的诗“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这是她丈夫打她的时候她说的话,把它写在纸上就是最好的诗。黑龙江的诗人能把诗写得朴素又最能感动别人的就是李琦。她的诗里没有那么高的技巧,但读完之后都能被其中的真情感动。所以在情感最激烈的时候是不需要技巧的,因为情感最激烈的时候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有力量,都是心灵上刮下来的血肉,肯定会打动别人。这也说明真正的好诗肯定是有感而发。但作为一个职业诗人,有感而发很难做到。象王长军老师,要写诗就每天在琢磨,观察每个细节,都能深思,但此时只是心动而已,没有达到那种感情冲击,让你哭、让你笑。如果在你最痛的时候,没有技巧诗句也能动人,而且技巧会自动产生。所以感情动人的好诗应该是人心、人品而不是技巧。
还有一种好诗就是思想扎人。有思想的诗特别有锋芒有力量。诗中对世界的认知、概括的非常准确而有力量,饱含丰富性复杂性深邃性等等,这样深入骨髓的诗也不需要技巧,但能震撼人心。辽宁有一个诗人刘川,他也是口语。他把一人间的这些事儿弄得非常深刻。他最著名的诗是写孕妇:“她们体内的婴儿/都是头朝下/集体倒立着的/新一代人/与我们的方向/截然相反/看来他们/更与我们势不两立/决不苟同/但我并不恐慌/因为只要他们敢出来/这个世界/就能立即把他们/正过来”。其中的哲学性、深刻性,显而易见。每个人生下之初,本性都是理想的、干净的,但活来活去就都一样了。自然人都变成了社会人,世俗的强大力量中有人的无奈和无能为力。这种哲学性的诗不需要技巧,但谁能发现它就需要功夫。所以这种有思想的诗更需要诗人自身的深刻和丰厚。
还有一种好诗就是技术惊人。不论你是哪个流派,哪个主义,只要技术上有创新有独特的发现,让人大吃一惊,哪怕只一个比喻句,就是好诗。技术的最高层次就是无中生有。我们常规说到的好诗虽然也有技术,但都是想象之中的想像力,这不行,只有超出常人的想像力的诗才是最好的,就象有东西砸在头上,让你震惊并幡然醒悟:原来诗可以这样写!这就是给你洗脑。这样的诗的最大贡献是给人的心智向远处推进了,哪怕是一厘米,也是一种贡献。但也有一个弊端,就是由于技术太惊人太神太玄,让其中的情感和思想变得太隐蔽,很多崭新的真理就这样别忽视了。所以最高妙的技术是让人感觉不到技术,又能让其中的情感和思想更迅疾地走进人心。这又回到了无剑胜有剑上来了。但不容忽视和抗拒的是,技术主义已经又成为一种潮流。谁能在技术上操练得前所未有可能就成功了。
我个人觉得技术主义必须也必然要改变,技术主义的诗歌里必须要掺进情感和思想,而且要要更直接彰显后者。否则技术主义就会导致诗歌越走越狭窄,读者越来越少,诗歌成为一种学术化的东西。想想当年口语叙事以及下半身的发生,就是当年对技术走到极端的一种反抗。再有七八年诗歌还是会回到九十年代初,读者越来越少,诗人越写越费劲,这样才出现了口语、下半身什么的,其实下半身就是当年对技术走到极端的一种反抗。我个人主张诗歌本土化,并以此来修正过分和过于神玄的技术主义。本土诗学的作品大都是短平快,深入浅出,大道至简至浅。这样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更难。去年我写过一篇《呼唤和重建本土诗学的精神和特征》,《诗刊》发表后,台湾一些学报都转载了,作家网上转载点击率超过200万,这说明大家对本土诗学还是很渴望和期待。本土化的诗歌我总结就是要大爱、大我、大动、大说,具体就是写有情有义的诗歌,在行动中而不是在书斋中获得写作的灵感,写能用言语说出,且一说就能听懂的诗歌。如果技术主义能把以上这些原则作为技术的目标,那技术主义就成功了。情感感人、思想扎人、技术惊人其实就是本土诗学的具化,当然这三者不是隔离的,而是融合在一起。情感是传导器,思想是价值观,而技术就是彰显并融化前两者方法、熔炉和助推器。
(李犁:著名诗歌评论家、诗人,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副秘书长,《中国文人书画》杂志主编、《诗歌地理》主编。)
李犁:好心肠让诗人对万物肝胆相照
——王文军与大路朝天诗歌述评
本期两位都是辽宁的诗人,也是我的兄弟。在阴阳怪气众多的诗人乃至文人中,这哥俩犹如夏日的阳光,以明亮和炽热让人感到舒坦和温暖。这是两位有心肠的诗人,赤子之心和古道热肠。我见过太多的聪明过人和才高八斗的诗歌才子,但他们终没成大器,就是缺少一副好心肠。好心肠就是侠骨柔肠,它让你对万物肝胆相照,对弱者拔刀相助。所以我看重这俩哥们的心肠,就是再次强调情怀,也只有诗人的情怀才能对诗歌拓宽和提升。这让我想起《菜根谭》中的几句:“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鲁;与其曲谨,不若疏狂”。这就是说,精明圆滑,不如朴实笃厚;谨小慎微精雕细刻,不如坦荡大度。前者是自然,后者是自由;前者是天性,后者也可修为。对比这两位诗人,王文军多一点笃实,大路朝天多了些豪放。这好心肠加之个人的性格元素让他俩的诗歌本质一致,但风格和方式却明显不同。
“朴鲁”反映在王文军的诗歌里就是抱朴怀真,“鲁”在他的诗歌中体现为没有被开发和破坏的本真,并非是笨拙和粗糙,相反他的诗歌却很机敏和灵秀。比如他的这两句诗:“如果你累了,就看看我吧/看我眼中的泪水,比月光还亮……”。这如露珠一样清凉又透明的诗句折射出文军的机智、细腻和婉转的心。所以朴鲁是文军骨子里的东西,是他的朴素和纯真。这让他的写作一直没有离开乡村和田野,故乡和亲人。这不是写作上的策略,更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文军的身体和心灵始终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着,他笔下的河流、树木、白雪和乌鸦都是他正在经历的生活。这纯美的风景不是他的回忆,更不是他的梦幻和精神的乌托邦,是真实的即时的正在发生着的现实。在他看来,大自然和亲人才是生命的根本,也只有这些纯朴的没被破坏和异化的人与物才是诗,才是人性中最美最永恒的品质。这让他的诗歌与这些不与时俱进的风景一样显得淡远和古朴,又真切而永远地拨动人心。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根,触及了它就等于捅碰了人类敏感的神经和情感的泪腺。
正因如此,王文军的写作有了向生活的本源和艺术的本质回归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把文军诗歌称之为环保的诗歌,绿色的写作。这也是当下呼吁的慢生活的一种。在王文军的诗歌里,不仅慢还有轻和静。譬如他写山溪:“它清澈得/好像没有一样”,而羊肠小道:“一会儿被杂草吃掉/一会儿又被荆棘吐出”。读这样的诗歌就像瞭望家乡上空袅袅上升的炊烟,淡远而宁静,而胸中却有雷霆在轰响。而当情感的潮水退去,留在心灵上的是至绝的净和静,犹如文军写的“旷野无声,白茫茫的一片”。这是实景,更是他心灵之境的外化和具象化。这一实一虚,让诗歌有了意境,有了让人仰望的高格。对诗歌而言,就是清澈和澄明;对诗人来说,就是超拔和升华。而这一切,都源自于文军的心灵在写作的瞬间轻轻地向上一跃。
所以我们可以把王文军的诗歌称之为“轻”的写作,轻一是说王文军写作的状态不咬牙切齿,不冥思苦想;轻二是说王文军诗中没有浓妆艳抹,更没有呼喊尖叫,整个过程都是轻描淡写,犹如素描和白描。轻三是说他不追求重大的意义和思想,而是让诗歌轻轻地飘起来,直飘到凌云处,成为一种让人敬仰的境界。从审美品格上来概括王文军的诗歌就是冲淡,即朴素清淡中散发着自然的气息,而这气息也是向上冲的,能飞多高,取决于诗人的心肠以及时时刷新的感觉、思维和技艺。
与王文军诗歌的“轻”比,大路朝天追求诗歌的重量,也就是诗歌的意义和思想。如果用一个审美品格来衡量他的诗歌应属于实境,就是在实际的事与物中敲打或抠出与之对应的意义来。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他的内心有着对世界无限的看法,平时这些思想休眠着,一旦与一些事物相遇,这些生活中的实景就勾出了他的人生以及对万物之思。所以他的诗歌实而重。实是指他不写那些虚幻的东西,重是说他的诗歌承载了他太多的经验和思考。譬如:“那只精灵的藏羚羊/在发现枪口和雪豹的一瞬/闪电一样跃起来//那些修行者/努力平息着身体里的电/下意识地隐居林泉/把自己变成食草动物/他们洞明披着人皮的社会里/那些四伏的虎狼之心(《作一只动物是多么不容易》)”。我认为这是大路朝天写的最好的一首诗。首先说修行者是把自己变成了食草动物就是一个新的发现,发现即诗。所谓诗人的创造也就是发现出人意料的发现,如此而已。这是好诗的基础。而在独特的发现中放进了深刻的思,诗歌就有了力度和高度。人为了剔除和回避恶而通过修行变成动物,而动物同样活得捉襟见肘,无缘无故地遭遇枪口和危险。这就直接思进了人和动物的命运和本质中去。这思是诗中的镭,微小几近于无,但爆破力足以让读者目瞪口呆。
有重量的诗歌视角都是向下的,一直扎进大地之中,扎进生存生命的根本和哲学里去。但是大路朝天的表达却是非常的轻松自如流畅,没有生拉硬扯和牵强附会。这是他的个性使然,也就是前面说的“疏狂”的效果。疏狂表现在他的性格中就是坦荡和豪放,犹如大风在原野上铺开,广袤而浩荡,摧枯拉朽也泥沙俱起,这让他的诗歌既有力量也显粗粝。粗粝反映在这组诗歌中就是有点粗糙,许多地方似还可打磨。粗粝的优势是让这些诗歌拉得很开,思维和意象之间跳跃得很自由,比如他把月光切成片,“这一片是李白的/这一片是王维的”,竟然还有“唯物主义的”。这就是他性情之疏狂带来的不羁与超常的想象力。所以大路朝天是一个举重若轻的诗人,很多重大的重要的题材他捏把捏把就变得轻松和愉悦,这让增加了他诗歌趣味性和鲜活感,让人在这个密不透风甚至有点窒息的时代感觉到清风和流水。所以大路朝天的诗歌像他的名字一样奔放大气,有丝丝不悦和孤寂也被他的坦荡所稀释,这就是诗如其人。所以大路诗歌的价值就是让诗歌走下神坛并兄弟化。当然在平常甚至嘻嘻哈哈的下面是他的炭火和暗器,前者是诗人的好心肠,后者是诗歌的批判精神。
世界上只有读诗才愿意从中读出“人”来,希望通过诗歌见其诗人的精神和品格。也只有诗歌才能凸显出诗人的性情,或豪爽或闷骚或其他。本期作品透视出两位诗人的共同点就是好心肠,这是成为大诗人的硬件。当然硬件不仅这一个,还需要同时具有天分和技艺。对这哥俩来说,前两者不是问题,唯一需要锤炼的就是诗歌的技艺,当技艺化成他们自身的素质,他们的写作将会走得更远更高。
李犁:用诗承受生命之空和重返故乡
6月4日傍晚,在北京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旁边的上岛咖啡屋,我和来自云南、湖北、河北还有几个北京的诗歌大腕闲聊,其中一位嫌咖啡太淡,于是改喝啤酒。酒至半醺,云南的哥们说:中国女诗人我最看好玉上烟,她的视野越来越广阔,也越来越有冲击力。湖北的朋友急忙附和,但最后说:她的态势很好,但是最近网上那些写器官的诗有点不好。云南的朋友立马反击说你不懂。于是两个人吵了起来,我和北京的一个诗歌大腕急忙出来拉架,但云南的朋友还是很激烈地说了一番诗歌不要有禁地,应该允许诗人们探索等等,说完把啤酒瓶子狠狠地摔在地上,扬长而去。
这是一个不太愉快的聚会。但仔细想来因为诗歌观点,兄弟间剑拔弩张以至于伤了和气,还是很好玩的,至少让我感觉很多诗人对诗歌心存真诚和敬畏,在这样一个急功急利的时代,有人还能为一无所用的诗歌大动肝火确实让人感概也感动。回到家我上网把玉上烟这些写女性器官的诗歌找出来,看看是什么原因让两位兄弟同室操戈呢!
我仔细看了玉上烟这几首写女性身体的诗,我想说的是这两位吵架的兄弟可能都没认真看,因为两个人都没有说出作为正方或者反方的理由。盲目和想当然是我们很多诗人和卫道士的坏习惯,听了一句敏感的词语就立马有了结论,这是造成很多好的诗歌受到谴责的原因。玉上烟是写了女性的器官,但是一点都不下流,读完之后反而感到有点凄凉。因为在她的诗里,这些器官不过是一个说事的媒介,一个符号,而且她并没有多在这些器官上掰扯,而是写有没有这些器官,几个女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也因为这些器官,几个女人的生活被捣得七零八碎。玉上烟是通过这些器官在写社会的千姿百态,写人情的厚薄冷暖,其中有浓郁的人道关怀和对不公不义的批判。而我们的诗坛似乎确实有点太敏感也太正统,看看莫言那些小说,有些细节已经远远地拉开了诗歌的距离,要是让这些诗歌的掌权者来当他的责任编辑,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可能早就被掐死在萌芽里了。
我觉得玉上烟从这些诗开始,突然有了一个飞跃,就是她的视野一下子打开了,并且诗歌越来越锐利。虽然还有破绽还不圆润,但是其冲击力让我们震惊也让我们摇撼。这就比很多诗人写了好几十年诗,从技法上你无懈可击,但是读起来就是犯困,这不温不火的状态就是一种亚死亡,就是死不死活不活的植物人。而且继这些诗之后,她的又一批新的视角新的态势的诗歌诞生了。
我们看到她的写作较之以往更自由更自然更从容更随意。像长江经过了三峡的惊涛骇浪之后,一下子进入到平原,有种辽阔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预示着她的写作也已经成广阔无际的状态。也就是说她找到了写作的泉源,以后想写什么,开关一拧就咕咕往外冒了。
这也标志着玉上烟由一个业余写手变成了职业诗人,由依赖经验和冲动进入到凭心智和发现的随性写作。因为在玉上烟写作伊始,诗歌只是她的一个泄洪口,她把堆积多年的情感向外倾泻,但是激情和冲动是靠不住的,一旦掏空,一旦退潮了写作还怎么维系?很多诗人的写作就死在激情过后干涸的河床上。但是玉上烟成功地越过了这个时期,这除了她的天资,我想肯定还会有大量的阅读在支撑着她扎实地往前拓进。玉上烟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大量的阅读,现在也在如饥似渴地学习,不仅是文学的,还有大量的哲学和美学著作。这不仅让她写作的根基越来越厚实,也让她的视野越来越广阔,更让她的思维和写作姿态和方法都始终站在写作的前沿。比如这期发表的这些诗,写得都是身边日常生活中的庸常事物,但是读起来却很有顿挫和节奏,这是蕴含在这些事物中的“道”与作者内心深处对人生的深刻体悟相谐和,再一层层有秩序地呈现出来。自然自动自发,像唠嗑也像喃喃自语,轻松自如,完全没有传统方式的正襟危坐冥思苦想甚至咬牙切齿。顺手拿她这首《它从不看我们悲伤的脸》为例:“一个人也能赌:用左手和右手赌/我喜欢让左手大行其道/于是暗中做了手脚/我把大小王分给了左手。意外的是:/右手居然赢了/重要的筹码并没有改变牌局/后来我把两张大牌又给了右手/这次,左手还是输了/卡在左手和右手之间的我/仿佛一条被扭曲的被单。这说明/“事物存在局限性,合理性和不确定性”/就像总与我们作对的生活/它从不看我们悲伤的脸。就在刚才/我得知一对恋人在大海里消失了/大海的浪花/不过暂时多了一点点”。
平静散漫。这是叙述方式,也是人生态度。但当你轻声或者默诵几遍后,一种深刻的冷会渗进骨髓,那是对人生刻骨的认识,还有同情和爱。这就是人生,非但不能掌控,更多时候总是走向愿望的反面,呼唤不能照应呼唤,而这一切又都那么正常,即使是再大的悲剧,也不过是让生活的浪花暂时多了一点点而已。作者的平静是因为接受这种残酷并无惧,也就是常说的看透了生活还依然爱着。这是一种乐观豁达的人生观,也是深邃的态度,但它们溶解在平常松弛的表达中和散淡琐屑日常的生活细节里。这里诗歌的边界似乎也消失和模糊了,就是说诗歌的形式看起来不像传统意义和教科书上定义的诗歌,这预示着诗歌从内到外都在发生着变革,这种写法与当下前沿写作态势呼应着,一齐向更前推进着。
基督教里有句名言叫“道成肉身”,这是说耶稣下凡降世道成肉身,然后替人赎罪并拯救人,道成肉身就是神借人性来示予人神性。那么引申为诗,就是诗成肉身,将诗意溶解在人的举手投足之间,包括日常的生活细节里,日常生活诗歌化了,诗歌本身也变成了肉身也日常化了,这就让诗歌与生活融为一体。所以我们在诗歌写作中看到了文体本身与生活化语言越来越融合,诗歌内容与诗人的境遇也越来越重叠。这就使诗歌变得很真实。玉上烟的诗歌就是她真实生活的反馈,那就是孤独与坚守,飘泊与坚定。我们都知道为了生存,玉上烟背井离乡,在孤独的飘泊中,诗歌就是她的情人,就是她的伴侣,每天对诗歌说话,也用诗歌说话,诗歌就是她工作外的全部生活。在异乡生命无法承受的不是重也不是轻,而是一种空,空落空茫,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或者是巨大的恐龙的嘴,这需要她不断的写作来填充。譬如她的《歧途》、《洱海之夜》,这种情感就很突出。所以写作对她来说,绝不是那种小妇人日子的锦上添花,也不是鹅绒枕头旁的闲愁絮语,而是命,诗歌就是她的命,是她的命运。所以她的诗歌里充满了疼痛感,这是心灵在抽搐,是她与命运抗争时的震撼和颤抖。更可贵的是她还能越过自己的苦难,将自己的孤独上升到同情别人的眼泪,这就让她的诗歌有了悲悯和情义。而在异乡,不论你怎么调整姿势,也很难有根的感觉,像她自己写的:“在异乡,我有浮云之感/在车水马龙的家乡,我也如过客/没有人注意到我/‘从歧途误入更深的歧途?’我点上一支烟/我有,从未有过的孤独(《回家》)”。
在异乡的浮云之感是孤单,在家乡还犹如过客就是孤独。孤单是有形的,是缺少同伴。而孤独是思想上的无伴,是心灵的空,是理解缺失,和呼唤没有呼唤来承接。这些她生活中真实的感受和体验让她的诗歌变得很沉实,像剑,没有凛冽的锋芒也没有刺眼的光芒,但是被它击中,你会有很钝重的感觉,甚至一命呜呼,至少长昏不醒。她用各种方式甚至是自戕的方式来摆脱这种孤独,但是孤独始终像热气一样笼罩着她,因为她本身就是沸腾的水:“我藏起身份,虎牙,可疑的言辞,新旧心事/在小酒馆喝得半醉半醒,把两条烤鱼喂了野猫/铺天席地的榕树下,我还抽出背包里的纸牌/占卜了下半年的运气/整个下午,我游荡在小岛上,像一个阔别家乡多年的浪子/慢走,快行,不管去向(《鼓浪屿》)”。我把诗人这种种的行为,看做一种抗争,与孤独与命运与内心中满满的空。孤独划伤了诗人的生活,却成就了她的诗歌,让诗歌被充足的元气充满,这也是地气,是生存之根发出的带有泥土的新鲜气息,是她心灵里撕下的血和肉。其实孤独是一种思想,是一种超然于世俗之上的高贵和先知,坚守孤独就是不沉沦,并努力从滚滚红尘向上一跃。而无家可归的感觉一百年前那些先知们就体验并开始寻找药方了。德国诗人哲学家荷尔德林对此有吐血的体验,他认为现代人的无家可归主要就是技术、功利、实用等把人的自然属性瓦解了,把人引离了故土,让人远离了人,那些原属于人的理想、神性、灵性都被遗弃,人变成实用的机器而不是人了。所以他深切地发出“还乡”的呼唤,也就是重返神灵,重返故乡和童贞。他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因为只有诗人才能激发人们去温爱,温爱那矜持温柔的人灵。只有这些虽然远离故土,却一直凝视、眷恋、光耀自己的故乡的游子,才能深怀执着的牺牲,向故乡的亲人们发出诗意的呼唤。从这个角度来说,玉上烟诗歌中的漂泊感和孤独感就是在寻找精神的故乡时留下的足迹和影子。但愿荷尔德林提出的重返神性和灵性对她也是一个良药,让她的诗歌和孤独找到方向和神灵。
而玉上烟自己开的药方就是写诗,在诗歌中发狠发飙,用极其残酷的方式来对待这种孤独和消解这种精神的异乡症:“作为一个每每像赴死的/过时的浪漫主义者,现在,我充满了喜悦/……二十年来,我坚定不移的,不过是/假象。现在/我一下就能喜欢上一个人/一下就能进入爱的身体/一下就能养出无耻无畏之心/一下就能忘掉一个人/一下啊,只一下就完成了爱情的全部(《爱情之远》)”。我想这首诗会启发那些好事者的想象力,编造出很多离奇的故事来。其实作者只是在表述一种观念,一种对付这个稀奇古怪时代的一种方式,“一下”就完成,这是快刀斩乱麻的方法,也是这个速朽速变时代的无奈之举。更多的是作者在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在自嘲和反讽。但这种观念和率真却成就了这首诗,让它饱满锐利并深刻和快速地直抵核心。同时这种决绝自由的态度也是人感性的审美解放,它驱动了人的创造力,并把人的灵性、激情、想象、智力、魄力等感觉力量显现出来(马尔库塞有过这方面的论述)。
我想在真正的好作品面前,一切鼓噪之舌都应该闭嘴。诗人之间较量的应该是手艺,你不服你就拿出好作品来。对于玉上烟来说,除了把诗歌当做一种瘾之外,还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和从容来面对一向就喜好无事生非的诗坛,把那些中伤和飞弹当做种种的传说和传奇,一笑而过。
在黎明的清水里淘洗黄金
——金所军诗歌印象
李犁
我是先认识金所军然后才看他的诗歌作品的。阅读让我惊讶。因为生活里的金所军给我沉默寡言诚恳敦厚的印象,而他的诗歌却让我读到了激情灵动干练还有微小的感伤。就象他自己的诗句说的那样:“雨后的天空,明亮而稍冷,深邃而安静”。
这让我把他的诗歌想象成布衣,质地是纯棉的,经过了清水的漂洗,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像一颗沉静的心,素朴低调并沾有生活的滋味和一点点的凉。我把这看作金所军的诗歌品质和人生态度。
所以金所军的诗歌不飞扬更不四处迸溅,他的情感在向内凝聚,直到凝成饱满的果实或者淬火的铁。这使他的诗歌沉实又有重量。有点悲凉但不悲伤,这是对人世间保持清醒和冷静,是过早预见到时光以及万物的结局而产生的悲悯和忧虑,还有热爱和感叹。这一切促使他的诗歌具有了洗练之态和流动之美。
洗练和流动是中国古代《二十四诗品》中的两种诗歌品格,前者主要指技巧,后者指意境,他们又都标志着作品所达到境界。我这里引申一下:前者代表写作方法,即怎么在混乱和杂芜的生活中提取和精炼诗歌的黄金;后者代表形态,说明诗歌是液体的,流动带出节奏和音乐的美。如他的《阳光》:“请给我阳光/从第一缕曙光开始/顺着树梢爬过来/从露珠一样的心情开始/干干净净洒满白纸//请给我足够的光芒/让我在睡梦中也能感觉到温暖/那明亮的翅膀/那无边无际的照射与飞翔/甚至包括它的阴影//请给我阳光/让我睁开疲倦的双眼/像小草感受微风的抚摸/像一个穷苦的孩子/手捧花花绿绿的糖果/奔跑在向阳的山坡上//我不是一个贪婪的人/请给我一点阳光/小小的明亮的一点/用手绢包好/或者画在纸上/什么时候想看就能看见//最好能有一片贴身的阳光/衣服一样穿在身上/就像此刻夜深人静/顺着思绪爬过来的阳光/始终依偎着游走的笔尖”。
我们几乎无法减掉任何一个字句,多一句少一句都不能准确的倾诉出作者内心的风暴!就象我们小时候削铅笔,少一下就不尖锐,多一下就断裂了。同时也说明金所军的诗歌非常适合朗诵,不管是谁只要用心来阅读,都会不知不觉读出声音,并被诗意的无穷和美妙所笼罩。这就是我说的流动之美,这里不赘言。下面重点谈谈洗练,即金所军是怎么“洗练”诗歌和诗歌的境界的。
上面这首《阳光》,除了当中越来越深入的情感在流动,让我们打动的还有构成这首诗的符号乃至意象。假如把其中的“曙光、露珠、光芒、温暖”等换成别的词和意象,再譬如把阳光像“一个穷苦的孩子/手捧花花绿绿的糖果”以及把阳光“用手绢包好/或者画在纸上”等比喻和细节换成其他,此诗就不能有如此的感染力,甚至没有了魅力。这些词句和意象以及更多文字组成的细节都是作者经过心灵的过滤,智慧的反复打磨才成为语言的珍珠和不可或缺的灵与肉的。所以,洗练就是挑选和打磨,首先是从字词句的选择开始,然后扩展到整首诗歌中对事件和题材的选择。字句的选择更多用的是比喻,整首诗歌的选材和淘洗则是一个细节的呈现和事件的叙述,它是一种象征,寄予了作者对意义的追索。
这让我想到老生常谈的一个词,即创新。其实诗歌的每一次进步,都是技术的进步,都是写作方法和技巧的创新和推进。写作者之间首先较量的不是内容,而是手艺,就是面对同一题材,看谁更有绝活。像剑客比的不是剑而是剑法。而绝活首先就是语言的创新,语言的创新就是语言的搭配和嫁接上的出奇制胜。最常见的就是比喻。金所军这方面是自觉地,也是比喻的高手,像他写的《一张白纸》:“一张白纸/彻夜等待着/等待着美丽和幸运的来临/等待着黎明徐徐上升/等待着失散多年的弟兄来敲门……即便纸上行走的一万吨白/一万吨黑/一万吨抒情/加起来是三万吨想象/依然远远不够一张白纸托付终身……”。把白纸拟人了,而且用吨来形容白、黑、抒情和想象,虚的看不见的不仅可知可感还有数量了。还有“秋分不是秋风/秋分被两滴露水夹在中间/前面是白露/后面是寒露/秋风在这天有点凉(《秋分》)”这里语言的修剪打磨都了极致的程度,是比喻又超出了比喻的范畴。还有《老宅子》:“老宅子消失了/像痛一样//曾经有过/现在无影无踪了”这里用虚比实,中间还有通感,不仅形象而且思想和内容也引起了变化。这些陈旧的词汇,经过他的重新嫁接便变异出新的光彩和境界。
这里我们隐约意识到技术带来了内容的变化,甚至意境的深化。因为比喻甚至更多的修辞方法使诗歌的表意更准确,更形象更深邃更美。现在很多诗人和评论者羞于谈技术或者语言。觉得那样解析诗歌太表层了,经常使用一些哲学和美学上的概念来统摄诗歌,虽然提升了诗歌的主旨,但是使诗歌分析变得大而空,从而把评论排除在写作方法之外。其实诗歌就是修辞学,怎么把修辞方法化作写作者自身的一种习惯和素养,从而不是刻意和强迫而是一种自然自在本能地无为和无所不为地使用才是最大的成功。
其实很多诗人都是这样,他本身并没有觉得自己使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而是他天生对语言对诗歌有一种敏感,他冥冥中被一种神奇的力量驱使着,对语言进行淘洗和锻打,使自己成为语言的巫师,使诗歌成为语言的炼金术。金所军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他总能在世俗和实际得如铁板一块的生活里敲打出诗意,就象给密不透风的黑暗屋子安上一个窗口,让阳光和鸟鸣渗进来,让诗歌鲜活葱郁起来。而且:他不局限于用此物比喻彼物,他还把一些生动的画面以及情节和细节带进诗里,让诗歌与生活的界限消失“……大地和丰收平分秋色/剩下的柴禾被送回了村庄/我看见当年的穷人董铁锁/端着大碗、趿拉着鞋蹲在新房的门坎上……(《秋天站在树顶上》)”还有:“……这天,父亲的心比秋风更凉/葬了老绵羊/父亲咳嗽了一声/担起一担结霜的柴草返回家中/走到半路歇息了一下/顺便把左肩的伤心换到了右肩上(《秋分》)”。前者是用生活中一个真实的画面来阐释丰收的意义和价值,以及背后无法用言语说出的隐喻。后者在本身就悲凉的事件中,又在结尾陡然提升了一下:“顺便把左肩的伤心换到了右肩上”把虚的伤心变成能两个肩膀来回换的可见可感可以触摸的行为,这就使原本的悲凉变得更刻骨更宿命化。从而也就使原本实打实的一个生活场景诗化了。到这里诗在惯常的生活中抖地向上一跃,意境立马开阔了,境界耸起了。
这再一次证明了诗歌技术的力量。是诗歌手法的高妙和新颖强化了诗歌的魅力,也提升了诗歌的品格和境界。有句话是武艺有高下,情绪无古今。古往今来,诗人们的情绪和感受本质上没有改变,但是诗歌的方法和表达方式都前进了。就是因为诗歌能在前进中对自身技术和方法不断地挖掘和完善,以至我们的眼睛一次次被诗歌中的创新所擦亮和吸引,并最终使我们的心灵被诗歌的品质所击中和笼罩。金所军就是一位能自觉地从生活中淘洗诗意,又乐此不疲地打磨和冶炼诗艺和诗歌境界的诗人,所以他的诗歌总是带给我们许多意外的兴奋和惊喜。
这让我想到前苏联那本著名的文艺感想集《金蔷薇》里,写到一个清洁工为了给一个女孩制造象征幸福的金蔷薇,用一生的时间从首饰作坊的尘土中筛选金屑,并一点点积累到足够打一只金蔷微的材料。金所军的诗歌也是这样,在他的作品里,并不是照搬生活,而是在杂乱的琐屑的尘土飞扬的生活现象中发现和筛选有诗意的细节,再经过他情感的过滤和智性的修剪和打磨而成为诗的情节和细节。就象《二十四诗品》中对《洗练》的阐释:“犹矿出金,如铅出银”,就是说从杂矿里提取黄金,从铅石中冶炼白银。这样才能达到“空潭泻春,古镜照神”的境界。
但是要做到洗练的境界,是对诗人心智的考验。没有心灵的丰富和智力的强有力,是无法做成语言的炼术师。在“西北风吹着/吹得胡同呜呜作响/吹得冬天声嘶力竭/吹出一种/令骨头和大地发冷的/声音(《西北风》)”短短几行诗的背后,也许是磨坏的无数个石头。而没有辽阔的胸襟与对人和物细致入微的关怀和体恤就无法触及到诗歌的河底,就无法把诗歌漂洗得一尘不染。朴素和谦躬,悲悯和大度不仅是诗歌的精神,也是诗人的品格,只有以卑微的心才能映照出天地的辽阔,只有怀抱朴素才能把诗歌洗练得不仅精粹还自然和透明。金所军正为做到这一点而努力,所以他的诗歌在意象和细节的光芒上才更前进了一步,进入到整体的朴素和自由:“妻子轻声诵读一则故事/儿子安静地听着/普通人的故事/比蚂蚁的悲伤也多不了多少/但妻子开始流泪了/儿子也泪流满面//此刻,只有她们两个人在伤心/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是个不需要抒情的时代/不需要感伤的泪水(《时代》)”
这显然是一种反讽,是对我们这个时代不动声色的批评,当然还有关怀和焦虑。但是从写作的姿势上是放松的,已呈现出自然朴素的气质,没有以往在字词句上的较量和比拼,更多的是让事件本身来说话,行文松弛而散漫,但是一种冷已经穿过皮肤直抵骨髓。还有“一个死去的人/生前我认识她/死后/我曾想去看看她//一个死去的人/生前偶尔通通电话/死后/我曾梦见她//一个死去的人/生前见面不多/死后/想见也见不上了//一个死去的人//生前是个活生生的人/死后仿佛出了远门//一个死去的人/她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死得很惨/过去好几年了(《一个死去的人》)”
这首诗歌比前一首更自由更自然,全篇没有情感的外泄和喜怒,好像在谈一个和自己不相干的生与死,几乎是随欲(不是随意)而言和平铺直叙,但更深的技巧已经深藏在自言自语当中。作者也并非是故意的大智若愚,而是此时的诗歌技术已经化成了他的一种习惯和下意识。这是更高档次上的洗练,如果说上面那首诗是在尘土中筛选出具有诗歌本质的金屑,而这里主动去选择这样事件的本身就是诗人对生命和万物最彻底的的同情和关怀。
至此诗歌在金所军的洗练下,变得越来越薄,薄到磨破了一层纸,薄到了语言与诗意与心灵完全重合,薄到透出光亮和黎明,露出他追求的清澈和澄明的境界来。而他的写作行为就像在黎明的清水里淘洗黄金,滤去泥沙,让金子的光芒更纯粹和深沉。
这境界就是金所军对人世间的关怀和深情,对卑微生命的关注和抚摸。他努力用诗歌把瞬间的美好永存,把对人生悲凉的态度化作对万物的悲悯和大爱,并诗意的行走在纸上。
这就是我理解的金所军写作的主旨和内容。所以他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乡村诗人,乡村只是他写作的一种符号,他用这些熟悉的生活来隐喻他心中人类的苦难和幸福,现状和未来。这一切证明他是一个布衣诗人,并拥有清澈的眼睛,和大地一样谦逊和诚朴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