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蝇飞过的地方||王永寿

NO.1 一连几个月,何三娘的哭,就沒停过。前年,她丈夫病故,还沒摆出这样哭的架势。
何三娘天天哭得花容失色,雨打梨花般惹人怜爱。起初哭得不带调,没节凑,一会号啕大哭,哭得地动山摇,一会低声啜泣。可能没摸出哭的道儿。后来,那哭竟修练得跟人家唱京剧似的,动作也跟上了,摇着头,拍着大腿,余音拖得老长,脸儿憋得彤红,鼻涕眼泪下巴似雨帘。
何三娘到底哭啥呢?村里人都清楚,哭自家的房子建不下去,大家都可以建,唯独她家不可,能不伤心?但她后来哭得分不清字眼,或许,消耗体 能太多,底气不足了,哭了啥?谁也沒听出字眼,音调倒蛮抑扬顿挫,跟专业哭丧人员相比媲。几个月下来,人瘦得换了一副模样儿。原来的她,虽说已五十出关,但还是风韵犹存,那眉毛看上去又黑又弯,恰如烟笼葱缭的柳叶黛,双唇则又红又润又饱满,如同含娇蕴羞的桃花瓣,那面颊更是粉粉嫩嫩,白里透红,仿佛阳春三月的俏枝悔。只可惜,建房之事,把她个美坯子全御了,原来大家都说
她像刘晓庆。咋几个月下来,就成了个瘦骨如柴的一張皮包裹着,瞧一眼,怪吓人的。
NO. 2 今年春季,雨水特别多,把何三娘的泥土屋给冲垮了一个屋角,房子看起来就不平衡了,整个房子重心往这边倒了的倾斜,住是不敢了,何三娘索性请小挖机扒了重建。可村里不让建,她就来气了,找到村长,对村长说,人家水田都可以大大方方,挺直腰板子做,我拆旧建新咋不可呢?
村长嘴里正刁着一根烟,陆陆续续从鼻孔里冲出两道烟,歪着头,沒把嘱里的烟抽,说话时那根烟似乎抖得要离开两片唇皮,声音含糊地说,小村已列入规划区内,就是动个茅坑、猪栏,也得经过政府同意,方可动土,你擅自就做,靠上县太爷了不成?
何三娘带着哭腔说,村里刘三強,刘自金,他们咋可往水田上建?政府不是说保护耕地吗?
村长“呸”地从嘴里吐出半根烟,说,这两个人,情况特殊,上面领导开了口。我们村里没责任。你有能耐,也叫县长给个电话乡里,村里自然不管你,爱往哪儿落?谁敢透口气。
村长知道何三娘家没背景,早查清了她家的根系脉络。村干部对有来头的村民,见了人家,像条哈巴狗。
何三娘知道,刘三強的外甥在公安局当副局长,刘自金的姑父在县组织部干部科,当科长。这年头,沒个靠山,想行个事,简直铁板一块——缝都没有,村官那双眼,很势利,你有大靠山,他们就像当年的汉奸,见了太君似的,唯唯诺诺。要是沒个亲戚在政府里当差,他们都把你当软柿子捏。
何三娘动土时,村里几尊神都敬了香,每人给了两条中华烟,又另给两仟块钱村长,让村里的一班人马到酒店喝一杯。现时,那点蝇头小利,人家跟本没放在眼里,做时照给你添堵,让你悟出个理儿,不是打发叫花子,指望再下重料。可何三娘似乎不懂这潜规则,丟了半截蚯蚓,就想钓到大王八,哪有这等好事。执法队天天来砸,来唱高调,说打击违章建筑。何三娘见了那阵势,除了哭,还是哭。起初,村里人天天围着看热闹,也有站得远一点说风凉话与嘲笑的。时间一长,人们就不以为然,没人凑这份热闹,看到拆,最多瞅一眼,匆匆走了,谁也不想听何三娘的老调。何三娘家因为没背景,日子又过得紧巴巴,又是村里的独姓,自然就让村官执法找到了“用武之地”。 这年头,没钱,无靠,基层干部尽在你头上动土。受遭殃,大家都避而远之,这世道,势利眼多。个別人看不下去执法队老来骚扰何三娘的房子,就给她出主意,说,关隘难通钱作马,你光疼钱,能不拆?乡、村、执法的头儿,一人塞个三五万,看谁还敢吆三喝四来“执法”。何三娘掐指一算,摇了摇头说,给不起。沒好处,人家自然天天来履行公事,秉公执法了。现在的基层干部,都是花钱进步的,人家垫了底儿的,能手软吗?竞选个村官,一个比一个狠,你花六十万,他就翻一翻,最后拼到两佰多万,他们成了一方诸候之后,不要收回垫本儿吗?那百姓还有好果子吃吗?原来选举拉票时,给你一条烟,现在求他办事了,那是十倍二十倍,甚至一百的礼也说不准,那是他收回本钱的时候了。 何三娘一个妇道人家,不知这个理儿,就知天天以泪洗面,他们不是菩萨,没有慈悲之心。收到大红包,表面说几句大道理,我是共产党员,替人民办事,是我职责,钱收回去,把我当成啥了?说起来咱还有点亲,为自家人扛一扛,挨上面一顿骂,值!人家自然觉得他铁,对自已的事上心,丟下钱就走了。所以,现在的百姓,很厌村官,不提还好,一提,就咬牙切齿,捞钱的本事不知上哪儿投的师,你根本无法想像,收了你的钱,还对他千恩万谢,当然,百姓不是傻瓜,离开后冒出一句:村官,都是恶贯满盈的混球儿。
NO.3 何三娘到 过村委会找过村长理论过。
村长坐在老板转椅上,双脚伸到办公桌,很有节凑地动着双脚说,別再缠了,比你困难的,得优先建。
何三娘几乎衷求遁,我危房不重建,住在里面万一压得人,政府能负责吗?
村长霍地站起,说,吓唬我?门都没有,你没向政府申请就拆了,无视人民政府,政府沒重罚你,算人民政府开恩了。
何三娘被村长的动作与极凶的面相,吓得一惊,继而呜咽起来,哭声压得很低,仿佛水壶里煮开的水,动静不大,边哭边说,屋都倒了一个大屋角,瓦都掀下来了,村里谁不知道,这泥土屋,修补管用吗?我拆了就向你们报告了。
村长点燃一根烟,用力吸一口,吐出个大烟圈,扭头对对何三娘说,你先斩后凑,靠上哪个大领导?啥事得先向我们村一级政府汇报,咋不信村政府呢?那你就牛到底吧!看你厉害,还是我们村政府厉害,告诉你,政府养着执法队,就是修理你们这些刁民的。
何三娘知道村长这些话,通谍她彻底死心。但不做,过年儿女们回来住哪儿?不可能一辈子租人家的老瓦房住,她不想与村长争下去,鸡蛋碰不过石头,闹缰了,他就彻底卡死了,最后,何三娘还是向村长赔不是,流着泪,离开村委会。
何三娘思量几天,厚着脸皮托了不少人去乡里,村里说情。去活动的人,都与领导沾上一点亲,但礼薄,领导一听替何三娘说情,都挨了骂。
看样子,何三娘的房子,各级领导统一了口径——不让建。
山穷水尽疑无路,何三娘只有以泪洗面,租住的小瓦房里天天传出她哀婉的哭声,听者无不心生隐隐之痛。
人碰上麻烦事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解决不了,真会急死人,烦死人。虽说现在倡导和谐,但基层干部跟本没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意见,没有关心群众疾苦的理念。他们把权力当作一棵摇钱树,钱塞了,一句:经我们研究决定,你实属困难户,同意。沒好处,跟你讲政策,讲原则。
何三娘因为房子建不下去,觉得在村里人面前抬不起头,村里原先一些跟她要好的人,也渐渐疏远她,很多人与她碰面,几乎不搭理她。农村人很现实,越遭欺的人,对他(她)越避而远之。见有几个钱的人,就想方设法去套近乎,巴结权贵,总能捞到好处。正如周立波所说:跟着苍蝇会找到厕所,跟着蜜蜂会找到花朵,跟着千万赚百万,跟着乞丐会要饭。现在人,那双眼贼溜得很,和谁在一起,惦量得仔细。
何三娘越来越焦悴,每每见着被执法队推倒得乱七八糟的新房,就禁不住潸然泪下。哭,成了何三娘每日的必修一课。沒有人同情她,她也不知咋的?见了新房那个样,自然而然要流泪。
她租住在人家的旧瓦房,周围都沒人住,大家都建了新房,那歪歪斜斜的老房子,就像留守的老人,没人理了。不过,离何三娘的新房很近,最多八十来米的样子,何三娘出了门槛,就能瞄到被拆了还剩半人高的新房基。
何三娘想使的法子都使了,乡、村干部的牙缝就没动一下。看来,真没县长的金口,怕是永远摊在那儿了。
何三娘想,一个平头百姓,是与县长扯不上关系的。看来,建房是没指望了。想到沒辙,何三娘又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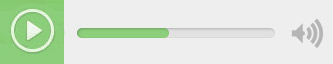 何三娘的娘家,在偏远山区,只有一个哥哥,六十多岁了,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沒盼头,她很少回去。
这回,何三娘心烦意乱极了。从破瓦屋钻出,就被一些人指指点点,好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在农村,大家能办成的事,你一家行不通,那真是有点丟脸面。
何三娘想避开这些怪怪的目光,决定回娘家住上几天,虽然娘家不能带给他希望,但她认为回去走走,可以调节精神,把烦恼御下。
那天,她是坐早班车回去的,暮春里,春色已浓,山雾弥漫,车速缓慢,朝湿的雾气将车子包裹起来,像一只蛹,游走在乳白色的蛋清里。快十点钟,雾霭褪尽,山色清淅,车速加快。一路,何三娘忧心忡忡,她把头探出车窗,视野里,一串红和金黄色的野菊花点染了墨绿的山峦沟壑。她贪婪地深吸一口。
快十一点钟,车子才到了她的娘家——洞白圩村。这个大山里的小村,森林茂密,沟谷深邃,溪流潺湲,天然一幅云通道人山水。美丽的风景,没有拂去何三娘心头的不快,脸上还是遮掩不住的衷伤。
何三娘的哥哥,见妹妹这次回来,咋比妹夫前年去世,更为忧伤,便问起缘由来。
何三娘连连叹气,刚漏出一点声音,又慢慢弱了下去,愁闷悬在脸上,拽得眼角都耷拉下来。
哥哥的目光很重,石板似的压在何三娘的嘴唇上,焦躁、失望在脸上波涛汹涌,再慢慢吐出一句:到底出啥子事了?
何三娘“哇”的一声哭开了,那哭声,让哥哥不知所措,但他觉得妹妹一定是遇上棘手之事了,不然,倔強的她,不会这么伤心。
哥哥用阴鹫的目光,盯着何三娘说,就是天塌下来,也用不着伤心成这样,谁吃了豹子胆,竟敢负我妹,哥给你摆平。
何三娘知道哥几斤几两,更知道哥的脾性,内向、怕事、软弱,这就是哥哥的特点。今天,哥说这话像换了个人似的,她知道哥的家境,没资格说这种大话,两个儿子在苏州打工,两个儿媳在县城,一个在酒店端盘子,一个做保姆。哥是个老实透顶的人,说话从来没重声,也不说过头话,今个,哥咋啦?莫非皇上赐给了他尚方宝剑,在妹妹落魄之时,救驾来了,但这深山老林,不说皇上不会来,就是乡、村干部也难得踩进,哥咋出此言?
何三娘止住了哭声,眉宇几乎被兴奋崩开。
哥哥的脸,皱纹舒展开来,灿烂地开放着,好像对妹妹的事,有十足的把握,凑近何三娘,压低声音说,遇着啥不顺心的事?要是那些苍蝇蚊子(指村官)敢欺负你,那他们那顶帽子就別想戴了。
何三娘惊愕地盯着哥哥那張嘴,好像哥哥换了一張嘴,原来的那張嘴,打死也吐不出这种话,她被哥哥说得一头雾水,家里连一个吃皇粮的人也没摊上,哥这是唱的哪一出?莫非哥老年痴呆了,开始说胡话了。
在她陷入沉思之中,哥又凑近一点何三娘,说,三春,啥事跟哥倒个明白,哥这回定给你个说法。也让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惊出一身冷汗,讨好你一回。
何三娘定神地看着哥那張一張一合的嘴,顿时,眉头紧蹙,啧了一声,觉得哥不像有老年痴呆,也不像在开玩笑,说话的表情显得很严肃。难道咱家祖坟冒青烟了,有人戴上官帽了?或攀上高枝了,不可能,绝不可能,两个侄子都是初中生,在外做苦力,两个孙媳妇进城,一个在酒店,一个听说做保姆,再沒有其他亲戚出人投地的,哥不是在大白天痴人说梦话吧。何三娘的脸,又阴了下来。
哥见何三娘一脸迷惑,嘴凑到何三娘耳根道,咱家与县长扯上关系了。
这一句,像青天白日一声惊雷,炸得她心中涟漪翻腾,她几乎乐得要蹦起来。
何三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怀疑在做梦,拧一下自已的大腿,啊唷一声,又睁大双眼,盯着哥哥,给哥手腕狠拧一下,哥“哎呀”一声,她确认不是在梦中,乐得心跳加快,不管怎么说,哥冒出这句话,必有其因,那她的房事,就有救了。
何三娘迫不及待地问,哥,到底怎么擎上高枝的?
她哥左瞧瞧,右看看,其实,自家屋里用不着这么神秘,但他怕隔墙有耳,走漏这天大的秘密,她哥突然笑了,可能意识到自已太多疑,原来,他家是独户,离开村子一百多米,那張像核桃纹的脸,像花朵一样,灿烂地开放着,幸福总在脸上掩饰不住,轻声对何三娘说,三春,咱家晓利在县长家做保姆,县长说了,咱家有什么小麻烦事,只要不触犯法律,尽管开口,但外面別漏嘴说咱哓利在县长家做保姆,就说晓利的大舅子当县长,看谁还敢给咱家使坏。
何三娘听完哥哥的话,笑在脸上迅速铺展开来,微歪着头说,这回看乡长、村长怎么卡?
哥哥睨一眼何三娘说,三春,建房啦!
何三娘笑着点头说,建那点房子,乡村干部没少“费心”,被他们叫执法队来拆了十几回,比唐曾西天取经还艰难。
何三娘的哥哥又说,晓利下午要回来一趟,你跟他道个明。
何三娘朝哥哥点了点头。
下午三点钟,孙媳妇哓利回来了,见了姑姑,晓利显得很意外,姑姑似乎很长时间没回来过,双方几句客套话,何三娘就直入正题,道出了自已建房之难的一路辛酸。
孙媳妇听后说,姑姑,既然你急着要做,那你下午就赶回去,明早就有消息。
何三娘被孙媳妇几句话,心里畅快多了,脸恢复到往日的晴朗。
四点二十分,山脚下的马路正好有一班客车经过,何三娘匆匆下了山,赶坐这班客车。

NO.5 第二天一大早,乡、村干部就赶到何三娘的住处,何三娘正吃稀饭。
乡长进屋找了一把椅子坐下说,我们经过这几天的研究决定,同意你家建房。昨晚县长又打电话过问你家建房情况,县长与你家啥关系?咋那么上心?
何三娘显得很不屑地说,大关系倒沒有,是我娘家孙媳妇的大舅子,我哥不肯我们丈此之势,来捞好处。
乡长的嘴角飘起一丝笑意,眼里含着谦和,话里带着恭敬,咋不早说呢,我与县长也沾点亲,咱们也算亲戚了,房子抓紧做吧!
村长沒坐,站在乡长右侧,点头哈腰,声音低低地说,你家拆危房而建,我们根据上面的政策,补助伍万伍仟,但外面千万不要声张,你家情况特殊,其他群众还达不到补助的条件。另外,你一家人的低保,村里近日将替你办好,还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关心群众疾苦,是我们基层干部的职责。
乡长的微笑溢满了整个面孔,又说,听说你儿子是高中生,在广东创业,明年就到村里为工作吧!村里也需要这样有作为的年轻人。
乡长与村长两人的说话,像打铁铺里的打铁声,一人一下。把个何三娘说懵了。也不知替他们泡杯茶,俩人走了之后,何三娘偷着乐了起来。
何三娘怎么也想不到,冒充了一回县长的亲戚,好处真多多,房子能建,一家低保村长的觜一张一合,就成了,儿子又能做村官,人家说,女人傍上大款有钱,咱靠上大官,什么好处都有。
何三娘的房子突然能建,成了村里人的话题,猜测那真是多种多样,有说送了大红包,有说何三娘勾了村长的魂,有说何三娘上访碰上一个好官,好官给了力……但奇怪的是,村长却在何三娘工地上忙开了,这唱的是哪一出?有些事,总是纸包不住火,很快,全村人都知道,县长是何三娘的亲咸,难怪这些干部这么乖。
何三娘经过精心打扮,走起路来又现出款款有韵,杨柳春风,村里人见了她,都要跟她唠磕几句。
村长天天往何三娘建房工地上跑,叮嘱工匠们认真点,卖力点,自已操起铁锹,这儿弄到那。
何三娘见了哭笑不得,想起前后两种做法,摇了摇头,冒出一句:这苍蝇,高调嗡得再动听,再怎么装扮,飞到哪儿?都让人厌。 (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平台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