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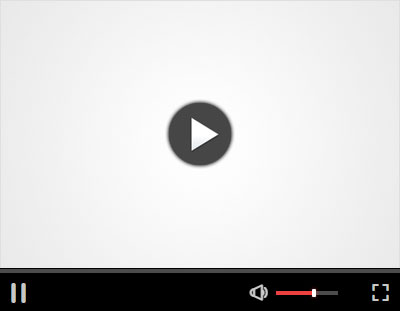 一块并不宽阔的田地间,为何会有捡拾不尽的残砖碎瓦,在以窑洞为主流民居的陇东乡下?父亲告诉我们,说听说这里以前曾是一座古寺。何寺,兴败何时?父亲不知,爷爷也说不明白,爷爷说他只知道安兴四组玉珠家那块地原来是个庙场子,安兴村大大小小的神庙早先都聚集在那里,后来张家出了一位道人,带领村民把庙场子神庙一处处迁建,于是就有了遍布全村的大小神庙,但爷爷并没听说过过庄岭梯田间的庙宇,或许爷爷记事之初,那块地里的神庙已荡然无存。 历史不曾为谁逗留,黄土塬畔一处小村,却演绎过的无数神庙兴衰,正如演绎过无数兵荒马乱的大地,经历过无数的朝兴夕废,那些崛起于黄土垄头的风物,最终都湮灭进黄土,如轻风掠过,如雁渡寒潭,去不留痕,那些有一丝儿记忆与残存的历史,就成了不灭的神话。正宁到彬州交界处,有一座高庙山,高庙山的庙会近十多年红红火火,高庙山的历史还是用故事来说说,请点击收听。小县正宁区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寺庙的传说。“苟仁寺”的传说,“高庙山”的传说,以至“显圣寺”的相关传奇,都流传了数百年,都渐渐融入玄幻,变得迷离,收纳着人们对正义的追求和对超自然能力的冀望。只是在这片土地上,却似乎没有一座寺庙建筑可以像云寂寺那般,被周边民众更多的传道,更多的牵念,没有一处古寺庙,留下比云寂寺更多的故事和诗文记忆。苟仁寺早已无存,苟仁寺的传说却在正宁周边广为流传,请点击收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