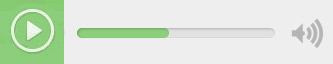新浪博客:河津赵爱玲http://blog.sina.com.cn/u/1289300977 散文 父亲的土地 文/ 赵爱玲 1 那时候我上二年级,和老奶奶住在一起。父亲的钟声就是我每天上学的闹铃声。 父亲是生产队队长。每天早上6点他就敲响了村子中央的铁钟,“铛——铛”,社员们就提着农具到钟下集合,听父亲分工。老奶奶一遍遍地喊我:“玲啊,玲,起来,上学啦!”我每天晚上要纺一个线疙瘩,然后就着油灯写完作业,才可以睡觉。所以,早上老奶奶一叫我,我嘴里答应着,心里却是迷糊的,眼皮也睁不开。直到天儿大亮了,我才在老奶奶反反复复的喊声中急慌慌地爬起来。我背着书包一溜小跑,远远看到学生正在操场里跑操,校长站在边上巡查。我得想办法趁校长不留意插进队伍,不然要被罚的。我站在操场北边的破墙根,把身体隐在墙后,一只眼睛对着墙缝,心里扑腾腾地跳着。这时候就有三三两两的小伙子大姑娘扛着锄头或者铁锨嘟囔着:绝后的××,这么早,又要扣工分了……我分明听见他们是在骂我父亲。我又气又羞,心里埋怨父亲,干活又不是上课,今个完不了不会明个吗,干嘛要催着人家早起?再说了,睡不够多难受。我正探头探脑,冷不丁就被校长发现了,我耷拉着脑袋,满面羞惭地背着书包从村南头到村北头,来回跑三遍……更让我无地自容的是,一路上,总会遇到大姑娘小伙子埋怨父亲的牢骚声,更有过分的还朝我吐唾沫。 隔三岔五就有小伙子或者大姑娘站在我家门前骂:“绝后的××,我吃队里的,吃你家啦?你他娘的少管……” 有一次,我放学回来,撞见我家邻居的姑娘小芳耍泼,她滚在我家门前连骂带哭:“我锄坏了玉米,我就故意咋啦?又不是你家的,你罚我返工,你还扣我工分,你活该绝后!”她看见我就冲着我骂,“活该!” 老奶奶在屋里捂着脸抹眼泪。我惊恐地望着她,她用大黑襟裹住我,抱着我说:“没事,你爸没错,他就是太过认真了。唉,可都不认真吃啥啊……” 那时候,我有四个妹妹了。 我隐约明白了一些事理。 看见社员上下工,我自觉地回避到一边,或者埋下头快步跑过。 不知道父亲是否受够了,我真的受够了!我在老奶奶面前不止一次地诉说自己的抱怨。 终于,在年底的时候,老奶奶牵着我的手,找大队书记,她说贵贱(死活的意思)不能让我孙子干队长了,他太实诚太认真,孩子跟着受骂,不该啊……奶奶一推我,我就哭着说:“我不要爸爸当队长!我不要爸爸当队长!我受不了他们骂我爸爸!”书记为难地说:“除了他,咱队里还找不出个对土地这么认真的了,那我们以后吃啥啊?”我惊讶地抬头,心想,他怎么和老奶奶说的一样? 我对于土地的恨意,就在那些骂声之中,一点点地滋长了。 2 就这样,父亲当队长一直到分田到户。那时候,我是四年级学生了。父亲再也不用敲钟了,也再不挨骂了。大家见了父亲都很尊敬,经常请他去地里指点,比如怎么给棉花择叶,怎么种红薯保墒,如何给种玉米授粉……那时候,我走过人群时,再也没听到埋怨父亲的声音,不仅如此,我还能感受到他们眼神里流露的敬意…… 老奶奶说,不一样啊,以前给生产队干,你爸爸遭人恨,现在给自个干,你爸爸是香饽饽啦!谁见谁敬着呢。 老奶奶看着美滋滋的我,揩着我的鼻子说,看把你乐的,你爸爸是个好庄家把式!庄稼人就认这个! 那年正月,我有五个妹妹了。家里像往年一样,不准备喜庆(当地的风俗,生了男孩摆宴庆祝)。父亲却说,摆宴。很长一段时间,乡人以为我们家生了男孩。 我老奶奶,我爷奶,我父母,加上我六个,一家11口人,像我家这样四世同堂在一口锅里吃饭的,我们村里还真没有,即便是有也已经分成几家单过了,所以我们家分得土地最多。可是我们家没劳力,就我爷爷和我父母三个人。于是我们就成了小劳力。 每年春季,一到星期天,父亲5点多就把我们从热被窝里一个个拎出来,扛着锄头,提着绳子和镰刀,背着干粮袋子和水壶出发了。我们家的地在中条山顶,距离我家大约15里地,从山底到山顶,坡很陡,到不了半山腰我们就累得走不动了。赶到山顶,太阳已经老高了,父亲已经锄了一小块地了。父亲手把手教我们锄地,他先让我们分清麦苗和杂草,然后示范,前腿要弓,后退要前伸,手往后拉。他过一会返回来检查下,看我只除草,就说,我们是锄地,没草的地方要松土。因为父亲反反复复地检查,我们不断地返工重做,我们的活儿也就越做越慢。眼看和父母的距离落得越来越远,我们也就失去了干活的心劲,干脆坐在地头玩起了蚱蜢。用马尾巴草茎从蚱蜢脖颈处穿过,打个结,两两相斗……父亲正要吆喝我们,就听见妈妈高声地吵父亲:“你当孩子是你的社员啊,差不多就行了!都停下,到埝头柿树底下吃馍!” “噢,吃馍啦!”我们把手在衣服上搓几下,一人一个馍馍,馍馍是大部分玉米面和一小点白面做的馍,这比以前的玉米糕好咽多啦。一口馍,一口大葱,好吃极了。父亲三两口吃完了,就兀自蹲在地里捡拾刚才锄的草,码成捆放到地脚头,回家的时候背回去喂牲口,我们家十几亩地全凭牲口拉犁播种,牲口圈里养着一头驴子,一头犍牛,还有一头小母牛。三头牲口每天要吃很多草,要堆小山一样高吧! 等我们吃完了馍,父亲就吆喝我们开始干活,山顶上我们家有五块地,父亲分给我们一块,说干不完不许回家! 春天的太阳虽然不毒,可是一天下来,我们又累又渴,感觉夏天般炎热。干干停停,就这样一直干到下午。父亲干完活儿,让母亲帮我们,他自己却下到山坳里垦荒地,他垦出很多小块地,有的只有两三平方米,有的地块稍大点,这样的小块地加起来比有的小人口家分的土地还多。这样的小块地因为地势偏狭,无法使用牲口,就必须完全靠人力,犁地播种都由爷爷整靶,父母和我们用绳索拉,我们就像列宾油画里的纤夫。父亲会种上蓖麻、豆子、红薯等一些耐旱又好生长的农作物。到了秋末,全都种上小麦。大部分山里人,因为土地多,又因为贫瘠,只种一料麦子,可是父亲总会在差不多的土地里,种两料作物。 每当读到“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我会感同身受。在儿时的意识里,土地上的劳作即苦难,它深深烙在我的心里。 劳作之余,在高山之上,我会无数次想像自己能够长出一双翅膀,飞离土地。
3 每年农历五月初,我们的村子最忙碌。由于麦子和大蒜是同期收获,所以我们夏收的劳动量是双倍的。那时候我们家乡还没收割机,完全是手割。而就在这时,水地的大蒜也到了收的时候,错过了收期,大蒜头脱茎了,就没法编成蒜辫子了,也就卖不成好价钱了。大蒜的收成是我们全家的花费来源。 每天早上四点多,父亲就叫醒我们,父亲背着一捆镰刀,赶着我们上山。天上还有月亮和稀疏的星星,困得几乎睁不开眼睛,我们一路走一路看星星,不看星星,我们会打瞌睡。父亲说,起个早,天凉快,等太阳出来了,咱就干完了…… 可是会吗?那么多的土地!我的手上满是血泡,老痂还没脱落新伤口又出现了,手指伸不直,腰痛腿酸,一坐下就不想再起来了。任凭父亲怎么说怎么吆喝,我也不起来了。那时候,我蹲坐在地头,晒得头发晕,我抹着眼泪在心里发誓:“我要离开这里。”那时候,我是那么憎恨土地,那么憎恨土地里没完没了的劳作。我决心好好读书,永远离开土地。很多年后的一天,我读到鲁迅的句子:我们热爱故乡的文化,却并不热爱故乡的土地。难道不是吗?我们在血液里爱着故乡,却一个个拼命远离故乡,而离开的理由就是土地。 然而,我的父亲,他是那么痴迷在土地里。他一边收割,一边快乐地甩着汗瓣,他不说话,可是笑容在他的眼睛里。当他把麦捆扛到我家的木制平车上,他会返回地里捡拾一根根麦穗,像在怀抱一个个孩子…… 晚上,我们都累得睡下了,父亲却撂下碗筷,去了水地收大蒜。那些大蒜深埋在泥土里,要手握蒜刀一个一个地挖出来。母亲躺一会也出去收蒜去了,我负责照看妹妹们睡觉,看家。 遇到雨天,劳累的人们也该歇息了,可是我们村的人们更忙了,那些因为收割麦子堆积如山的大蒜,蒜叶已经发出腐烂的气味,再烂下去就无法编蒜辫子了。家家大人小孩齐上阵。父亲教会我,我教会妹妹们。 白天,晚上,直到编完,直到雨停。满手黑绿的污泥,浑身上下弥散着腐烂的蒜臭味…… 天晴了,我们跟着父亲继续收割麦子。我们把麦子摊在打麦场,父亲吆喝着我家的两头牲口,拉着石碾子碾麦子,我和妹妹拿着铁锨,等父亲喊:“接屎!”就急忙小跑着赶过去,把铁锨放在牛屁股下……后来,碾场就用上了四轮车,我不用再跟着牲口满场跑了…… 碾完了麦子接下来是晒麦子,拣个太阳好的日子,父亲头戴多年的破草帽,衔着一根烟袋锅子,把一袋袋麦子用小平车拉到场院里,摊开,然后脱掉鞋子,光脚在麦子里犁出均匀的麦沟,像这样一天要反复几次,我试过一次,脚丫子烫得我直喊叫。别人家嫌麻烦,只晒一次就归仓了,父亲却总是拉进、拉出反复三次。他说功夫没白费的,彻底晒干,不生虫子不发霉。 晒好的麦子被父亲一袋袋倒进他亲手做的砖粮仓里,透气但不漏洞,老鼠进不去,就连虫子也只是在仓外徘徊…… 夏收和秋播之间的日子是农闲的。没有那么忙碌了,父亲还是起早贪黑,早上我醒来时,父亲已经割草回来了。他说这个时期,人休息,也是牲口静养的时候,必须让牲口吃饱吃好,到了秋播时机,牲口才有精神干活。平时没事他就储存农家肥,把牲口圈里的粪土一车一车铲出来,堆积在水地头,然后浇上大粪,开始蓄粪。我们家的庄稼长势好,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父亲做农活细致认真,一个是父亲舍得施农家肥。一般人下不了那样的苦,所以地里不是杂草高过庄稼就是庄稼叶子色泽浅淡,打卷,生虫子。 那时候,我总会听见人们经过我家土地时说:这家的庄稼做得好啊!每当我和父亲经过庄稼地时,总习惯评点一块块庄稼。父亲看到庄稼矮小,杂草疯长的地块时,总会惋惜地说,看看,这庄稼做成啥了! 听到那些关于父亲的赞誉,我从由衷地开心,也觉得自豪。我明白,所有这些都是土地给予的。对于土地,我充满复杂的感情,既恨又敬畏。
4 暑假是城里孩子的天堂,可是对于农村的孩子,尤其是我们这样有着很多贫瘠土地的山村孩子,暑假是炼狱。大部分孩子的主要任务是割草。各家都养着一两头牲口,对于农民来说,牲口几乎是家中一员,它是家庭的主要劳力,而草是牲口的口粮,割草对每个家庭来说,是大事正事。经常吃青草的牲口膘肥体重,经常吃干草(麦秆)的牲口松垮瘦弱,看每家的牲口,也可以看出一个家庭是勤劳还是懒惰。那家的女儿或者儿子天不亮就背着满满一筐青草回来了,那女儿或者儿子的勤劳的好名声就出去了,而且十里八乡地远扬,提亲的说媒的就纷至沓来…… 放暑假了,别人家的孩子只是早上割筐青草,就可以玩一天了,我的父亲还要带着我们天天到旱地杀埝。用我现在的理解,杀埝的原理就好像给土地做个全方位的美容。先用斧头或者锄头把埝墙上的荆棘、杂草清理掉,这就好像给人洗脸去污,然后用锄头刮去埝墙的表皮,这好像给人去死皮敷面膜。据说埝墙上刮下的土是上好的肥料,能够滋养土地,所以最后一道杀埝的工序才是最重要的,用铁锨把这些埝土均匀地撒在土地上……像这样做土地,在我们村也只有两个人,村西头的老夏头和我父亲。老夏头已经去世了,只有我父亲还这样做土地。他做土地就像在养人,过上一两年,他说这块地需要休息,只种点秋作物,不种小麦了,缓缓气。大家几乎不这样做了。很多人已经把远在中条山上的土地撂荒了,因为这些土地由于从来没施过肥料,再加上只靠老天下雨,连年干旱,导致这些土地越发贫瘠,一亩地打不下多少粮食。上世纪90年代初,仿佛是一夜之间,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男人大都去了工地,女人大都到饭店洗碗……土地大片撂荒了,杂草丛生,完全没了土地的样子,父亲看着,叹着气,土地全凭人做啊……他感叹,农民抛掉了土地,就忘了本,那还是农民吗? 我和我的姊妹们一个个憋足了劲儿都发愤读书,想要离开土地,去过另外一种生活。贫瘠的土地上有限的收入逐渐吃紧。我上大学二年级那年,一天,听妈妈在信里说父亲随着一个建筑队在我所在的城市打工!那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的父亲也终于不得不远离家乡……多方打听,我终于在一个小工地上找到了正在施砖的父亲。 在高高的墙上,父亲一手抹着水泥,一手小心翼翼地堆砌着砖块……秋天的天空格外高,格外蓝,羽毛一样的白云在父亲的身边漂浮着,流动着。在城市,在异乡,我仰望着父亲,不敢大声叫唤,我担心蹲在高墙之上的父亲分心。我久久地望着,望着……亲切和难过交织的感觉使我想哭。 这一年,父亲没杀埝。他一直辗转于城市里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
5 后来,我的五妹、三妹、六妹相继考上了理想的院校,那时,学校都并轨了,学费相比以前高多了。我已经在外成家,我卖掉自己还没来得及装修的房子,主动和父亲一起供妹妹上学。父亲来往于土地和工地之间,二妹已经招了上门女婿(家乡称弟弟)。弟弟要和父亲一起供妹妹上学,可是父亲拒绝了,父亲要凭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女儿养大成人。 与其他农民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父亲首先种好土地,然后才去打工挣钱。旱地是粮仓,水地是庄户人家的钱袋子。父亲把所有的水地都轮种了大蒜和玉米。寒冷的冬天,庄户人大都坐在炕头暖和、打牌、闲聊,父亲用自行车载着大蒜走街串巷叫卖:“卖蒜啦,峪口大蒜啦!”早上5点多就出发了,晚上11点多才回来。母亲和我们经常站在村头等啊等…… 就这样,父亲靠着土地和打工,供妹妹们一个个毕了业。等到妹妹们在外面结婚成家了,父亲终于可以放松了。我们劝他把土地交给弟弟,让他们种,别再干了,到几个女儿家轮着住,安度晚年。 这几年,我们几个都在各自的城市买了房子,还清了房款,生活逐渐稳定下来。三妹带父母在她武汉的新家住了三个月,陪着父母在武汉长江大桥散步,坐轮船,逛公园,六妹带着父母游北京逛西安。弟弟拆掉了家里的旧房子,建了五间两层小洋楼,三个孙子健康聪明,父母过着平静幸福的晚年。但是,父亲不论在哪个女儿家,只要估摸着到了农忙时节,他就立马要回家。他时刻惦记着他的土地。 记得有一天,我在电话里劝父亲别到地里拼命干活了,父亲在电话里说,咱们家的旱地只留下一块离家近的种了麦子,其余的都不种了,国家施行退耕还林,都种了树,咱家种了核桃树和花椒树。父亲开心地说,那块种麦子的旱地,平展,不用人力了,播种收割都用联合机器。国家现在政策好,取消了农业税,种树还补贴粮食,这可是从来没有的啊,种小麦玉米国家还补贴钱…… 听他的口气,好像是还要在土地上大干一番的样子,我有点担心他的身体,父亲和母亲都有心脏病,我希望他们的晚年能够离开土地在城市安度。我们有这个能力。 自从父亲做了肾结石手术,特别是突患心梗停止脉动紧急抢救之后,我反复劝他,你要服老,不要拼命干活了,现在的生活好了,粮食充足,钱也够花,您该尽的责任都尽到了,您应该享福了,我们做女儿的都有养老的义务,您也让我们尽尽义务。 就在我们计划着说服父母离开土地时,一向健壮的弟弟(二妹的丈夫)突然离开了人世。父母和二妹还有我们都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三个幼小的孩子忽然之间失去了他们最爱的爸爸,父母失去了孝顺的儿子,二妹失去了相依为命的丈夫,而我永远失去了敦厚善良的弟弟……我故乡的家,顷刻之间失去了顶梁柱……从未在我们面前流过眼泪的父亲,放声痛哭。年迈的双亲几乎在一夜之间白了头发,苍老下去。 我们抱头痛哭。父亲放声痛哭了一次之后,再也没有流泪,他叮嘱我们不要在二妹跟前哭。 我年近花甲的父亲再次成为我们家庭的精神象征,他用他的行动劝说母亲和二妹面对现实,三个孩子还小,生活还得过下去。他又像壮年一样,全身心扑在了他的土地上。他更加细致地给土地做着美容,他把土坷垃碎成柔软无比的丝绸……他把蛐蛐带回家里,用麦秆做成精致的房子,他在花池里种下的南瓜和丝瓜,爬上了二层楼的围栏……我三岁丧母的父亲,以自己的方式,从小练就了化解悲伤的功力。普通的柳条在他手里会被编织成精巧的篮子、背篓;原本同样贫瘠的土地,一经他的双手,就变得肥沃,打出双倍的粮食…… 我年迈的父亲,学会了打牌、下棋,他不再拼命地干活,他在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他不能倒下。他轻松自如地做着他的土地。他仿佛拥有了更多的时间,他自由自在地规划着土地,蒜地里套种玉米,玉米地里套种豆子,地垄上种辣椒……他把平面的土地做成了充满立体感的艺术。 如今,村里早已没了牲口的踪影,也再没有背着筐子割草的孩子的身影了。机器早已经把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村民们过着城市一般的生活,洗澡,看电视,旅游,上网……人们不再起早贪黑,他们一觉睡到自然醒。可是,一想到土地上忙碌的我的父亲,我还是很难过。我是那么想把我的父亲从土地上带到城市,从此离开劳作,过我认为安逸的生活。 每次踏上家乡的土地,总觉得熟悉而又陌生,我常常问自己,你爱这块土地吗?实际上,我在外游离的日子多于在家乡生长的日子,回到家乡,看到的多是陌生的脸孔。每次看到沧桑的父亲,因劳累和悲伤浇铸的花白的头发,因经常暴晒的黝黑的面容,青筋暴露的粗糙的手,我的心都会痛,可是父亲分明用他的笑容告诉我他过得很好,不用挂念。 但是,我多么希望,我劳碌一生的父亲和母亲能够在晚年离开土地,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城市。当希望一次次成为奢望时,我开始反思自己,我的父亲在城市里生活的日子真的快乐吗?他因为用不惯座便器每天早上宁肯到公园找公共厕所;他因为不习惯没事做,每天把家里的地板擦了又擦…… 也许,土地里的父亲才是快乐的自在的。正如我站在讲台上是快乐的,痴迷文字是自在的。孝顺并不是非得带他离开土地。此时此刻,我甚至认为,土地并不是具象的泥土的组合,它更是抽象的精神集合。每个人的心灵里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每当迎来一批新生,我如农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耕耘。每当送走一批学生,我像父亲站在丰收的庄稼地一样,挥着汗水,满心喜悦。 原来,我一直行走在父亲的土地上。
一个人格更健康的人,通常更有能力面对压力,更有能力做出选择,更有能力面对痛苦,有更成熟舒服的人际关系,他的潜能被开发出来得更多,所以相对各方面的能力会更强,这个能力当然包括挣钱的能力,所以他的生活会相对轻松舒服。这也是为什么心理咨询可以帮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