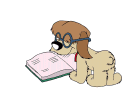但是,从中亚近代史的角度,尤其是沙俄在中亚地区统治政策的角度来看,《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是沙俄自十六世纪在鄂毕河流域立足以来,首次将行政管理体制扩展到哈萨克草原东部地区,以科层管理方式统治哈萨克人。这标志着沙俄对中亚地区的统治由此前的羁縻政策转向建立行政机构,以逐步吸纳新征服领土和臣民,并为十九世纪在中亚的进一步扩张奠定了基础。从法典文本的角度来看,1822年颁布的《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是此后沙俄颁布的中亚各地区管理条例的奠基之作。无论是同时期的《奥伦堡吉尔吉斯人条例》(1824年),还是十九世纪中期征服草原地区之后颁布的《七河省和锡尔河省管理条例》(1867年)、《草原地区临时管理条例》(1868年)、《草原诸省管理条例》(1891年),各版条例均在不同程度上继承1822年条例开创的统治原则,在政策细节上酌情删改。因此,对1822年条例文本的解读不啻为研究沙俄在中亚统治政策最为重要的切入点。
国内外学界此前对该条例的关注相对较少。[3]欧美和俄苏学界对沙俄统治政策的研究在地域上将重心置于河中农耕区,时段上主要关注1867年之后;而将十九世纪前半期定位为军事征服史和外交史,故较少关注其制度建设的面向。[4] 当代哈萨克斯坦学界的相关著作主要服务于上世纪90年代独立之后建构国族主体性的诉求,其叙述重点在于描述沙俄的征服和本地民众的反抗,仅少数学者关注沙俄具体的政策实践。[5]本文旨在以1822年条例文本为基础,阐述该条例所蕴含的主要统治政策,及该体制对沙俄在中亚地区扩张带来的影响。

▴
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的肖像画
(М. М. Спера́нский, 1772—1839)
1822年《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颁布的历史背景
《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在政治史和制度史层面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在废除哈萨克中玉兹汗位之后,该条例在名义上继续维持“苏丹”(султан)、“毕”(бий)等传统哈萨克社会精英的统治地位,以沙俄当局力量为草原地区划分牧场,调停氏族部落间冲突,并提供医疗、防疫和荒年粮食供应等基础设施,维系游牧生活方式的延续;但实则以要塞军力为后盾的行政管理体制将部落精英规训为帝国边地基层官僚,以帝国法律压缩传统游牧社会习惯法的适用范围,以草原空间分割和边界管理防止大型游牧政权兴起,以商贸、文教和社会服务吸引游牧人弃牧从农。在部分承认草原游牧传统的基础上,该条例为沙俄边疆当局深度介入哈萨克社会提供了一套系统方案,并为后续逐步征服整个草原地区,以及在草原地区以南的河中农耕区大规模用兵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军事基础。受限于草原地区的政治形势,条例规定的一系列机构和职能并未在颁布之后迅速实现。但它为之后半个多世纪沙俄在草原地区的政策明确了方向。
1822年条例名称中的“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сибирские киргизы)所指的是大致分布于哈萨克草原东部,即额尔齐斯河以西以南至巴尔喀什湖的哈萨克游牧民,地域上对应今哈萨克斯坦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6] 生活在哈萨克草原东部地区的哈萨克中玉兹和大玉兹于18世纪中期归附清朝,故草原东部在19世纪沙俄逐步强占吞并之前曾为清朝领土。俄文文献中所谓“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这一概念与沙俄对哈萨克人的认知有关。1734年奥伦堡建城后,活动于哈萨克草原西部的小玉兹哈萨克人在俄文文献中常被称为“奥伦堡吉尔吉斯人” (оренбургские киргизы),主要由驻扎在奥伦堡的军政主官管辖。与此对应,活动范围在哈萨克草原东部的哈萨克中玉兹部众被称为“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其相关交涉事务在1822年以前由西伯利亚总督管辖。这一概念在地理上的边界,亦与沙俄十七至十八世纪在西伯利亚的扩张和统治密切相关。其中,沙俄当局以要塞线维持其在鄂毕河—额尔齐斯河流域的统治,而要塞线本身也成为划分地域、标识人群的文化符号。
1822年斯佩兰斯基对西伯利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之前,沙俄当局处理草原东部哈萨克人的管理机构为由二名官员组成边区委员会,隶属于驻扎鄂木斯克的西伯利亚军团司令。边区委员会管理居住在要塞线附近或要塞线内的哈萨克人事务,对要塞线外的哈萨克人则无权管辖。[7]该机构对哈萨克中玉兹内部事务介入程度有限,旨在笼络汗王和苏丹以使其保持名义上的臣属地位。1819年瓦里汗去世。此时主政西伯利亚的斯佩兰斯基抓住机遇,宣布不再承认中玉兹汗位,并推动新条例的出台。1822年7月22日,沙皇谕令正式颁布《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
1822年《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所见新管理体制
1822年《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的正文共计十章319条。其中,第一至六章(第4条至第253条)为条例的主体部分,规定新管理体制的机构组成和职权范围。这一新体制由西西伯利亚总督和鄂木斯克省长两级俄罗斯政府与由哈萨克人推选的边疆地方基层政府组成。在边疆上层统治机关方面,哈萨克草原东部地区事务由西西伯利亚总督统筹,具体事务由辖境接临草原地区的鄂木斯克省长及其公署(省公署)负责。
在行政层级方面,鄂木斯克省下设区(округ)[8],依相对于西伯利亚要塞线的地理位置分为内区(внутренний округ)和外区(внешний округ)。外区为草原东部地区哈萨克人游牧地区,因此也是1822条例所规制的主要对象。区下设乡(волость),乡下分阿吾勒(аул)。阿吾勒由50至70帐(кибитка)游牧户组成,相当于农耕地区的村落。每个阿吾勒由其内部哈萨克人推举产生的阿吾勒长(аульский старшина)管理。乡由10至12个阿吾勒组成。乡的划分往往对应某一哈萨克氏族(род)。各乡的主官被称为苏丹(султан)。乡苏丹可指定一名助手,并配有通晓俄语和鞑靼语的书吏。在阿吾勒和乡的基础之上,区由血缘上较为亲近或地缘上相邻的15至20个乡组成。
1822年《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的核心内容是在草原东部地区引入行政管理体系。在鄂木斯克省管理机关之下,各外区的管理机关为区衙 (окружный приказ)。区衙由大苏丹(старший султан)担任主席,另有由鄂木斯克省长指定的二名俄罗斯人代表(заседатель)[9]及二名选举产生的哈萨克人代表为区衙成员。区衙按照条例规定的编制配备书吏、翻译和口译员。
该条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所谓“选举”制度。1822年条例尝试在区和乡两级建立任期制和选举制。条例中规定,区衙建立之前,须先进行阿吾勒长和乡苏丹选举。阿吾勒长选举每三年举行一次,可以连选连任。阿吾勒长的选举以口头方式进行,以简单多数原则选出。其当选的人选需呈报区衙,由区衙允准,但区衙无权更改选举结果。如区衙对某阿吾勒选举的人选有异议,可呈报省长。[10] 乡苏丹的选举规则和任期与阿吾勒长选举类似。一旦当选,“其苏丹头衔可依照嫡长原则世袭;但在一些情况下,依照习惯,在征得乡公社(волостное общество)同意的前提下,乡公社可另选苏丹,但不得在未经省公署同意的情况下向此人授予权力。如果苏丹没有继承人,则从其兄弟或近亲中推举候选人,但也需要经过乡公社和省公署允准。同样,如果整个苏丹的支系绝嗣,也要经过同样的选举和审批流程。”[11]而不再主管乡事务的乡苏丹,尽管不会被剥夺“苏丹”称号,但也不得介入乡事务的管理。条例相关条文并没有详细规定阿吾勒长和乡苏丹选举的具体投票和计票程序。此类细节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出台的条例中得到完善。
相比乡级政府层面一旦当选便拥有世袭特权的乡苏丹,区衙首脑大苏丹则有更为严格的选举和任期制度。区衙的大苏丹须从下辖各乡的乡苏丹人选推举而出;而区衙的两位哈萨克代表则可以从乡苏丹、毕或阿吾勒长的人选中推举。区衙成员的人选均需得到省公署允准。大苏丹的任期为三年,区衙哈萨克代表的任期为两年,均可连选连任。[12]
在基层司法领域,条例将涉及哈萨克人的司法案件分为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三类。刑事案件包括叛国、谋杀、抢劫及牲畜扣押(俄文:баранта,西里尔哈萨克文:барымта)和抗法等类。此类案件一概由区衙审理,并受省法院监督。行政诉讼涵盖对阿吾勒长、乡苏丹、大苏丹和区衙会议哈萨克代表等土著官员的诉讼案件。原告需依行政级别向高于被告对象一级的行政主官提起诉讼。
包括盗窃在内的诉讼案件(исковые дела)则交于阿吾勒和乡中的毕(бий)处理。此类案件均以口头方式、依据哈萨克的宗法习惯处理,并在判决后立即执行。如原告对毕官的判决不服,可以书面方式向鄂木斯克省长提起上诉,请求再次审理。而毕的资格可因审判不公而随时被中止。[13]值得注意的是,1822年条例尝试在乡以下实行行政和司法分立原则:条例规定,在乡和阿吾勒两级,乡苏丹无权干预司法。普通民事诉讼案件由毕官受理,而刑事与行政诉讼案件则主要有区衙受理。1822年条例并未明确毕官的产生方式。
1822年条例所规定的哈萨克基层政府以区衙为“区—乡—阿吾勒”三级行政体系的权力中心。区衙有永久驻地,且以书面公文处理日常案件,以俄语和鞑靼语登记簿册。日常事务中,如区衙成员出现分歧,案件依大苏丹意见处理,但各方意见须登记在册,提交省公署(第71条)。乡和阿吾勒两级的主官在日常行政中主要以口头方式下达政令,但涉及国家经费开支的活动,区、乡和阿吾勒三级均须以简便方式依照相关法律记账。大苏丹、区衙哈萨克代表、乡苏丹以及区衙和乡苏丹随从文员均根据编制从沙俄边疆当局获得薪金和补贴。区衙另有省公署支发的办公经费,以及用于赈灾、医疗和教育的拨款(第117-119条)。区衙配备有作为警察力量的哥萨克卫队(отряд)。哥萨克卫队由沙俄要塞线上的哥萨克调拨,一般常驻于在区衙所在地;特殊情况下分拨驻扎到乡,为沙俄控制草原地区基层社会的主要力量。
为强化沙俄当局作为哈萨克官员权力来源的印象,1822年条例独辟一节规定上述哈萨克官员的行政级别。大苏丹在当选之日即获得沙俄陆军少校军衔(相当于八等文官),且在服务三个任期之后,有权向当局申请沙俄贵族(дворянство)身份。区衙中,其他官员均不得获得高于九等文官的品级。乡苏丹的级别相当于十二等文官。阿吾勒长和毕如没有获封官衔,则视同俄罗斯内陆的村长。[14] 条例第50条明文规定,“所有被选任的吉尔吉斯人首领,在没有上级政府的同意下,均不得自行确定权责。他们仅仅是上级政府授权通知人民的地方官员。”除赋予哈萨克基层政府职官品级观念之外,条例尤其重视建构选举和授权流程的仪式感。条例试图将大苏丹和区衙代表的选举大会塑造成新体制下的重大仪式。[15]

▴
前排居中者为着沙俄军官服装的大苏丹
概言之,新体制突破了十八世纪沙俄对草原地区实行的羁縻统治传统,以民众推举加官方授权的方式形成乡和阿吾勒执政精英,并以这两级哈萨克官员为基础,推举出区级大苏丹和二名哈萨克代表。这一体系将此前沙俄边疆当局对哈萨克游牧社会的干预制度化:一方面,当局以选举之名使得游牧部落社会内部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公开化、对当局而言“可视化”。另一方面,在行政流程上,通过建立省公署监管区乡选举,区衙监管乡、阿吾勒选举的制度,哈萨克基层政府的合法性表面上依然来源于游牧部落和氏族的选举,而沙俄边疆当局的授权则变得日益重要。
1822年条例的主要目标在于建立一套适用于草原地区的统治体制,但新管理体制并非彻底另起炉灶。在官号方面,新体制沿用了作为部落和氏族首领的“苏丹”称号,但极大地束缚了苏丹的权限。“毕”在传统哈萨克社会的地位因时而异。权位高者,有传说中在十七至十八世纪初分管三玉兹的托列、卡兹别克和艾伊铁克。但在1822年条例所建立的新管理体制下,毕成为了乡和阿吾勒两级司法体系的一种职务,仅有权受理民事诉讼案件。尽管如此,官号的制度化有利于新制度在草原地区生根,让部落精英和普通牧民逐渐接受相同头衔背后大相径庭的权力内涵。
画土分疆——1822年条例对草原空间的划分和维持
将土著精英整合入科层制管理体系仅仅是整个1822年条例所规划管理制度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对哈萨克草原东部地区的空间划分和空间秩序的维持。尽管1822年条例仍明确以血缘为基础划分阿吾勒和乡,但在承认血缘原则重要性的同时,沙俄当局通过诸多手段强化内外边界观念,进而将区—乡—阿吾勒的纵向科层组织与横向的空间划分结合,旨在限制游牧人的移动性,抑制游牧社会跨区域的联合潜力。
条例第一章标题即为“划界”(Разделение)。条例要求依照区—乡—阿吾勒三级行政单位划分沿额尔齐斯河西伯利亚要塞线以西以南的哈萨克草原东部地区。各区边界的划分由俄要塞线军需官负责。区边界一经划定,各区衙“权力不得超越起行政边界”(第10、60条)。条例强调,“每个区的居民未经地方长官允许不得越界”(第9条)。各区被禁止在其它区衙辖境内自行缉捕罪犯和逃亡者,而须通知逃人所在区境的区衙以采取措施。在乡边界层面,条例同样强调由行政边界来设定权力实行的空间范围:如乡边界划定后,同一氏族被划入两个乡,则乡苏丹不可管理两个乡的事务。“在乡公社同意的情况下,权利可交给其子或兄弟;否则需要通过选举产生新的乡苏丹”(第35条)。乡苏丹不得在辖境以外的乡行使权力,即使其他乡的哈萨克人与苏丹有血缘关系(第107条)。阿吾勒长在没有通报苏丹的前提下不允许自行游牧转场,且只有在苏丹下令的前提下,才可与其他官员发生职务上的联系。上述条文旨在以行政原则取代传统的血缘纽带,重新建构各层级的游牧人组织。
条例所关心的不仅是被视为俄属哈萨克草原东部地区内部边界的划定。根据距离要塞线的远近,各区被分为近线区(близ-линейные округи)和边境区两类(пограничные округи)。属于边境区一类的各区须在远离要塞线的一侧树立界标,以宣示沙俄主权界线。同时,边境各区应配备规模更大的哥萨克卫队,以卫戍边界。区衙成员应率领哥萨克卫队巡查边界,平日由边境各阿吾勒长负责巡查事务。在重要地块应树立永久性界标(第77-80条)。条例规定,“禁止俄属哈萨克人越过此边界游牧”(第78条)。
边界一经划定,对跨界移动的管控也会相应匹配。除上文提到常规的游牧活动以外,条例重点关切的尚有两类移动方式:商贸与牲畜扣押。在商贸方面,条例规定,区衙有义务收集过境商人和商队的信息,并提供保护。所有异国人士(иноземец)在进入第一个俄属边境区时,区衙负责出具出具书面文件。如异国人士意图经要塞线进入俄内陆省份,区衙须护送其至最近的要塞线关卡。异国人士通关须出示在区衙出具的书面文件。如异国人士或商旅行进路线未经区衙驻地,则可由边境某乡苏丹处出具书面文件,供要塞线关卡查验。乡苏丹出具的书面文件须上报区衙(第69、83条)。所有经要塞线入内陆省份的异国人士和商旅均须经关卡查验,其书面文件须上报省公署。在处置非法越境的异国人部分,条例仅提到对清朝臣民的处理方式:扣留后送交省公署,并由省公署遣送至恰克图(第86条)。对旅行者和商队的管控,能有效体现新管理体制空间划分的意义,并在日常的行政实践中强化区乡两级哈萨克官员对行政边界的认知,进而强化沙俄当局试图塑造的边界观念,限制游牧群体的移动性。
边界管控的另一重点是抑制牲畜扣押行为。牲畜扣押是游牧社会常见的一种现象。它指的是某游牧民或氏族因感到遭受来自另一个人或氏族的不公正待遇,通过劫掠、扣留对方牲畜的方式以迫使对方谈判补偿。在完成谈判后,扣押牲畜的一方往往会交还全部牲畜,或扣留一部分作为赔偿。[16]然而此类朴素的草原传统容易诱发氏族乃至部落间的冲突,以致形成长期的纷争。因此,对于试图在草原上建立稳固政治秩序的沙俄当局而言,牲畜扣押不可作为单纯的民族习惯对待。1822年条例第五章将涉及哈萨克人的司法案件分为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案件三类,而牲畜扣押与叛国、谋杀和抢劫一道被定义为刑事案件,须由区衙派人侦查、区衙会议审判且受到省法院监督(第206-214条)。乡苏丹作为氏族中由影响力的人物,往往与牲畜扣押事件的当事方有血缘或地缘上的联系。故条例规定,“如苏丹被指控放任抢劫或牲畜扣押,甚至卷入其中,则立即移送法庭”,接受刑事审判(第256条)。
除此之外,条例专辟一节,规定草原地区的防疫隔离措施。而这部分措施的设计,则充分利用了前述行政体制,将对潜在病疫的应对转变为强化行政建置的有利因素。条例将应对疫病的主要责任置于区衙。一旦出现牲畜倒毙现象,区衙一方面需要立即通报临近的要塞线长官;另一方面应以乡为单位,切断疫病乡与无疫病乡之间的联系,通过草原地区的哨所士兵传递信息。区衙要警告无疫病乡的哈萨克人尽快转场,远离出现疫病的牧区,并针对易感畜群建立隔离措施。而乡苏丹和阿吾勒长必须尽向普通牧户传播讯息,以防疫病扩散(第236-242条)。
需要指出的是,在1822年条例落实之前,草原地区并非如后世文人想象的自由世界:游牧氏族和部落之间同样存在依习惯、协商或暴力划分的牧区边界。而1822年条例首次在哈萨克草原东部地区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行政层级及对应的行政边界。与此相应,行政边界在规范意义上划定了各级哈萨克官员的权力边界。结合要塞线海关、司法和防疫隔离等制度,沙俄当局通过对放牧、迁徙、牲畜扣押、疫病防治等行为的规制,使行政边界逐渐从文本变为现实,进而使之成为沙俄草原统治秩序的基石。
限牧劝农:1822年条例对牧人定居的引导
如前文所述,设官立制和划分疆界均为抑制草原地区兴起大规模游牧政权的手段。而要从根本上消除游牧集团对农耕社会的军事威胁,最终需要通过游牧民的大规模定居和转入农耕生活方式来实现。1822年条例对各级政府在信息收集、房舍修建、土地分配和利用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发展草原地区经济,首先需要准确的人口和土地资源的统计信息。1822年条例要求各区衙登记本区下辖各乡苏丹和阿吾勒长的真实姓名和驻地变动情况;每三年进行一次各乡和阿吾勒的帐户及异动信息的普查,以便统计人口数量;如辖区内有建筑或不动产,则要求登记该地块信息(第68条)。
其次,边疆当局以拨款激励区衙修建各类房舍,将区衙驻地发展为具有商业意义的集镇。1822年条例规定,每个区都必须建造以下四类建筑:1)区衙办公房舍和区衙文员的住所;2)神职人员的礼拜寺;3)可服务150至200人的诊所;4)哥萨克卫队的兵营(第124条)。为此,各区衙必须制定预算,上报省公署,并按照预算执行建筑计划。在引入1822年条例的最初五年,执行该条例的各区哈萨克人享受五年的免税优惠,但鼓励哈萨克人自愿捐赠牲畜、物品或货币以支持医院、学校和福利机构房舍的建设。捐赠物资均需由区衙登记造册,呈报省公署。
相对准确人口和土地信息是后续区衙依照条例分配土地使用权的基础,而土地利用政策则明确包含引导牧人定居和参与农耕的目标。1822年条例规定,每个区须指定地块,划分适用于农牧、手工业和商业的土地。大苏丹有权使用区衙驻地周边5-7平方俄里的土地;每位区衙哈萨克代表有权使用2平方俄里土地;每位区衙俄罗斯代表有权使用1平方俄里土地。区衙翻译和文员的土地分配标准对标同级哥萨克军官。而驻扎在草原地区的哥萨克卫队成员,每人可分得15俄亩份地用于维持生计。此外,如有自愿从事农耕的哈萨克人,每人可获得15俄亩土地,由区衙监督其耕种和使用状况。条例要求,区衙的俄罗斯代表和哥萨克卫队成员应作为表率,积极参与农耕和建筑修造工作。如有可能,应发展园艺、养蜂和其他副业。应吸引苏丹、阿吾勒长和普通哈萨克人积极利用区衙下辖的各类设施,为他们提供帮助、支持和建议,以吸引更多人适应定居生活。如已分配土地在五年内未经耕种或使用,则区衙有权收回并重新分配(第167-183条)。
值得注意的是,1822年条例的起草者还尝试在草原地区引入包括公共粮食供应、医疗、防疫、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服务机构,以吸引牧人转入定居生活。条例以17条的篇幅规定公共粮食供应政策,第150条开宗明义:“即使小麦并非吉尔吉斯人的主要食物,为了预防他们在牲畜倒毙或染病而陷入饥荒,以及为鼓励他们务农定居,要在每个区设立官粮铺(казенная хлебная продажа)。”[17]官粮铺的定位是为草原地区牧民提供基本的粮食供应,尤其是在灾荒时期平抑粮价。为此,鄂木斯克省为每个新开设的外区准备3万卢布贷款。待官粮铺的资本规模达到初始资本的2.5倍之后,可开始还贷。条例对官粮铺的利润、销售价位和销售量都作出具体限制。各区官粮铺的主管和护卫人选由省公署确定,其薪金从官粮铺营业利润中支发(第150-164条)。值得注意的是,第160条规定,官粮铺以俄国货币进行粮食交易。而1822年条例规定的对哈萨克牧民征税方式仍然是值百抽一的牲畜实物税(ясак)。[18] 可见,除维系基本的粮食供应外,在草原地区开设官粮铺还有推广沙俄法币使用、将边疆地区纳入俄属西伯利亚地区经济循环以吸引哈萨克人定居农耕的目的。
在医疗卫生方面,条例规定,每个区须配备两名医生(лекарь),为官兵和居民提供医疗服务。每个区须建设固定的诊所,为区内贫穷和重病的哈萨克人提供诊疗场所。诊所内的勤杂人员可雇佣贫穷的哈萨克人,其开支由各乡和阿吾勒承担,日常运营由区衙管理。医生应该为患者的需求在区内走访。此外,医生应该尽可能劝说哈萨克人接种天花疫苗,由当局提供物质激励(第229-235条)。
在文化和教育方面,条例起草者认为哈萨克人当时的信仰更倾向于原始多神崇拜,而非正统的伊斯兰信仰,故存在吸引大多数哈萨克人皈依东正教的可能性。条例鼓励省公署联系教会,向草原地区派遣传教士。如果某个区皈依东正教的人数达到一千人,那么鄂木斯克省必须拨款建造教堂,并要求教会分配牧师。如牧师顺利进驻,应与省教育部门长官配合,尽力筹款建立教会学校,教授哈萨克学童俄文读写、算术和法律。乡苏丹和阿吾勒长的子弟如自愿入俄罗斯学校学习,可由当局公费支持。学童在接受俄文读写和算术训练后,如家长同意,可担任公职。除上述待建的草原地区教会学校以外,其他俄罗斯学校均应以各种方式支持哈萨克人就学。条例还承诺,每个哈萨克人都有权依法送子弟到俄罗斯学校接受教育(第243-249条)。在社会福利方面,条例要求各州厅准备五至十顶帐篷用于社会救助,为受伤、年长、有精神疾病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帮助(第252-253条)。
条例甚至考虑到为接受定居生活方式和俄罗斯教育的哈萨克人打开社会上升通道。条例规定,在乡公社和地方长官允准的情况下,帝国境内的哈萨克人有权赴内陆省份谋生。每位哈萨克人均有权申请加入帝国的某一阶层(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ословие),有权登记注册为某一行会的成员。在转入其他阶层之后,哈萨克人脱去异族身份,转而承担相应阶层的权利义务(第268-271条)。



▴
《突袭》
俄罗斯画家维列夏金的画作
(В.В. Верещагин,1842-1904)
作为哈萨克草原东部历史转折点的1822年条例
尽管1822年条例全文通篇以主权者的口吻规定哈萨克草原东部的政治事务,但事实上,要塞线外的第一个外区区衙的开设要等到条例颁布近两年之后。1824年4月8日,鄂木斯克省下辖的第一个外区,卡尔卡拉林斯克区(Каркаралинский округ)完成大苏丹[19]和区衙代表选举。当选大苏丹的是托热出身的图尔逊·钦吉索夫(Турсун Чингисов)。[20]为支持区衙工作,鄂木斯克省选派鄂木斯克亚洲学堂的三名学员赴该区担任下辖乡苏丹的书吏。区衙哥萨克卫队由要塞线抽调的250名哥萨克组成。在区衙开设的政令中,省长要求哥萨克携带农具和种子,在区衙周边从事农垦,以免对区哈萨克牧民造成经济负担,并通过发展农业吸引牧人定居。区衙开设之时,区、乡和阿吾勒的划界工作尚未落实。同年4月29日,鄂木斯克省开设第二个外区——科克切塔夫区(Кокчетавский округ)。这两个区的共同特点是存在支持沙俄新管理体制的游牧社会精英。而区衙所需的书吏、译员、作为护卫的哥萨克卫队和最初五年的运行经费均由俄当局提供支持。尽管区下辖各乡仍存在反对新管理体制的势力,两个区依然顺利开设。[21]
在19世纪30年代,该省陆续开设阿亚古兹区(Аягузский,1831年),阿克莫林斯克区(Акмолинский,1832年),巴彦阿吾勒区(Баян-аульский,1833年),乌奇布拉克区(Уч-булаксий,1833年),阿曼卡拉盖区(Аман-Карагайский,1834年)五个区。与条例文本中的核心关切相似,各区开设时,西西伯利亚总督和鄂木斯克省长的关注的重点主要为以下五方面:1)乡和阿吾勒精英对区衙首脑选举和宣誓效忠仪式的参与;2)区和乡两级行政单位边界的划分;3)对牲畜扣押行为的严格限制;4)对农垦和商贸的支持;5)吸引尚未效忠的哈萨克氏族加入俄籍、采纳新管理体制。[22]
这一时期途经哈萨克草原东部地区的俄国军政官员和旅行家从不同角度记述了草原地区的变化。至19世纪60年代,沙俄已经稳固控制了草原东路。19世纪中期的俄国旅行者鲜少记载哈萨克氏族越额尔齐斯河游牧的情形。尽管区和乡的边界尚未稳固,行政体系带来的区域划分观念已经存在。在引导定居方面,阿克莫林斯克区衙驻地发展成区域商贸中心,为商人与牧民自发交易的场所。值得注意的是,到访的俄军政官员大多抱怨该地区的管理制度尚无力将俄罗斯文化扩展到本地社群,但鲜少有人反映本地统治不够稳固。
作为斯佩兰斯基一生宏大立法事业的一部分,《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以319条的篇幅建构了一整套结合草原游牧传统的沙俄统治体制。以吸纳哈萨克部落精英为基础的科层制管理、并由此建立行政区划和边界管理制度,均为防范草原地区形成跨地域游牧政权的手段。而要从根本上消除欧亚历史上游牧帝国出现的可能性,彻底将农耕管理体制建立在草原之上,则需要以多种措施吸引牧民转入定居生活。配合欧洲近代出现的火器制造、要塞修筑、土地勘测、后勤管理等技术,1822年条例所推行的官僚制、行政区划和定居政策在相对有限的人员进驻和资金投入的条件下,经十数年基本覆盖草原东路。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之后,沙俄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如疾风骤雨一般。但“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沙俄在新征服领土上的制度建设却鲜为前人学者关注。在沙俄对中亚地区的统治体制发展过程中,1822年条例具有奠基性作用。在1822年之前,沙俄更多强调对草原东部地区因俗而治。而1822年条例在行政上将冠以“苏丹”名号的部落首领转为边疆当局领导下的区、乡和阿吾勒各级官僚;各区乡划定疆界,以区乡和要塞线力量限制越界游牧;并通过土地利用、税收、文教和社会保障等手段优待定居人口以削弱游牧传统。概言之,1822年条例标志着沙俄对哈萨克草原地区的统治政策从羁縻转向建置,旨在抑制草原地区大规模游牧政权的出现,将草原地区从“危厄边疆”逐步转为帝国纵深腹地。
注释:
[1] 关于斯佩兰斯基在西伯利亚总督任内的改革措施概述,参见徐景学主编:《西伯利亚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35-239页;Marc Raeff, Siberia and the Reforms of 1822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6), pp. 39-128.
[2] 二十世纪初之前的俄文文献常以“吉尔吉斯人(Киргиз)”或“吉尔吉斯—凯萨克人(Киргиз-Кайсак)”称1926年之后世人熟知的“哈萨克人”,以“喀喇吉尔吉斯(Каракиргиз)”或“野石吉尔吉斯(Дикокаменный киргиз)”称1926年之后的“吉尔吉斯人”。本文在引用史料文献时为为贴近原文,译为“吉尔吉斯人”;而在一般行文中则使用当代更熟悉的“哈萨克人”译法。相关讨论参见巴托尔德著,张丽译:《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吉尔吉斯简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84-585页;另见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坎著,中国社会科学院丝绸之路研究所等译:《哈萨克斯坦简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4页。
[3] 其中,最为重要的著作是孟楠:《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7-91页。该作品在俄文术语译名方面为笔者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4] 如皮尔斯(1960)叙述时间点从1867年开始,仅以一章概述1867年之前以军事行动为线索概述沙俄征服中亚的进程;考察重点也集中在锡尔河、撒马尔罕和费尔干纳三省。马丁(2001)考察的时段同样以19世纪60年代为开端。这与她参考的档案时段有关。重要英文著作参见Richard A. Pierce, Russian Central Asia, 1867-1917: a Study in Colonial Ru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0);Virginia Martin, Law and Custom in the Steppe: the Kazakhs of the Middle Horde and Russian Colon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urrey: Curzon Press, 2001); 重要俄文著作如Терентьев М.А. История завоеван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Т.1–3. СПб. 1903–1906; Халфин Н.А.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1857–1868). М., 1960.
[5] 例如,哈萨克斯坦学者坎的通史作品充分体现独立后民族主义史观视角下的历史叙事,参见格奥尔吉·瓦西利耶维奇·坎著,中国社会科学院丝绸之路研究所等译:《哈萨克斯坦简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10-125页。当代哈萨克斯坦也有一些学者从事微观层面的制度史研究,如苏丹加利耶娃关于沙俄统治下基层哈萨克官僚的系列研究,参见Гулмира Султангалиева, “Казахское чиновничества Оренбургского ведомств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и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XIX),” Acta Slavica Iaponica (Томus 27, 2009): 77–101.
[6] 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地域大致对应今哈萨克斯坦的北哈萨克斯坦州、阿克莫拉州、卡拉干达州一部分、巴甫洛达尔州、东哈州等地。
[7] 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译:《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314页。
[8] 关于俄文术语округ的译法,孟楠因将губерния与область均译为“省”,故将округ译为“州”。格奥尔吉·坎的《哈萨克斯坦简史》中译本译为“区“,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一卷)》中译本译为“区”。因当下国内学界一般将欧亚地区各国一级行政区область译为“州”,为避免造成误解,笔者将округ译为“区”。
[9] 关于此处对区衙之заседатель的译法,孟楠著作译为“代表”;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一卷)》中译本译为“陪审官”。因区衙成员所承担职能不仅限于司法,译为“陪审官”可能产生歧义,故本文取孟楠一书译法。
[10] Масевич М.Г.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Казахстана. Т. 1. Алматы, 1960. С. 94.
[11] Масевич М.Г.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Казахстана. Т. 1. Алматы, 1960. С. 94.
[12] Масевич М.Г.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Казахстана. Т. 1. Алматы, 1960. С. 95.
[13] Масевич М.Г.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Казахстана. Т. 1. Алматы, 1960. С. 103–104.
[14] Масевич М.Г.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Казахстана. Т. 1. Алматы, 1960. С. 95.
[15] 关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首领继位仪式中抬毡环节的讨论,参见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第24-48页;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35-336页。关于哈萨克传统中汗继位仪式的抬毡行为记载,参见捷连季耶夫著,武汉大学外文系译:《征服中亚史(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5页。
[16] 关于牲畜扣押的相关描述,国内较早的研究参见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63和366页;英文学界的主要研究参见Virginia Martin, Law and Custom in the Steppe: the Kazakhs of the Middle Horde and Russian Colon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urrey: Curzon Press, 2001): 140–155. 但马丁没有注意到的是,与哈萨克草原地区牲畜扣押相关的立法至少可追溯到1822年条例。
[17] Масевич М.Г.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Казахстана. Т. 1, Алматы, 1960. С. 100.
[18] 即牧户每占有一百头牲畜,每年须向当局上缴一头作为赋税,参见Масевич М.Г.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Казахстана. Т. 1. Алматы, 1960. С. 100.
[19] 哈萨克斯坦著名思想家阿拜·库南巴耶夫的父亲库南拜(Кунанбай Оскенбаев)于1849-1852年担任该区大苏丹。
[20] 此人之后连续六个任期担任该区大苏丹(1824-1843),且其子图列克(Тулек)和谢尔江(Сержа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也出任过该区大苏丹。
[21]Письмо султана Сасыма Аблайханова оренбургскому военному губернатору с просьбой закрыть Кокчетавский окружной приказ. 24 июня 1825. // Масевич М.Г.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Казахстана. Т. 1. Алматы, 1960. С. 137.
[22]Правила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аркаралинского окружного приказа, составленные омским областным начальником. 11 апреля 1824. // Масевич М.Г.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Казахстана. Т. 1. Алматы, 1960. С. 112–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