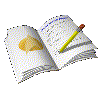|

然而,这本书在1830年问世之时,却无人问津,甚至一度被当成禁书,因为它的内容过于真实,甚至它的作者借主人公于连之口,挑战了法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相当于动了别人的奶酪。由于这本书一出版,就遭到各方面的攻击,作者司汤达也成了当时上流社会最不受欢迎的作家。这本书的命运也极其悲惨,两次出版,印数不到800册,还都卖不出去。多年之后,这本书让无数人着迷,令无数作家和评论家青睐,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人都大加赞赏,高度肯定了此书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遗憾的是,当这本书吸引了无数读者的时候,它的作者司汤达,也已经躺在坟墓里近百年了。活着的时候,作品无人问津,幸好他还是国家公务员,不然,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但他死后多年,却凭借《红与黑》取得了与巴尔扎克比肩的文学地位。“到1880年,将有人读我的作品”,“到1935年,人们将会理解我”。 
011783年,在法国东南部的一个保守的中产阶级家庭里,出生了一个孩子,名叫亨利·贝尔。这个名字我们也许不熟悉,但他就是日后闻名世界的著名作家司汤达。司汤达的父亲,是一个极度保守的律师,他敌视一切革命,惧怕任何新的思想,在那老旧的传统里,维护着自己的地位。和父亲不同,司汤达的母亲,思想开明,崇尚自由主义,司汤达爱自己的母亲。司汤达6岁的时候,也就是1789年,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革命到来,意味着很多东西都将发生改变。司汤达亲历了这样一次变革,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90年,司汤达七岁,他亲爱的母亲意外去世,司汤达的人生,陷入了另一种困境,生性沉默寡言的父亲,对司汤达非常严厉、冷漠,还把他交给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教育,希望将他培育成一个保守的教徒。然而,此时的司汤达,在外祖父的影响下,渴望自由,父亲的安排让他感到痛苦。1796年,司汤达进入了外祖父主持的学校就读,这是一个不同于大革命之前的学校,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它传授科学文化,传播进步思想。在这样的氛围里,司汤达成了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观念,深深扎根在他心里,影响了他的一生。越是对自由充满向往,司汤达就越是讨厌那些充满束缚的东西,于是就越要反抗。多年后,他在自传《亨利·勃吕拉的一生》中谈到,这种反抗,是因为他极端厌恶平庸事物,蔑视金钱和商人,强烈向往自由意志、力量和奔放的热情。
02在学校,司汤达和同学相处得不算愉快,他用自己的方式成长着,在文字方面,他极其敏锐,获得过一些奖项。1799年,16岁的司汤达,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了。他踌躇满志地来到巴黎,想考入更高等的学校继续学习,其实这都不重要,他只是想离开固有的环境,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时候,革命如火如荼,可是对16岁的司汤达来说,这一切都不重要,谁做元帅谁做总统,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他宽阔的肩膀,并不打算用来肩负国家的兴衰,红红的脸蛋也不代表革命的热情。他想到巴黎去,在那里邂逅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他梦想着有英雄救美的机会。然而,现实无情地碾碎了司汤达年轻的、狂妄无知的梦想。当他走进巴黎,高大的屋子之间狭窄、肮脏的巷子,充满着腐败食物的气息,还有穷人身上的汗臭味。他在巴黎住了几个星期,没有看书,一连几个小时信步走在街头,去欣赏那些美丽的姑娘。照着镜子,司汤达对自己的长相尤其不满意,一张粗俗的哈巴狗似的脸蛋,略圆,红得像猴屁股,还肥胖,宽大的鼻子长在这张脸上,尤其不合。虽然眼睛里面闪闪发光,充满不安的好奇,但谁能看到啊,谁又愿意去看啊。就连穿的衣服,也是一身过时的绿色大衣,圆圆的身体,如同一个绿色大西瓜。他明明生活在巴黎,却像被巴黎排挤在外,他感到孤独。可是这一去,司汤达更加自卑了,朋友一家,住在漂亮的大房子里,过着舒适的生活,而这一切,都在提醒着他,他就是一个穷鬼,囊空如洗,不名一文。他只想随心所欲的活着,可他又难以忍受自己一事无成。但他不知道做什么,直到有一天,司汤达被叫去抄写信件,每天早上10点开始,一直到深夜。他不停地抄写信件,抄写报告,直到手腕酸痛,但他不知道这没完没了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尽管战争很可怕,但年轻的司汤达感觉,比起干讨厌的事情,他更喜欢战争。
03就在司汤达做梦渴望自己的艳遇的时候,革命却在热烈地进行着。他加入了拿破仑领导的军队,并通过亲戚的关系,谋得了一个光鲜的职务。1800年,17岁的司汤达,随着拿破仑的大军,一起南下意大利。他长得很粗笨,为人却很机巧,很能说讨人喜欢的话,他装得勇敢,装得聪明,宁愿撕下自己的舌头,也不愿问一个愚蠢的问题,他不会让人看出他的愚蠢和无知,也不会让人看到他内心的恐惧。可是有些东西,还是会在不经意之间表露出来,听见远处传来的炮声,他露出惊奇的表情:随后,司汤达官运亨通,没参加过一次战役,就被任命为骑兵少尉。但他不想上阵杀敌,他只想上街看女人,米兰的大街上,到处都是时尚的女人。这让他觉得,自己像女人,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他去了妓院,找了妓女,出来的时候,他健康的身体染上了疾病——梅毒。几年的军旅生涯,让他感到厌倦,他不愿再干这样的事情了。他喜欢这样的生活,既不用命令任何人,也不用当任何人的手下。在剧院里,他爱上了一个女演员,那个女演员去了马赛,他就追到马赛,成了商品铺里的一个小伙计。她像梦想一样走进他的生活,与他生活在一起,白天他手上沾满白糖和面粉,晚上就去剧院把她接回家。
04爱情的幻想破灭之后,1806年,司汤达又回到了军队,继续在拿破仑的军队里任职,成了一名军需官代表。这个身份,让他备受尊敬,每当他走在街上,那些德国小镇的士绅,就脱下帽子毕恭毕敬地行礼。和身份地位一起落在身上的,还有种种恼人的烦恼,上司要他从被劫掠一空的辖区搜罗七百万战时税,还要他在混乱的辖区建立秩序。高官厚禄,让他钱包鼓着,年近三十的他,桃花运居然很好,比二十岁的时候更好。他的日子,再一次过得很舒服,他在没有战争的地方安安静静地读书。他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渐渐地,也能更加正确地看待世界,他变得更自由,也更接近最真实的自己了。他参与到战争中,却如同局外人一样,他成了军人里古怪的一员,看着看着,他看到了艺术的价值。他有钱,也有时间,为了消遣,他打算去写一本艺术史。可是写着写着,他又不甘寂寞了,生活这么富足,这么充实,这么美好,他不能将时间浪费在写字台上。
05在战场上,司汤达就是一个闲人,没有功劳,也没有苦劳。他观察战争,越来越觉得百无聊赖,于是,他悄悄带上各种书籍,作为消遣。拿破仑战败后,司汤达狼狈而逃,带去的书,写的日记,全都没了。他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逃回了普鲁士,连皮肤都被俄罗斯寒冷的冬天冻裂了。拿破仑下台了,司汤达在军中的好日子结束了,革命失败了,旧王朝复辟,司汤达觉得,前途一片黑暗:他彻底受够了战争的折磨,他再也不想命令谁,再也不想听命于谁。从今往后,除了最自然的事,除了创作这件最艰难的工作,他什么都不想做了。这是他的黄金时代,他全身心地把自己奉献给音乐、艺术、写作,也把自己奉献给爱情和女人。“爱情之于我始终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我唯一的大事。可是,这些女人大多数并没有给我以爱的荣幸。不过,她们确实充实了我的生命,而在她们之后,就产生了我的作品。” 经历了几段感情,失败的失败,被骗的被骗,就是没有一段成功的,司汤达不再执着于爱情了。他实在想不通,想要一段美好的感情,想要好好爱一个人,为什么就这么难呢?他打算研究一下爱情,便写了一本《论爱情》,可是《论爱情》的命运,和他的爱情一样失败,11年里,只卖出去17本。人就是为了幸福来到这个世界的,人人都可以幸福地活着,但并不是人人都能获得幸福。
06然而,到了1821年,即便在意大利,司汤达也不再自由了。统治者和当局对“自由”深恶痛绝,所以,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人,是一个危险的人,很容易陷入危险的境地。司汤达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意大利处境艰难,仔细一想,还是走为上计。已经到了不得不走的时候了,他不走,人家也会将他驱逐出去。于是,他回到巴黎,回到那间属于他的阁楼里,专心从事创作,他要写书,写书,写书。他也许不会知道,他日后能名垂青史,恰恰就是因为他这个不太重要的业余爱好。他活得越来越穷,写书又没有一点收入,他精心创作的《论爱情》,遭到了出版商无情的讥讽:书卖不出去,生活还要继续,他只能每天领 5块钱的救济金。我希望把我直接运送到公墓,安葬费不得超过三十法郎。 在这个忧伤的月份里,他第四次写遗嘱,但一次都没派上用场。可是第二天早上,朋友们来了,司汤达的心情又好了,有个朋友在桌子上看见一张纸,纸上写着:《于连》。朋友们听后,都很兴奋,鼓励司汤达打起精神,加油创作。得到鼓励的司汤达,果真开始写这部小说了,不过,《于连》这个标题被他改成了《红与黑》。可是那时候,《红与黑》并没有给司汤达带来任何名利,反而给他带来无数麻烦,这本书一度成为禁书,而司汤达,也因为写了这样一本书,遭到了上流社会的嫉恨。我死到临头,并不怕人看不起,但我仍要说几句,我生不逢时,不属于你们那个阶级,在你们眼里,我不过是一个出身卑微而敢于起来抗争的乡下人。 我看到有些人,他们并不认为我年轻而值得同情,反而想杀一儆百,通过惩罚我来吓唬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出身下层阶级,备受贫穷煎熬,却又有幸受过良好教育,敢于混迹于有钱人引以为豪的上流社会。 他那副既愚蠢又迟钝,但是神气活现的样子在议会里很吃香。实际上,这些先生最痛恨有智慧的人。基佐和梯也尔先生惹他们讨厌的地方不正是他们的“智慧”吗?实际上,他们所以容忍有智慧的人,仅仅把他们当作一种既必需又讨厌的东西罢了。 
07《红与黑》出版后,并没有给司汤达带来钱财和名声,反而带来了一堆麻烦。但他似乎是幸运的,政府的任命很快旧来了,他再次成功国家大院里的职工。一开始,他也很认真地编写报告,认真工作,可是他发现,他的上司压根就不看他精心编写的报告。此后,他将工作交给部下,而他自己,则做自己的事情。这一份工作,司汤达干得很舒服,不用干活,还有丰厚的工资,他舒舒服服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谈情说爱,自由自在。然而,这也没有持续多久,他的守护者落马了,新上任的领导听说司汤达拿钱不干事,大骂其不干人事,一道严厉的命令来到了司汤达手里,要他立即到岗。于是,司汤达愁眉苦脸地穿上制服,结束了悠闲的生活。他很不情愿,顿感心力交瘁,他的身体已经很坏了,身体肥胖而沉重,每走一步,颤抖的身子都要用力拄一下手杖。更不幸的是,他得了中风,连工作也干不成了,只能回国养老。可是,曾经绚丽多彩的巴黎,在他面前,突然失去了颜色,死神冰冷的手,触摸着他,他懒得打量这个灯火闪烁、车水马龙的世界。他沉寂着,偶尔出来走走,孤独的背影像慢慢离去的黑点。
081842年3月22日,司汤达像往常一样,拖着肥胖的身体,疲疲沓沓地走在热闹的大街上。他的眼睛已不再发光,而是变得萎靡不振,由于中风后遗症,他的嘴角不停地抽搐。夜晚,巴黎的大街上,灯光忽隐忽现,思司汤达视野一片模糊,他在交易所大门前,倒下了。人们将他送回他居住的小屋,屋里到处都是纸片、笔录、是许多尚未写完的作品,还有很多笔记本。“我认为,死在大街上一点也不可笑,只要不是故意这么做。” 他死得热热闹闹,死在大街上,可是他下葬的时候,为他送葬的,只有他的三个亲朋好友。他是一位作家,可是在他去世时,报纸上连六行讣告都不肯登载。在司汤达的遗嘱里,他的所有遗物,包括所有遗稿,全都交给表兄处理。出于对死者的崇敬,他的表兄却希望出版司汤达的作品全集。他们撬开盛放遗稿的箱子,一大堆纸,密密麻麻的字迹,杂乱无章。一个不被同时代人认可的作家,穷得只有自己费尽心力写就的书。
09面对如此多的遗稿,整理的工作太庞大了,以致于让人望而生畏,就连司汤达的遗嘱执行人,也只能无奈地叹气:没法办。这些文字都杂乱无章,不合时宜,就这样被丢进某个角落,一放就是几十年,那个装着这些稿子的箱子,被送来送去,最后被送进图书馆当作档案封存起来。这一放,就是四十年,没有人想到要将之打开看一看,理一理。而司汤达已经出版了的作品,也还在静静地躺着,等着突然被发现。而司汤达的墓园,也被遗忘在某个角落,长满荒草,直到人们想要修建一条公路,需要铲除他的坟,才有人突然想起,这是一位作家。他的预言确实成真了,在他死后几十年,人们在图书馆沉寂的角落里,发现了司汤达。“二十世纪的某一位评论家会从十九世纪卷帙浩繁的作品中发现司汤达的作品,并且比我们的同时代人更公正地对待它们。” 他又说对了,距离司汤达去世,已经180多年了,可是司汤达的作品,依旧很受欢迎,尤其是那本在当时饱受抨击的《红与黑》,更是令无数人喜爱。有些人之所以不被同时代的人理解,是因为他走在了同时代的人前面,他需要给那些人时间,他们才能理解他曾经说的,做的,向往的。
10作为一个作家,司汤达四十多岁开始小说创作,十几年当中,写了几部长篇,几十部短篇。他只是写,然后将这些作品留在世界,这些作品带给他的,也只是死后的名声。可是他写过,他的生命就因此丰满过,灵魂饱满着倾泻而出,化作一篇篇文字。他对爱的渴望和想象,最终被他写进作品之中,成为一个个饱满的文学形象,就像《红与黑》里面那个深情的夫人。他活了不到六十年,是坚定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追求享受,但并不与时代同流合污,他勇敢地抨击自己的时代,他有这样的勇气。因为他让时代远离他,所以他的作品是不受时代限制的;因为他只过最内在的生活,所以他的影响充满活力。 一个人越是跟着他的时代随波逐流,他就越会随着时代一起死亡。一个人越是在自己身上保留真正的本性,就越能凭借其本性流芳百世。人生有无数种活法,但我们永远都要记得,我们的活法,只是无数种活法之中的一种,因此,我们随时可以走出去,重新换一种活法,去活,去爱,去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