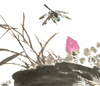希望从“人心”深处寻找制度问题的解决之道,看似深刻,其实不得要领,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10月19日,我在《东方早报》发表文章《“复礼”解决不了社会不文明问题》,与前一日早报刊发的秋风先生文章《中产阶层需要“复礼”》进行商榷。23日,秋风先生发文《首要的事情是信赖人心》,反驳我的观点。但秋风先生的新文章并不能说服我,特再撰文回应。
首先,关于当前中国社会不文明和失序的主要病因,我的诊断其实与秋风先生不同。秋风先生认为,不文明和失序的发生是因为“中国人,尤其是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部分成员不明礼,不守礼;再进一步,当代中国城市社会也没有形成礼”,我却认为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的许多重要规则本身既难以让人信服,又难以让人畏服,所以得不到遵守,而造成这些规则难以让人信服或畏服的根本原因在于规则自身的缺陷。
规则要想被信服,至少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规则本身是合乎正义的,因只有正义才能够诉诸人的理性而说服他;二是规则的制定必须尽可能经由被要求服从者之手,因经由自己同意的规则是最可能被遵守的规则。规则要想被畏服,关键不在于其所规定的惩罚之严厉,而在于其实施之确定不移:只要你违反了规则,规则规定的相应惩罚就必然会降临到你头上。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具备切实有效的违规行为发现机制和惩戒机制。但是非常遗憾,当前中国社会的许多重要规则恰恰缺少这些要素。这样的规则,对本性就倾向于无拘无束的人而言,是很难被他们遵守的。(这层意思原已写入前一篇文章,发表时因版面限制被删除,或致秋风先生误解)
因此,我并不是说“要让人们遵守规则,就需要让人们看到,整个社会都在遵守规则”。我只是认为,必须让大多数社会成员看到,通行的规则至少基本是可信服或可畏服的,否则就不可能说服他们遵守规则。如此,我自认为并不存在秋风先生所指责的“循环论证”的问题。
秋风先生认为不能“只从规则上、制度上找到解决制度问题的方案。解决问题的更好出路,在于回到人心,通过教化,养成国民之敬”。我却认为,制度问题恰恰只能从制度求解,希望从“人心”深处寻找制度问题的解决之道,看似深刻,其实不得要领,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人心诚然有善端善性,有可信赖的一面,但人心同样有恶根恶柢,有永远需要警惕提防的一面。是否可以信赖,主要的根据不是人心本身,而是人心所处的环境。所以十八世纪的德国思想家康德将道德修养描绘成一个理性与欲望之间旷日持久搏斗的艰苦过程(参见《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实践理性批判》)。
秋风先生举“最美”一词在网络上的流行,可以证明“天命之心涌动在每个人身中”,但却证明不了“天命之心”将会决定一个人的一贯行为。所以,网络舆论虽然会对社会中偶然出现的善事给予迫不及待的赞美,但赞美者躬行此类善举的却不多。既然如此,将制度设计与改进的基础主要放在对人心的信任上,就未免太过轻率了。
而且,即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回到了人心,也不一定就能够解决制度问题。因为在资源有限的人类社会现实的限定条件下,仁爱的逻辑一旦扩大推广开来,并非不可能导致难以解决的矛盾,正如当代美国思想家约翰·罗尔斯所指出的,“只要仁爱在作为爱的对象的许多人中间自相矛盾,仁爱就会茫然不知所措”(见《正义论》)。相反,“哪怕是一群魔鬼,也可以为自己立法以组成一个社会,只要他们有此智慧”(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即使是自私自利的一群人,也可以在利益博弈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道德存在,这才是良善制度的真正价值所在。
秋风先生承认,在当下中国,经典的教诲难以约束一部分人背弃经典所要求之德行,但是他仍然乐观地说:“但这又怎样呢?哪怕只有一半、三分之一的人坚守自己的信念,社会就有了善种。”秋风先生忘了还是不知道,即使是传统儒家中国中那些一辈子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儒生,实际也没有几个人真正做到了终生“坚守自己的信念”。
我可以举例:宋元易代之际,虽然有文天祥那样坚贞不屈的人物,但更典型的其实是南宋京师临安危急时内外大臣“表里合谋,接踵逍遁”的情景(见元代学者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七“朝臣逍遁”条),和南宋灭亡后投降元朝的宋室旧臣之众多(南宋末年诗人汪元量《醉歌十首》之十有云:“昨日太皇请茶饭,满朝朱紫尽降臣。”)。在儒家最为注重的民族气节上尚且普遍表现得如此不堪,遑论他乎?这些终生浸淫儒学的儒生尚且如此,遑论泛泛读上几句儒经的现代人?
秋风先生在其文章的最后指责我和诸多现代知识分子、官商精英一样,是制度决定论者,“不信赖人心,甚至根本否认人心的存在。因此也就否定教化对于优良社会治理的决定性价值”,并质问我们:“人如果由制度决定,那什么可以变革制度呢?”
其实,我们这些所谓的“制度决定论者”从来就不认为制度决定一切,我们只是主张制度比道德更根本更重要。我们也充分肯定教化的作用,但我们绝不天真地把这种作用抬举到至高无上的“决定性”地位。我们认为人心的一些幽暗是永远不可能被完全克服的,而且这些幽暗对人的行为一般起着更具决定性意义的作用,特别是对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是如此。因此我们主张,至少在设计制度时,应该像托马斯·杰斐逊所主张的那样,把制度奠立在“慎防或嫉妒”而非信任的基础之上(参见《1789年肯塔基决议草案》)。
我们同意人具有能动性,不完全由制度决定,也同意人可以变革制度;但是我们认为变革不良制度的驱动力,主要不是少数所谓“君子”的善心,而是源于自私自利的平常人的自利心。
“我并不否认人常常是温和而公正的,而且有些人在努力变得卓越;我也不否认有些人为对上帝的恐惧和上帝的爱、为对同胞的慈善和爱所动。我仅仅断言,当我们考虑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政府的真正起源时,所有的这些都没有值得一提的足够后果。”十七世纪的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的名言和人类数千年的历史提醒我们,将社会政治奠基于仁心美德的假设之上,结果永远只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