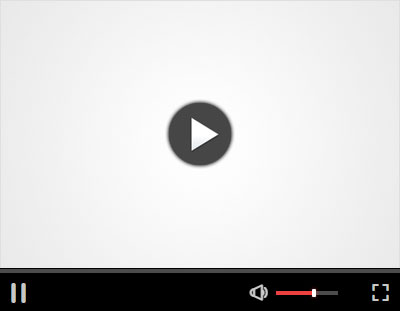“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些让你魂牵梦萦的地方,而之所以会如此,多半是因为那个地方在你人生的道路上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并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徐天进老师而言,山西省曲沃县的曲村镇便是这样的地方。 从曲村开始,与考古结缘,当他们一点点地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时,就像选择了一次次重新出发的旅程,千帆阅尽,留在心中的就是一片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风景。 在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即将到来之际,本期约读邀请徐天进老师为我们讲述他与曲村的考古杂忆。
徐天进:曲村考古杂忆 来自山西博物院 00:00 29:41 徐天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主任,山西博物院理事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田野考古、商周考古研究,曾参与山西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等遗址的发掘,曾主持陕西周原、周公庙遗址的发掘。主编《吉金铸国史》《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藏商周青铜器》,撰写《天马—曲村》西周墓葬部分及《晋侯墓地的发现与研究现状》《周公庙遗址的考古所获及所思》等论文。
说起曲村,我想绝大部分人压根儿可能就没听说过,当然也不会知道那是一处什么样的所在。在考古学家到来之前,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北方村落。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一系列的考古大发现之后,这里才开始有些名气,而所谓的名气也多半仍是在考古圈内或学术界,因为考古学家在这里解开了晋国始封地之谜。曲村,位于山西省的南部,属曲沃县管辖,西南距县城约15公里,好像是县城之外曲沃县最大的古镇,有一千户左右的人家。因为这里也是镇政府的所在地,所以村子的模样显得比一般的村落更气派一些。民居错落分布,村中有一条东西横贯的主街,街边有商店、医院、邮局、小饭馆。镇政府也在这条街上,居于村子中心的位置,这里原来是宋金时期的一座寺庙——大悲院,早些年尚存的献殿和东西厢房都被用做办公室了。据古建专家说,大悲院的建筑对于研究我国宋金时期建筑的结构法式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所以被指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曲村——这个山西的古老村庄,是我考古生涯真正开始的地方。在这里,我从一个考古专业的学生变成了一个考古专业的教师。从1982年到1994年的十二年间,因为参加北京大学和山西考古研究所的合作发掘,我大概在这里前后住了四年多时间。1994年以后也几乎每年都会回去,停留的时间或长或短。为什么?因为考古,因为北京大学在那里安了一个考古之家。和曲村结缘,完全是因为所学的考古专业。1982年夏天,我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有幸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随邹衡先生继续学习商周考古。那年的下半年,刚好是邹先生带北大考古专业78、79级的本科生到曲村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实习。这也是北京大学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在曲村遗址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发掘。先生考虑到我和另一位同时入学的王占奎田野发掘的训练不够,需要进一步的强化训练,或者说是需要补课,所以就安排我们报到后直接去工地,再参加一个学期的田野考古实习。开学后,我们先到北大注册报道,再赶往曲村,比大部队稍微迟到了几天。这年参加发掘的带队老师加学生近40人,从村东到村西,三两人一组,分散住在村民家中。这次的发掘规模是历年来最大的一次,揭露的面积达7000多平方米,除了大量的各类遗迹之外,还清理了不同时期的墓葬350多座。其中主要是西周时期的墓葬。1990年秋,和邹衡先生等在曲村考古工作站(自左至右:李为民、张辛、刘绪、邹衡、稻田耕一郎、徐天进、宋建) 在曲村的半年时间,我经历了从发掘、调查,资料整理,再到编写发掘报告的全过程,因为发掘规模大,揭露遗迹多,出土遗物也十分地丰富,所以工作量自然也就大。那时的山西用电十分紧张,发掘日记、器物的测绘和发掘报告,多半都是在昏暗的烛光下完成的。通过这次实习,我才开始真正了解或理解了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基本方法,对田野考古的重要性有了切身的体会。这次发掘,我的运气似乎也不错,挖了两座西周墓葬都有青铜器随葬,这对第一次发掘西周遗址的我来讲,印象非常深刻。事隔30多年了,我还记得两座墓葬的编号,分别是M6121、M6130。当然也还记得铜器的组合、特征等等。实习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编写发掘报告,因为材料太多,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可能完成所有发掘内容的报告,所以要求本科生同学只需完成部分发掘区的内容即可,而邹先生则要求我们(研究生)写出完整的发掘报告,为完成实习任务,那个寒假基本没有休息。正是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奠定了我之后能够胜任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从此,我才算是真正走上了考古的正途。1988年是我永世难忘的一年,也可以说是我的再生之年。那一年下半年的田野考古实习由同门大师兄刘绪和我一起带队,他负责遗址区,我负责墓葬区。在墓地发掘的过程中发生了一次重大的事故。查看当年的工作日记,还清楚地记着事发的时间是10月21日下午两点半左右。一座正在发掘的金元时期的墓葬(M6464)发生了严重的塌方,那时我正从这座墓葬的竖穴墓道下去,准备给墓室的封门砖拍照记录,人尚未到底,就听到墓口上有人惊呼:“徐老师,危险”!没容我有任何反应,墓壁就轰然垮塌了,我的身体瞬间被塌方的土所掩埋,随即失去了知觉。经过同学和民工们近20多分钟的奋力抢救,才将我从墓坑中“发掘”出来,还好,一息尚存,捡回一条命。后来听同学们描述抢救的过程,真是有些惊心动魄,把有的同学也吓坏了。因为这次事故,让我对发掘现场安全的重要性有了几乎是付出生命的体验,自那以后,不论是在哪里发掘,都会格外注意安全问题,也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故。之后我听人说,刘绪师兄当时曾和别人说,如果我要是抢救不过来的话,他就不干考古了。因为那年我们住一个宿舍,床对着床,中间隔一张桌子,每天都会面对面聊天。而事发那天,当他回到宿舍时,看到对面人去床空,可能触景伤情,才生出这样的想法。非常幸运,我没有死,他也坚持继续干考古了,并且成为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因为有了这次不同寻常的经历,我和86级的同学在师生之情外,还增加了生死之交的情谊。也因为这次意外的事故,让我和曲村有了别样的情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一年,我30岁。考古发掘的成果在经过科学的整理之后,多会以发掘报告的形式出版发行,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使用。这也是考古研究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部好的发掘报告需要做到全面、客观、准确地反应发掘的内容。天马—曲村遗址1980至1989年间的发掘成果于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刊行,16开本,1000多页,共四卷。20年后的今天来看,依然还是一部少有的大型考古报告。报告的整理和编写从1989年开始整理,到正式出版差不多也花了10年的时间。发掘10年、整理10年,20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而这项旷日持久的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邹衡先生的指导并亲力亲为下完成的。关于邹衡先生对晋文化考古的贡献,之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吉琨璋先生曾在“约读”上有过很详尽的介绍,我就不再重复了,我这里只想再补充几点似乎微不足道而对我影响至深的小故事。《天马—曲村》报告凝聚了恩师邹衡先生的大量心血,也是他毕生考古事业中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先生在拟定报告的整体框架之后,根据田野工作的情况,分配给我们几个弟子承担不同章节的内容。其中两周墓葬的部分安排我负责墓葬形制和陶器的部分,而邹先生自己则承担了最复杂、最麻烦的铜器和其他小件器物的整理和编写任务。共641座墓葬,遗物中数量最大的是各种装饰品,报告中公布的玉、石珠8857颗,玉、石管珠1666颗,海贝9960枚(371座墓)。其中M6197一座墓就出土了各种小珠子2153颗,这些珠子多大呢?直径在3毫米左右,而且有的已经破碎,邹先生反反复复不知数了多少遍,才有了准确到个位数的数据。那时邹先生已经60多岁了,而且还是高度近视,要点清这些数据并非易事。邹先生在曲村工作站二楼西侧的库房,独自一人伏案工作的场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正是因为有这样和先生共同工作的宝贵经历,让我对先生的学问之道有了深切的体会。求真、求实、严谨的治学精神,在这样看似简单的小事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天马—曲村》报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报告中所有的器物图(尤其是陶器),几乎都是我们自己画的,而不是像通常的考古报告那样,多由技工来完成。邹先生要求我们每个人自己动手绘制所负责部分内容的遗迹和遗物图。我想,先生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我们应该或必须掌握绘图技术,这是一个考古工作者应该具备的技能。另一方面则是希望我们通过绘图可以更细致、深入地了解、认识器物的特征。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先生对我们的绘图水平和质量有基本的判断,也就是说,他认为我们画的图够格,可以发表。我和上海博物馆的宋建先生,绘制了1118件两周时期陶器的底图,另外,按先生的要求,我还对全部墓葬(641座)的平、剖面图和发掘记录及随葬品实物逐一核对、校改,全部清绘一遍。这样的工作在曲村工作站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说实话,在当时日复一日重复做同样的事情,也会觉得枯燥,乏味,甚至觉得是在浪费时间。但事后再回头看时,发现在我自己的考古生涯中,那段时间的工作经历实在是最可珍贵的,通过这样的工作所积累的经验使我受益至今。
2018年在曲村考古工作站库房(36年前发掘时写的器物标签还在) 当我们参观山西博物院晋国霸业的展厅时,稍微留意一下就不难发现,几乎半数的展品出自晋侯墓地。1992年—2000年,是曲村遗址考古的第二个阶段。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晋侯墓地的发现和发掘。这个阶段的工作由我的另一位恩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李伯谦先生负责。非常幸运,我也有机会参与了这次发掘工作。晋侯墓地的发现是缘于盗墓。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在山西(乃至全国)兴起了一股盗墓之风,而且愈演愈烈。直至今天似乎仍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在太原新开的博物馆——山西青铜博物馆,其中相当部分的展品,即来自近年来公安机关打击盗墓犯罪收缴的文物,数量惊人。曲村遗址晋侯墓地的发掘持续了八年的时间,共发掘了九组19座晋侯及晋侯夫人的墓葬。因为抢救还算及时,墓葬没有被完全破坏。其中10座保存完好,9座不同程度被盗掘。我参与了第一次(M1、M2)和第五次(M32、M91、M92、M93、M102)的发掘,在发掘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的曲折和困难,可以说是一言难尽。而晋侯墓地之所以还能有10座墓葬没有再遭盗掘,邹衡和李伯谦两位先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是他们不断的、想方设法的奔走呼吁,才引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并开始对盗墓犯罪活动展开严厉的打击,在一段时间内遏制了盗掘犯罪行为的蔓延。晋侯墓地的发现和发掘,不仅是晋国考古的大发现,也是西周考古的大发现,更是中国考古的大发现。关于晋侯墓地的学术研究已经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著,归纳起来,其重要意义有以下几点:1.按司马迁《史记·晋世家》的记载,晋国的始封地在“唐”,但“唐”地究竟在哪里?自汉代以来便众说纷纭,有太原说,临汾说,翼城说,乡宁说、夏县说,霍县说,莫衷一是。晋侯墓地的发现,为确认晋国始封地提供了最重要的证据。尽管此前邹衡先生已经提出“天马—曲村遗址”就是晋国始封之地的观点,但还没有如此过硬的证据。因为晋侯墓地的发现,晋国始封地的问题得以基本解决。2.根据出土铜器的铭文,并参照文献的记载,可以比较明确地肯定这九组19座墓葬应该是从晋侯燮父到晋文侯(最后一位晋侯是殇叔?还是文侯?尚可讨论)共九代晋侯及夫人的墓葬。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处年代明确、世系清楚,贯穿西周早晚的墓地。因此,这批材料也是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年代标尺。3.晋侯墓地的发现对研究当时的器用制度、埋葬制度,即所谓的礼制也有着巨大的学术意义。曲村的考古收获,是晋国考古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能够参与其中,是我莫大的荣幸。曲村的考古还没有结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考古学家们去继续探寻。如:第一代晋侯,即唐叔虞的墓葬还没有发现,究竟会在哪里?文献记载晋侯燮父由“唐”地迁至“晋”,若此,“唐”和“晋”似乎并不在同一地,那么,“唐”是否还在他处?虽然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天马—曲村遗址就是西周时期晋国的都城所在,但迄今为止,尚未找到和晋国贵族相关联的宫室建筑,也没有发现和都城相关的城墙类遗迹。所以,晋国都城的寻找和确认仍然是未来的田野考古需要格外关注的问题。在晋侯墓地发掘结束之后,在曲村东南不远(相距4500米)的羊舌,发现了另一处晋侯墓地,在绛县的横水发现了文献失载的倗国墓地;在曲村的东部,今天翼城县的大河口发现了霸国墓地;在曲村的北部,襄汾县的陶寺村北发现了东周时期晋国的墓地。这些接二连三的发现,令人目不暇接,不断刷新我们对古代山西的认识。那么,“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的范围内,这些不同的政治实体或族群,相互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晋侯墓地自1992年开始发掘,不觉已经27年过去了,在遗址上建成的晋国博物馆也已经开放多年。而我自己承担的两座墓葬的正式发掘报告还没有完成,为此深感愧疚,这是我欠山西的一笔债,也是欠曲村的一笔债,希望能够尽快还清,以不负这片土地之恩。在徐天进老师的讲述中,我们听到了他对曲村的眷恋之情。在这期录制结束后,徐老师提笔为《约读》栏目留下了珍贵的墨宝,激励我们在宣传三晋文化的道路上不忘初心,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