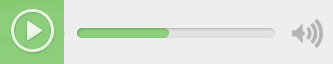我是希锐。
昨日端午,有吃粽子的习俗,相传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本想借着这个节日,从毛主席的点评视角,聊聊屈原其人,并将两人结合起来写,总结出一些精神内核,落到现实问题上来。
但,尝试写了一些,总感觉立论太空太泛,抓不到重点,删删改改,颇为受挫,不很满意,便搁笔沉思良久。
我觉得毛主席写屈原的那首诗,已经概括得很好了: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写作就是这样,有思路的时候,文思泉涌,没有思路的时候,硬想往外输出些什么东西,总是显得那么刻意和矫揉造作。这倒不一定是完美主义,更像是自我认知局限和间歇性低迷,所造成的写作上的“行动瘫痪”。愈是想写点什么,愈是写不出来,愈是写不出来,愈是感到焦虑,甚至摆烂了。感到某件事情已经无法向好的方向发展,于是索性干脆不采取任何改进措施加以补救和控制,而是任由其往坏的方向继续发展,甚至不想干了。写作也好,平时大家在工作、学习、生活等多方面也罢,都很难一直保持良好状态。偶尔会有倦怠乏力不想干的时候。但有少数人,则选择稍作休息,迎难而上,最终破局而出。从这个标准来看,我们将多数人称之为普通人,少数人为高手。可以说:
真正的高手,遇到困难,往往并不会摆烂,或者说,初期产生一些负面情绪,而后又能很快调整过来。想着端午节的屈原纪念文章暂无太多思路,整个人又有些“摆烂”,便想着,干脆结合毛主席的奋斗经历,聊聊“摆烂”这个话题吧。类似的话题,其实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也跟大家聊过,但再次回顾,细细品读,依旧有不少新的启发收获。当年8月15日,毛泽东和同学乘火车,从长沙来到了北京。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并没有赴法留学,但他成为了这个活动的有力组织者,这锻炼了他的组织管理能力。或许,在他看来,当时更重要的事情,不在于提升学历,而在于按照自我的想法做事。不留学,不考试,想在北京这个大城市生活下去,那只有一条路:学历不占优,资历尚浅,毛泽东想要在北京找到一个心仪的工作,并不容易。所幸,得恩师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来到北大图书馆,在馆长李大钊手下工作,当了一名图书馆助理员。虽说收入差距悬殊,但毛泽东却挺满意,毕竟,比起一般人,八块大洋也不是个小数目了,这也承蒙李大钊的特殊关照。同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自然而然地接触到了北大的圈子、组织各种活动、阅读各类书刊、结识志同道合之人,并开始逐渐明确自己接下来要走的道路。后来,为了方便与其他同学的往来相聚,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人,搬进了故宫后面的景山东街。“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我住在一个叫作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
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这并非夸大其词,刚入社会的毛泽东等人,兜里确实没几个钱。8个男生只能挤在一张炕上,彼此用体温,来抵御北国的寒冷。更令人糟心的是,他们总共就只有3件大衣,没有办法,只得轮流着穿。尽管这群年轻人生活清苦拮据,还常吃捡来的白菜帮子加盐煮,但毛泽东似乎并未因此而停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
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北漂半年后,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回到了长沙。那会儿毛泽东还是待业状态,经过同学周世钊推荐,他成了小学里的一名历史教员。每周6节课,工资依旧不多,但毛泽东并无怨言,他依旧满意。因为他发现,自己能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到社会政治活动中去。一方面,从事一门副业,也在培植一项新的能力,促进自己成长进步。为了响应五四运动,他与何叔衡等人改组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同时还创办了刊物《湘江评论》。做媒体的朋友应该知道,办一份报纸何其不容易,涉及诸多方面。更何况毛泽东办《湘江评论》,多是以他个人之力,俨然那个时代下的“自媒体”。相比现在注册个账号就能发表观点,以前办报纸,可困难得多。毛泽东却顾不上这些,他挥汗如雨、奋笔疾书、思绪万千,常至半夜。“它们在他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朋友回忆)办报如此繁杂艰难,劳力劳心,一般人估计早就选择放弃了,但毛泽东依旧咬牙坚持下来。创刊号印了两千份,立刻被卖完了,只得加印,依旧供不应求。据说,任弼时、萧劲光等人日后会走上革命道路,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了《湘江评论》的直接影响。《湘江评论》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湖南省内,甚至还火到了省外,遍及全国。“《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但好的势头没过多久,《湘江评论》便遭到了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查封。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赴京的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他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发出大量关于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等,并发往各大主流报刊媒体发表。毛泽东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报纸上,被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驱张运动最终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但后续的一些事情,让毛泽东彻底认识到,自己曾经温和改良的路子,是行不通的。于是,从北京回到长沙后,毛泽东把目光开始转向并聚焦到经历了十月革命的俄国。
一方面,是和朋友创办文化书社。毛泽东租了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作为书社的社址。他还从多方筹借资金,努力扩大经营范围,吸收各类马列译著、刊物,并将这里逐渐打造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对内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一方面,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组建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又先后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去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赴俄留学。“几个月来,已看透了。”
“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
“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应该)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1920年12月底,毛泽东收到好友蔡和森的来信。蔡和森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表态是如此的明确和坚决,对于那时候的毛泽东来说,确实少见。“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冒险一点,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何必总陷于一片泥土。——尼采”
即便是伟人,也和普通人一样,难免会遭受各种各样的挫折和打击。一些人可能会选择坚持一阵子,但鲜有人能忍受长时间的曲折往复。尤其是漫漫长夜,黎明将至未至的时候,人最容易放弃崩溃,走极端。我们可能做不到像毛主席那样强大,那样厉害,能够“乱石飞渡仍从容”、“而今迈步从头越”,但至少,我们能从他的经历中,获得一些鼓舞,收获一些启发。路不是等靠要来的,不是空想得来的,而是自己通过不断地试错,甚至经过许多纠结痛苦,蹚出来的。“实际上你会从中穿过,穿过猛烈的沙尘暴,穿过形而上的、象征性的沙尘暴。
但是,它既是形而上的、象征性的,同时又将如千万把剃须刀锋利地割裂你的血肉之躯。不知有多少人曾在那里流血,你本身也会流血。
温暖的鲜红的血。你将双手接血。那既是你的血,又是别人的血。而沙尘暴偃旗息鼓之时,你恐怕还不能完全明白自己是如何从中穿过而得以逃生的,甚至它是否已经远去你大概都无从判断。
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
从沙尘暴中逃出的你已不再是跨入沙尘暴时的你。是的,这就是所谓沙尘暴的含义。”
——《海边的卡夫卡》,村上春树
愿我们都能穿越人生的一个又一个“沙尘暴”,蜕变新生。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