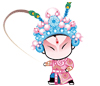1977年,对我来讲可以用大悲大喜来描述。悲的是我们完成到深山老林中的宣传任务,自桐柏深处回归教室,安心读书的愿望和环境刚刚形成,毕业季到来,读书的机会瞬间被终止。刚踏进“二八”年华,就修业期满,经学校考核合格,准予毕业了。只因当时就业形势不乐观,有非农户口的城里人都难以就业,需要上山下乡,去“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我这个出生即下乡的农民后代,回乡种田便成为不二选择。

喜的是在冬季兴修百万方水库的艰苦劳作中,主要目的在于为大家兴修水利鼓舞士气、再接再厉的广播里,竟然传出了让所有莘莘学子几乎窒息的消息—恢复高考!这消息真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让我和大多数只能通过公平竞争途径,去改变自己未来的年轻人,重新燃起选择的希望,确立了新的奋斗目标。
元旦过后,学校的氛围已开始向重视文化学习的方向转换。老师们讲课的时间增加了,态度也认真了,同学们坐在教室的时间也在延长,课堂上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图书室开放的频率也提高了,就连昔日的喧闹声,都呈现出减弱的态势。只是时间较短,变化也很有限。我们回到教室,农历新年就触手可及,老师们只能匆匆结束课程,简单的复习加上简单的考试,放寒假了。
春季开学后,课堂上文化教育的内容才逐渐增加,除了语文教学外,数学和物理等课程的教学内容也有所增加。只是刚刚过去的一系列运动的惯性依然存在,加上“学工、学农”的时间较长,老师讲课不严谨,学生上课无教材,重新走进课堂的师生,大家都没准备好,教学进度缓慢不说,效率也十分低下。
课堂上,老师虽然在授课,却没有教学计划,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学生(至少我自己是)在认真听讲、拼命记录,但全无章法,缺少举一反三式的练习,抓不住重点,解决不了问题。整个学期下来,数学学了曲线这小部分内容,物理讲解的则是电学入门知识——串联、并联,化学、历史、地理、英语差不多是闻所未闻,都与我们无关。
原以为当时全国一样,都没有学习ABC,可后来的同学中有同一届毕业生,他说高中阶段学过外语,让我大跌眼镜。当我质疑我们一届的,怎么可能你学了,而我没有学时,他“嘚瑟”地回复我,那就是你们山里太落后,让我啼笑皆非。语文则是以报纸或其他文章代替课本,讲了些写作手法、中心思想方面的内容。
最可怜的是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对字母“C”的发音,竟引起部分同学的嘘声。因为他的发音,与以前那些用乡音教学的老师相比,独特、“另类”。同学们习惯成自然,以为是这位老师发音不准,便以嘘声回应,想让老师纠正发音。面对嘘声,数学老师只好用“我学外语、教外语,怎么可能发音都不准?”才避免了一场更为激进的“抗议”画面出现。
春风送暧,绿了杨柳,艳了桃李,红了杜鹃,最美人间四月天。只是这春寒料峭,“乍暧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二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在气候变换莫测的时候,农忙季节到了。同学们回生产队支援春耕,确保五一节前,将早稻插完。我很“幸运”,经历了家乡改种双季稻的完整阶段,体验了“早稻冷,晚稻热,搞得社员动不得”,最难将息的磨炼。
学生是插秧的生力军。插早稻经常是上穿棉袄,下穿单裤,赤脚踩在冰冷的泥水里,双手飞舞,将秧苗插进泥土里。如果天公不作美,在阴雨连绵的清晨下田插秧,就得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多次,才能战胜对泥水中寒冷刺骨的恐惧感,开始一天的劳作。我的搭档,是位比我大二岁的女孩,面对面将秧苗插在划行器划出的方块四角,作横向移动。刚开始尚能你追我赶,风风火火,谁都不甘落后,毕竟,二人的工作量是统一计量,一人落后必然影响另一人的工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腰酸背疼的感觉不断强烈,伸懒腰的次数此起彼伏,有了“攀比”之意。
都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可插秧时大家的感觉却是高度一致,那就是累、累、累。长时间、高强度的弯腰劳作,导致肌肉僵硬,全身疲劳,加上冰凉泥水的浸泡,寒气袭人,痛彻心扉,苦不堪言,谁还有心思去想,自己的搭档是谁。
忙完农活回到教室,在老师的指导下,尽量多学一些知识,提升自我,把前期耽误的课程补起来,把失去的青春追回来。
美好的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流失。似乎农忙假期的满身疲惫都未消失,期末考试就来到了眼前,稀里糊涂地走出考场,便被宣布“成绩合格”,准予毕业。黄金屋的大门缓缓关闭,颜如玉的靓丽黯然失色。
与现在的学生相比较,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书包一贫如洗,上学、放学,来去毫无压力;升学不用考试,更别说那解析不尽的密卷,上大学没有应届毕业生什么事,而是从工农兵中推荐;好在就业的时间安排得天衣无缝,学业结束之时,正是“双抢”开始之日,自动到岗,连介绍信都不用。
七月流火,正值抢插晚稻的时候。尽管搭档未变,农活照旧,但烈日炎炎与春寒料峭,差不多就是冰火两重天。除了汗流浃背,皮肤被骄阳直射的烁痛,那舌干口燥、力尽筋疲的感受,无法用文字描述。那感受,直到现在想起,都是谈虎色变,心有余悸。
“双抢”结束,来不及休养生息,冬季兴修水利的准备工作就揭开了序幕。我运气爆棚,成为水利建设的先遣队员,进驻八里之外的山林中,为大部队的到来劈路搭桥,盖棚垒灶。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如果在水利工地帮硬劳力打下手,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路,当然是无可厚非。很遗憾,指挥部将劳动定额分配到大队,大队分配到个人。我使出洪荒之力挖出的土石方,都无法完成每天的定额,挣不到生产队给我核定的5.5个工分。面对无论如何苦干都完不成定额的困境,我朝着“巧干”的方向努力。又经过数日探索,发现投机取巧才是完成每天任务的唯一途径。如是,我毫不犹豫地将前几天挖出的土石方,不断腾挪,变换地点,在初中同学的保护下,奇迹般地顺利过关,连续达标。
10月下旬,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欣喜之后,又如热锅上的蚂蚁,期待立即回到母校,向老师求助,看看是否能寻觅到一些教材,准备复习。谁知刚刚溜回家中,复习的资料都没有找齐,水库工地领导者旋即发现有人“失踪”,寻人口信如电报般飞到生产队里。队长不敢、也不会怠慢,立即找我母亲“要人”。为了生存,并避免得罪队长干重活的悲剧出现,回家一次,尚 不满72小时,便带着遗憾和一万个不情愿,返回了水利建设工地。
那时的施工,全是人海战术,靠的愚公移山式的肩拉手挖。最先进的“工艺”就是爆破,其次是“挖倒方”。前者是在坚硬的石壁上打眼放炮,炸开岩石;后者是在土质松软的地方,通过掏空山体的下方,挖断土方与山体的连接处,让山坡似泥石流一样倒塌,以提高挖土的效率。二种方式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垒大坝的土石方。这两种方式,都存在较大的风险,稍有不慎,便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哑炮的排除和“倒方”坍塌时的预防。就在这年冬天,在其他大队“挖倒方”时,出现了严重的安全事故,一死一伤,一位正值桃李年华的姑娘,被突然坍塌的土方埋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尽管没有学到应有的知识,也没有时间进行复习,我依然报名参加考试。与同龄人相比没有太大的差距。但自“老三届”开始,十年都没有考试,与“老三届”以来的“师伯、师叔和师兄”们同场竞技,我们这些学制短、课堂学习时间也短,课外劳动较多的“后辈”,自称“不学ABC,同样能做接班人”、“敢于交白卷”的一代,考试前还在水利工地“苦干、巧干”,没有复习机会,更别说拥有复习资料的一代,在“徒弟与师傅”的竞争中,不可能有必胜的信心。

11月20日傍晚,我自水库工地匆匆回家,收拾好各种文具和准考证等,时间已经到达二更时分,连抱佛脚的时间都不够,只能休息,为第二天的考试养精蓄锐。
人贵有自知之明。两天的考试结束,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带着失败的阴影,回到水利工地,继续坚持战天斗地的壮举,修理着偌大的地球。
成绩公布之日就是记录我们失败之时!自我们这届之前的几届校友,就唯有一位老师(74届校友,且参加过教师进修班)名列孙山之前,以下几届则被剃了光头。
种子一旦冲破土地的压迫就没有力量可以限制其成长。当恢复高考的基本国策确立之后,“在公布参加体检名单的同时,公布全体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的制度同时建立。这一提高招生考试过程公开、公平、透明的重要举措,宣告了公平竞争时代的到来,并锐不可挡。为我们这群完全不知道后门为何物的农村伢,提供了机会和希望。正是因为如此,要上学就成为我在煤油灯下、自高小的追击问题开始自学的始动力,揭开了我循序渐进、攻难克艰的知识速成之路。
恢复高考的强烈冲击,整整唤醒了十多届毕业生追求知识的梦想。追求知识、持续学习的理念,也在自己的心灵深处生成,初次考试的失败被我视作迈向成功的阶梯。龙门陡开的诱惑,江鲫飞跃的愿景,如野草般疯长。溪河汇川,山坡成峰。尽管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积压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冲击与挤压,但梦想还是要有的,一旦实现了呢!
这一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复出,一个全新的时代揭开了序幕;共和国缔造者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从1966年开始废止的高校招生制度正式恢复。
这一年,我回乡务农,成为地球修理大军中的一员,参加百万方水库的修建工程,深感力不从心的无奈;惊闻恢复高考的消息,让知识改变命运的种子从心灵深处萌芽。
这一年,最流行的歌曲是《祝酒歌》,最吸引人们眼球的电影是《永不消逝的电波》,最有意义的体育大事,是家体委下发颁布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证书和证章的通知。最流行的词语是恢复高考、美酒、理想、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