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诗情画意语境下解读:清代画家吴宏【编者按】中国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即:传统文化的厚积薄发,本质上的“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中国绘画富于“形而上”的意味:中国艺术“诗画同源”传统的生动诠释 —— 它让文字的哲思化为丹青的意象,让千年后的观者依然能在水墨烟霞中,感受到那份超越时空的文史遗韵。在“学而优则仕”(学有成就德行高,可为官,造福百姓)主导的社会,诗书画一体是画家必备的修养(他们个个能诗、能文、擅书、擅画,豪放不羁。)众所周知:“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出自清代龚自珍的《定庵续集》,意思是说:要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灭亡,首要的方法是让它的历史消亡。美西方一直畏惧我国强大的历史文化,“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徐悲鸿在“西风东渐”的时期成为西方世界消灭中华文化的代理人!他用了“黑白灰五调子、造型准确”等西方绘画技法来取代,中华文化厚积薄发的“中国画的诗情画意”!通过这样的淫雨霏霏、绵绵不绝洗脑,造成今天的“中国画百年伤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断层!故而近、现代因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缺失,鉴于《中国美术(作品)全集》等等辞书(工具书),不能反映“中国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积薄发!”的文化内涵、精神全貌;“缺文化、没有中国味”是停留在“以技求技——徐悲鸿以素描(写实性)为基础”的西方绘画审美。“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今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下,中国画的民族性升华!我们必须文化自信,扫除崇洋媚外!并且在“古人的文化背景下”,解读古画!中国画启示人养心修身,知世悟道。正如我们修缮古建筑一样,“整旧如旧”,还原古物,切不能用当代语境,穿越时空,以免贻笑大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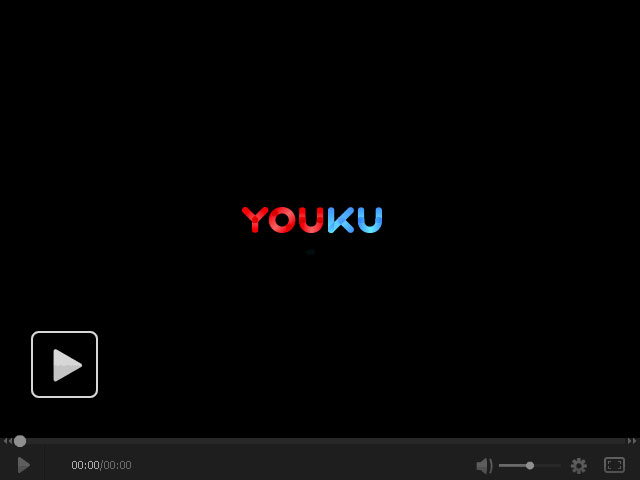
吴宏(1615 —1680),一作弘,字远度,号竹史、西江外史。江西金溪人,移居江宁(今南京)。自幼好绘事,诗书均精,自辟蹊径。顺治十年(1653)曾渡黄河,游雪苑,归而笔墨一变,纵横放逸。画作大多取材于自然景物及仰慕的桃花源仙境,构图疏密相间,气势雄阔。偶作竹石,亦有水墨淋漓之致。偶作竹石,亦有水墨淋漓之致;与龚贤、高岑、樊圻、邹喆、叶欣、胡慥、谢荪合称为“金陵八家”,周亮工赠诗云:“幕外青霞自卷舒,依君只似住村虚,枯桐已碎犹为客,妙画通神独亦予”。传世作品有康熙五年(1666)作《山水》册页、《江山行旅图》卷,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十一年(1672)作《柘溪草堂图》轴、《竹石图》轴,藏南京博物院;《山村樵牧图》轴,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国(清)朝画征录、读画录、桐阴论画、安雅堂集、江宁志、清画家诗史》 《溪山楼阁图》 清代 吴宏 绢本设色 179×95cm 题识:地蟠山矗矗,天沓树蒙蒙。眺远秋客澹,寻幽野性浓。乍疑牛渚客,又似鹿门翁。石城秋色远,风景宛然同。元人墨法,竹史吴宏。 墨韵中的溪山清梦 —— 吴宏《溪山楼阁图》赏析清代画家吴宏的《溪山楼阁图》(绢本设色,179×95cm)是一幅兼具北派雄浑与南派灵秀的山水佳作。题识 “地蟠山矗矗,天沓树蒙蒙…… 石城秋色远,风景宛然同。元人墨法,竹史吴宏” 点明了创作主旨:以元代笔墨技法,绘南京(石城)秋景,寄托文人 “寻幽” 之趣。画面中,吴宏以劲健的笔触、明快的设色,构建出一个可居可游的诗意空间,展现了 “金陵八家” 对传统山水的创新诠释。 一、构图:层峦叠嶂中的视觉交响画面采用“深远式构图”,通过 “近 — 中 — 远” 三重空间的递进,营造出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意境: 近景:石隐溪声
画幅左下角,巨石临江而立,以 “斧劈皴” 结合浓墨渲染,石面肌理如刀砍斧凿,间以淡墨皴擦出苔藓,展现岁月侵蚀的痕迹。巨石缝隙间,溪水潺潺流出,以细笔勾勒波纹,水口处用焦墨点染碎石,强化水流的动感。岸边几棵杂树参差生长,树干以双钩法勾勒,树叶用 “介字点”“垂头点” 密集点染,墨色浓淡相间,既有深秋的萧瑟,又含初冬的静谧。 中景:林屋隐现
画面中部,溪水蜿蜒向深处延伸,两岸林木茂密,以 “披麻皴” 描绘坡地,再用花青与赭石交替渲染,表现出草木的丰茂与季节的转换。林间隐现几座楼阁,飞檐翘角,以界尺勾勒轮廓,斗拱、栏杆细节清晰,屋顶用赭石色轻染,门窗以朱红点厾,虽工整却无匠气。楼阁前平台上,二文人对坐论道,一人抚琴,一人静听,童子侍立烹茶,人物虽小却神态生动,衣纹用 “铁线描” 勾勒,线条流畅自然。 远景:峰峦如屏
画面上方,主峰巍峨耸立,山体以 “解索皴” 结合淡墨积染,顶部用石青轻罩,山脚处云雾缭绕(以留白表现),形成 “山欲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 的视觉效果。主峰两侧,次峰如羽翼舒展,以淡墨勾皴,与前景巨石形成呼应,共同构成 “左青龙,右白虎” 的守护格局,使画面中心的楼阁成为被山水环抱的 “世外桃源”。
二、笔墨:北骨南风的技法融合吴宏的笔墨融合南北宗之长,在这幅作品中体现为 “北派的骨力” 与 “南派的韵致” 的完美结合: 线条的刚柔并济:勾勒山石轮廓时,线条方折劲挺,如北派 “斧劈皴” 般刚健(近宋代李唐笔意);描绘溪水、云雾时,线条圆转流畅,似南派文人画的 “吴带当风”。这种刚柔对比,使画面既有金石之坚,又具流水之柔。 墨色的层次递进:采用 “积墨法” 层层渲染,近景巨石用浓墨皴擦,中景林木用淡墨点染,远景山峰以极淡墨色晕染,再以花青烘染天空,形成 “由实入虚” 的墨色梯度。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增强了空间纵深感,还通过墨色的冷暖变化(近景偏暖,远景偏冷),暗示了光照的方向与季节的特征。 点染的节奏美感:树叶、苔点以 “攒三聚五” 之法分布,看似随意却暗藏数理 —— 密集处如重奏,疏朗处如休止符,形成视觉上的韵律感。这种 “密不透风,疏可走马” 的布局,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对 “秩序与变化” 的辩证思考。
三、设色:雅致清逸的秋山诗意画面以“浅绛山水”为基调,辅以花青、石绿,营造出江南秋日的温润与澄明: 山石赋色:先用赭石色渲染山石阳面,再以花青加墨皴擦阴面,冷暖色调的碰撞凸显了山石的体积感。山脚处的坡地则用赭石与石绿混合点染,暗示衰草与苔藓的交织,体现出 “秋意未深,冬韵初萌” 的季节特征。 林木着色:阔叶树以赭石点染叶片,表现秋日的萧瑟;松树则用花青与石绿交替点染松针,间以焦墨勾出松鳞,使常绿与落叶树种形成对比,丰富了画面的层次。 楼阁点缀:楼阁屋顶用赭石色平涂,门窗以朱红点厾,在青绿色调中形成视觉焦点,既符合 “居舍暖色调” 的生活常理,又暗合文人画 “以简胜繁” 的审美取向。
四、题识与意境:文人精神的图像化表达题识 “地蟠山矗矗,天沓树蒙蒙” 既是对画面的概括,也是文人心境的写照: “寻幽” 的精神指向
画中文人远离市井,于溪山楼阁间抚琴论道,暗合陶渊明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隐逸情怀。吴宏通过 “牛渚客”(指东晋袁宏,借指文人雅集)与 “鹿门翁”(指东汉庞德公,借指隐士)的典故,将画面人物升华为文人理想的化身,体现清初遗民画家对精神净土的追寻。 “元人墨法” 的传承与创新
吴宏虽标榜 “元人墨法”,却突破元画的萧疏淡远,融入宋画的严谨构图与世俗趣味。例如,楼阁的工细界画、人物的生动刻画,更近宋代院画;而山石的简笔皴擦、林木的写意点染,则取法元人,体现了 “师古而不泥古” 的创作理念。 地域文化的隐性流露
题识 “石城秋色远” 点明此为南京秋景,画面中临江的巨石、蜿蜒的溪流,可能取材于南京近郊的江河地貌(如秦淮河上游),而楼阁的形制亦接近江南文人别业。吴宏将地域特征提炼为艺术符号,既保留了 “师法造化” 的写实性,又赋予其 “中得心源” 的理想色彩。
五、与吴宏其他作品的风格对照对比吴宏的《清江行旅图》卷,《溪山楼阁图》展现出其艺术的另一面: 结语:绢素上的精神原乡吴宏的《溪山楼阁图》如同一首凝固的山水诗,在溪山的环抱中、在楼阁的雅集中,诉说着中国文人对 “诗意栖居” 的永恒向往。画中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激烈的情感,唯有一片宁静的山水、几间雅致的楼阁、几位超然的文人,却让观者感受到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 那是对自然的敬畏,对本真的回归,更是对心灵家园的终极追寻。这种以画为 “境”、以笔为 “舟” 的创作理念,正是中国画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的最高境界。 
《春山观瀑图》 清代 吴宏 题识:梅花庵主墨精神,老我重修翰墨因。只恐淋漓无艳治,淡妆端不媚时人。远度,录石田句。 墨舞春山的文人精神 —— 吴宏《春山观瀑图》赏析清代画家吴宏的《春山观瀑图》以题识 “梅花庵主墨精神,老我重修翰墨因…… 淡妆端不媚时人” 为引,点明其师法元代吴镇(号梅花庵主)的创作脉络,同时借吴镇 “墨戏” 精神抒发不媚世俗的文人情怀。画面中,吴宏以酣畅的笔墨、氤氲的墨韵,描绘春山飞瀑的雄奇与文人观瀑的雅趣,展现了 “金陵八家” 对传统文人画的继承与革新。 一、构图:虚实相生的山水乐章画面采用“对角线构图”,以左侧春山与右侧飞瀑形成张力,中间云雾缭绕,构建起 “动” 与 “静”、“实” 与 “虚” 的交响: 左侧:春山的静谧之美
画面左上方,山峦层叠,以 “披麻皴” 结合淡墨积染,表现出春山的温润与葱郁。山顶新绿初萌,以石绿轻罩,山脚处桃花数枝斜出,花瓣用朱砂点染,似有暗香浮动,点明 “春山” 主题。山腰间隐现茅屋数间,以淡墨勾勒轮廓,屋顶用赭石色渲染,门窗虚掩,暗示主人 “离尘不离世” 的生活状态。 右侧:飞瀑的动态奇观
画面右下方,瀑布从高处奔腾而下,以 “战笔” 勾勒水花,笔触跌宕起伏,似能听见轰鸣之声。瀑布下方,深潭水花四溅,以浓墨点染礁石,与飞溅的白浪形成 “墨白对比”。潭边巨石上,二文人对坐观瀑,一人举杯,一人展卷,童子侍立烹茶,人物虽小却神态悠然,衣纹用 “折芦描” 勾勒,线条劲挺,与飞瀑的动态形成呼应。 中部:云雾的朦胧诗韵
画面中部大面积留白,以淡墨湿笔晕染云雾,既分隔春山与飞瀑,又形成 “虚实相生” 的意境。云雾中隐约可见山径蜿蜒,似有观者足迹,引导视线从观瀑文人延伸至春山深处,体现 “曲径通幽” 的园林意趣。
二、笔墨:酣畅淋漓的文人意趣吴宏在此作中尽显 “墨戏” 精神,笔法洒脱如行草,墨韵氤氲似泼彩,深得吴镇 “墨沈淋漓” 之妙: 山石的写意性:山体轮廓以中锋圆转勾勒,摒弃刚硬线条,转而用 “湿笔淡墨” 层层晕染,再以浓墨点苔,如 “米点” 散落,表现春山的润泽。这种 “以柔化刚” 的处理,较吴镇更显明快,体现金陵画派的地域特色。 飞瀑的动态表现:瀑布以 “拖泥带水皴” 描绘,先以淡墨湿笔横扫出水势,再以浓墨勾皴岩石,形成 “水石相激” 的视觉冲击。水花用 “空白法” 表现,通过周围墨色的烘托,凸显水流的晶莹剔透。 点染的随机性:树叶以 “介字点”“混点” 随意点染,不求工整,但求神似;桃花用朱砂 “没骨法” 点厾,大小错落,似春风中摇曳,体现 “信手拈来” 的文人墨趣。
三、设色:淡妆素裹的春山本色画面以“水墨为主,轻色为辅”的设色策略,践行题识中 “淡妆端不媚时人” 的美学主张: 四、题识与意境:不媚时俗的精神宣言题识 “梅花庵主墨精神,老我重修翰墨因” 揭示了三层深意: 对吴镇的精神继承
吴镇作为元代 “隐逸画家” 的代表,其作品常以山水隐喻精神自由。吴宏题 “梅花庵主墨精神”,不仅指技法上的师承(如湿笔皴染、墨色氤氲),更指对 “不慕权贵、独守清贫” 文人品格的认同。 对世俗审美的反叛
“只恐淋漓无艳治,淡妆端不媚时人” 直抒胸臆,表明画家刻意避开时俗喜爱的 “浓艳”“工细” 风格,坚持以 “淡妆”(水墨为主)、“淋漓”(写意笔法)表达真我,这种 “不合时宜” 的选择,暗合清初遗民画家的精神困境。 对自我身份的确认
“老我重修翰墨因” 中的 “重修” 二字,暗含画家对艺术生涯的反思与坚守。在清初画坛 “四王” 摹古之风盛行时,吴宏选择师法吴镇并融入个人风格,既是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 “金陵画派” 独立精神的确认。
五、与吴宏其他作品的风格呼应对比吴宏的《云深疏树图》《清江行旅图》,《春山观瀑图》展现出其艺术的兼容性: 结语:水墨里的精神突围吴宏的《春山观瀑图》不仅是一幅山水佳作,更是一篇文人精神的宣言书。画中飞瀑的轰鸣,是对世俗喧嚣的回应;春山的静谧,是对精神家园的坚守;题识的呐喊,是对时俗审美的反叛。吴宏以吴镇的 “墨精神” 为武器,在清初画坛的摹古浪潮中突围,用酣畅的笔墨证明:真正的文人画,从来不是技法的堆砌,而是生命态度的真诚流露。当我们凝视画中观瀑的文人,看到的不仅是山水间的片刻逍遥,更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对自由精神的永恒追寻 —— 那是一种在世俗洪流中,依然能守住 “淡妆” 本色的勇气,是中国艺术最珍贵的精神基因。 《云深疏树图》 清代 吴宏 纸本水墨 128×32cm 题识:白云最深处,穷岩带疏树。山深无车马,独有迷人顾。仿李咸熙,竹史吴宏。 由奚萼铭旧藏,(奚鄂铭:又字萼铭,名光旭,斋名鄂庐,江苏江阴人,精鉴赏。)钤 印「吴宏」(朱),「远度」(朱)鉴藏印「澄江奚光旭鄂铭藏」(朱),「干学之印鄂铭审定」(朱) 云深处的疏淡诗心 —— 吴宏《云深疏树图》赏析清代画家吴宏的《云深疏树图》(纸本设色,128×32cm)是一幅兼具宋元意趣与个人风格的山水小品。题识 “白云最深处,穷岩带疏树。山深无车马,独有迷人顾。仿李咸熙,竹史吴宏” 表明其师法北宋李成(字咸熙)的创作渊源。画面中,吴宏以简练的笔墨、空灵的构图,描绘了云深山静、疏树萧疏的意境,既得李成 “气象萧疏,烟林清旷” 之神,又融入了金陵画派的清刚之气,展现出文人画家对隐逸精神的追求。 一、构图:留白中的天地大美画面采用“边角式构图”,以左侧山体与右侧云气形成对角呼应,中间大面积留白,营造出 “无画处皆成妙境” 的哲学意味: 左侧:岩壑的刚健之美
画面左上方,陡峭的山石以 “斧劈皴” 侧锋疾扫,线条刚劲如铁,转折处顿挫有力,尽显李成 “卷云皴” 的遗韵。岩石间几棵枯树斜出,枝干作 “蟹爪枝” 状向下低垂,枝头无叶,唯有几片残叶以焦墨点染,尽显萧瑟之意,暗合李成 “寒林” 画题的孤寂感。 右侧:云气的氤氲之韵
画面右下方,云气以淡墨湿笔晕染,先以清水打底,再趁湿点染花青,形成自然晕染的效果,与左侧岩石的刚硬形成 “刚柔对比”。云气中隐约可见几棵疏树,以 “介字点” 轻染树叶,墨色淡若烟岚,似有若无,体现 “云深不知处” 的意境。 中部:留白的哲学空间
画面中部大面积留白,既象征 “白云最深处” 的缥缈,又暗合道家 “空故纳万境” 的思想。这种 “以白代云、以虚代实” 的处理方式,突破了实景描绘的局限,赋予画面无限的想象空间。
二、笔墨:简劲疏淡的技法特质吴宏在此作中展现了 “以少胜多” 的笔墨功力,延续了李成 “惜墨如金” 的传统,又融入了自身的创新: 线条的金石气:勾勒山石轮廓时,笔锋逆入平出,线条斑驳如刻碑,转折处刻意保留 “飞白” 效果,似借鉴青铜器纹样,强化岩石的历史厚重感,较李成更显刚健。 墨色的层次感:采用 “淡墨起底,浓墨提神” 的技法,岩石先用淡墨勾勒轮廓,再以浓墨皴擦暗部,形成 “阴阳向背” 的立体感;疏树则以淡墨勾干,浓墨点叶,通过 “墨分五色” 表现出树木的远近层次。 点染的象征性:树叶以 “介字点”“垂头点” 寥寥数笔完成,不求形似,但求神似;苔点以 “胡椒点” 零星分布于岩石缝隙,如翡翠嵌于铁石,起到 “提神” 作用,体现 “疏可走马,密不透风” 的构图原则。
三、设色:清冷淡雅的情感基调画面以“水墨为主,淡彩为辅”的设色策略,营造出 “烟林清旷” 的秋日氛围: 四、题识与意境:隐逸精神的双重叩问题识 “山深无车马,独有迷人顾” 直接点明了画作的精神内核 —— 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与对世俗喧嚣的疏离: “云深” 的象征意义
云气作为画面的核心意象,既是自然景观的描绘,也是精神境界的隐喻。“白云最深处” 象征着超越世俗的理想国,那里没有 “车马”(代指功名富贵)的纷扰,只有 “迷人”(指知心友人或自然山水)的陪伴,体现了文人对精神纯净度的追求。 “疏树” 的人格投射
画面中的枯树、疏树,虽枝干萧疏却风骨凛凛,似是画家自我形象的写照。吴宏作为清初遗民画家,通过描绘 “穷岩带疏树” 的景致,既继承了李成 “寒林” 画题的孤寂意境,又暗含了遗民 “抱节自守” 的人格理想。 “仿李咸熙” 的文化对话
李成作为北宋山水的宗师,其 “荒寒”“清旷” 的画风常被后世文人借用来表达隐逸情怀。吴宏题 “仿李咸熙”,并非单纯技法模仿,而是通过与古人的精神对话,确认自身在文化谱系中的位置,同时借古喻今,抒发清初文人的共同心境。
五、与吴宏其他作品的风格对照对比吴宏的《清江行旅图》《溪山楼阁图》,《云深疏树图》展现出其艺术的另一面: 结语:一纸疏淡见精神吴宏的《云深疏树图》以不足一平尺的画幅,构建了一个深邃的精神宇宙。在这里,白云是自由的化身,疏树是人格的镜像,留白是心灵的故乡。画家通过对李成画风的创造性转化,将北宋山水的雄浑气象与清初文人的遗民情怀熔于一炉,最终在简劲的笔墨、空灵的构图中,完成了对隐逸精神的当代诠释。这幅作品不仅是对传统的致敬,更是一曲写给未来的心灵独白 —— 它让我们看到,在历史的云烟中,总有一片 “云深之处”,守护着中国人对自由与本真的永恒向往。 
《清江行旅图》卷 清 吴宏 纸本设色 纵23.7厘米,横242.5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他曾在顺治十年游黄河,归来后笔墨一变,纵横放逸,走出自己的风格。此画真实地描绘了江南仲秋时的水乡风情,远处山峦起伏,新篁杂生,烟雾蒙蒙。描绘了深山巨壑、层峦耸竣之中,亭台楼阁掩映,栈桥舟船蜿蜒曲折,行人若隐若现,洋溢出一派宁静祥和的气象,如入世外桃源,令人向往。整幅作品设色清淡,生动细致地描绘出了秀美的江南山水景色,落笔大胆而收拾严整,笔墨苍秀,厚重劲健,山石用皴擦苔点之法,水墨晕染,湿润而富有生机,树木画法工细,繁而不乱,取平远式布局,位置经营得当,是能代表吴宏山水画特色的作品。 江天万里的行旅长歌 —— 吴宏《清江行旅图》卷赏析清初 “金陵八家” 之一吴宏的《清江行旅图》卷(纸本设色,纵 23.7 厘米,横 242.5 厘米,上海博物馆藏),以长达两米四的横卷形制,展现了清江两岸的壮阔景致与行旅百态。作为与邹喆齐名的金陵画家,吴宏在此作中以洒脱的笔墨、鲜明的色彩、动态的构图,将山水的雄浑与世俗的烟火熔于一炉,既具宋代院画的写实精神,又含文人画的逸趣,堪称清初江景画的扛鼎之作。 一、构图:流动的视觉史诗画卷采用“散点透视”,如同展开一幅动态的江景纪录片,从近及远、由左至右徐徐铺陈,共分为三个段落,形成 “起 — 承 — 转 — 合” 的叙事节奏: (一)近岸人家:烟火气的起点画卷左端,江岸巨石嶙峋,以 “斧劈皴” 结合浓墨渲染,石面肌理粗犷,间以淡墨皴擦出苔痕,展现江水冲刷的痕迹。巨石间隙中,几棵古树参天,树干以 “双钩法” 勾勒,树皮皴纹如鳞,树叶用 “介字点”“垂头点” 密集点染,墨色浓淡相间,尽显盛夏繁茂。树下泊着两艘渔船,一艘舱门敞开,渔夫整理渔具;另一艘船头晒网,渔妇抱婴观望,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岸边小径上,挑夫弯腰前行,货担压得扁担微弯,身后童子跟随,动态生动。 (二)中流击楫:行旅的核心叙事画面中部,江水浩荡,以淡墨轻染水面,间以细笔勾勒波纹,表现 “风正一帆悬” 的意境。江面上,大小船只十余艘,形制各异:官船桅杆高耸,舱窗紧闭,船工奋力摇橹;商船满载货物,篷帆鼓起,船头商人凭栏远眺;小艇穿梭其间,渔夫撒网,樵夫担柴,尽显水上生活的繁忙。最醒目处,一艘楼船逆流而上,甲板上数人合力拉纤,纤绳绷直如弦,人物姿态各异,肌肉线条清晰可见,将 “行旅之艰” 刻画得入木三分。 (三)远山在望:诗意的收束画卷右端,江水向远方延伸,与天际相接。远处山峦连绵,以 “披麻皴” 结合淡墨渲染,山顶隐没于云雾(留白),山脚用花青轻罩,表现出 “山色有无中” 的朦胧感。江面上,一艘帆船渐行渐远,船身缩小如叶,帆影淡若轻烟,与近景的繁忙形成对比,暗合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的哲思。岸边茅亭中,一人独坐远眺,身边童子烹茶,为喧闹的江景注入一丝宁静,收束全卷。 二、笔墨:豪放与精微的交响吴宏的笔墨兼具 “北派的雄浑” 与 “南派的灵秀”,在长卷中展现出高超的控制力: 山石的刚健:近岸岩石以侧锋疾扫,“斧劈皴” 笔触凌厉,线条方折劲挺,转折处偶见 “飞白”,强化石质的坚硬;皴擦后再以浓墨点苔,如翡翠嵌于铁石,增添生机。 江水的灵动:水面采用 “平波法”,以细密的横线表现微波,近岸处因礁石阻挡,线条变曲变密,形成 “水激石鸣” 的效果;远处则用淡墨湿笔横扫,与天空融为一体,体现 “江天一色” 的辽阔。 人物的鲜活:全卷人物超三十人,身高仅寸许,却动态各异:拉纤者弓背蹬腿,肌肉隆起;摇橹者俯身发力,衣纹飘动;观望者手搭凉棚,神情专注。衣纹用 “钉头鼠尾描” 勾勒,线条粗细变化明显,尽显运动张力。
三、设色:明快热烈的世俗风情与邹喆的 “冷逸清寂” 不同,吴宏在此作中采用 **“浓淡相宜的暖色调”**,营造出热闹的世俗氛围: 四、意境:行旅图式的双重叙事《清江行旅图》超越了一般山水行旅画的写实性,蕴含双重叙事: 现实维度:清初社会的浮世绘
画中船只的多样(官船、商船、渔船)、人物的职业(渔夫、纤夫、商人、官吏)、活动的丰富(捕鱼、拉纤、贸易、休憩),构成了一幅清初长江中下游的社会全景图。尤其是拉纤场景的刻画,纤夫的艰辛与官船的闲适形成对比,暗含画家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具有现实主义色彩。 精神维度:文人视野的行旅哲思
画卷虽以世俗生活为主体,却在右端茅亭中设置 “独坐远眺” 的文人形象,其姿态与苏轼《赤壁赋》中 “飘飘乎如遗世独立” 的描写相呼应。这种 “俗中见雅” 的处理,体现了文人画家对世俗生活的观察与超越 —— 既置身其中,又保持精神的独立。 【观图显诗意】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屿出。回潭石下深,绿筱岸傍密。②鲛人潜不见,渔父歌自逸。③忆与君别时,泛舟如昨日。夕阳开晚照,中坐兴非一。④南望鹿门山,归来恨如失。
注释:① 诗题又作“登江中孤屿贻王山人迥”。王迥:孟诗中关于王迥的诗作很多,是诗人的好友,关系相当密切。 ② 傍:又作“边”。 ③ 鲛人:传说中的海底怪人。歌自逸:又作“自歌逸④ 开晚照:又作“门返照”、“开返照”。 ⑤ 鹿门山:在襄阳城南三十里。 五、与邹喆作品的风格对照作为 “金陵八家” 同期画家,吴宏与邹喆的创作呈现鲜明差异: 六、文化价值:一幅画中的长江记忆《清江行旅图》的长卷形制与写实风格,使其成为研究清初长江航运、民俗服饰、建筑形制的珍贵图像史料。画中官船的形制、商船的装载方式、纤夫的劳动场景,均与《康熙南巡图》等纪实性作品相互印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同时,吴宏通过 “散点透视” 将不同时空的场景并置,打破了西方焦点透视的限制,展现了中国传统绘画 “以大观小” 的宇宙观。 结语:流动的江山与永恒的行旅吴宏的《清江行旅图》卷如同一部无声的电影,在两米四的画幅中,既记录了清初长江的物理景观,也刻画了行旅者的生存状态,更暗含文人对 “动与静”“俗与雅” 的哲学思考。当观者的目光随着画卷移动,仿佛乘舟而行,在江天万里间见证人间百态,最终在茅亭文人的远眺中,完成从 “身历其境” 到 “心游万仞” 的精神升华。这幅作品不仅是金陵画派的杰出代表,更是中国艺术 “以画存史,以画言志” 传统的生动写照。 
《燕子矶莫愁湖二景图》(全卷) 清,吴宏,画幅30mX486cm。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长卷左绘南京莫愁湖,右绘燕子矶景色。莫愁湖湖面上一片浩渺,岸上树木苍翠,民居依山而建,毗邻而居;燕子矶山峦与江面相连,桅船停泊岸边,山青水静,一片详和。 【作品赏析】 这幅画描绘的燕子矶是南京的名胜。画面上江水与山石相连,渔船停泊在偏僻的港湾,天色傍晚,江水微波,烟雾迷朦的莫愁湖景象。莫愁湖内笼罩着轻纱般的云雾,岸边树木葱茏,使画面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长卷里的金陵双璧 —— 吴宏《燕子矶莫愁湖二景图》全卷赏析清初 “金陵八家” 吴宏的《燕子矶莫愁湖二景图》(纵 30cm,横 486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以宏阔的长卷形制,将南京两大地标 —— 莫愁湖的温婉与燕子矶的雄奇并置一画,宛如一部流动的金陵地理志。画家以劲健的笔墨、明快的色调,勾勒出江南山水的灵秀与世俗生活的烟火,既具写实性,又富诗意,堪称清初城市风光画的巅峰之作。 一、双城记:空间叙事的并置与对话全卷采用“左右分卷,中以江连”的结构,将莫愁湖(左)与燕子矶(右)通过江水脉络串联,形成 “一柔一刚、一静一动” 的视觉交响: (一)左卷:莫愁湖的温柔梦乡构图:平远式的江南秘境
以俯视视角展开湖面,湖水平如明镜,以淡墨轻染,间以细笔勾勒波纹,表现 “风定池莲自生香” 的静谧。湖岸线蜿蜒曲折,蒲草、芦苇以 “双钩法” 描绘,叶片细长灵动;岸边柳树成荫,枝条用 “蟹爪枝” 下垂,树叶以花青点染,尽显江南水乡的婀娜。 人文意象:烟火与诗意的交织
沿湖分布十余处民居,白墙黛瓦,以赭石染屋顶,朱红点门窗,错落于绿树丛中。屋前晒网的渔妇、湖畔浣衣的少女、柳下对弈的文人、船头横笛的牧童,构成一幅鲜活的市井风俗画。湖心小筑 “郁金堂”(莫愁女传说中的居所)以界尺勾勒,飞檐翘角,内设琴桌画卷,暗示文人雅趣与民间传说的叠加。
(二)右卷:燕子矶的雄浑史诗构图:高远式的山水壮歌
以仰视角度突出燕子矶 “长江第一矶” 的险峻 —— 矶石如巨鲸跃出江面,以 “斧劈皴” 侧锋疾扫,线条刚劲如铁,间以浓墨皴擦表现裂隙与苔痕,矶顶杂树丛生,枝干虬曲,树叶用焦墨点染,尽显苍劲。江水在矶下奔涌,以 “战笔” 勾勒浪花,与矶石的静态形成强烈动感对比。 动态叙事:行旅与自然的博弈
江面上,三艘帆船正绕过矶头:官船千帆竞发,船工奋力摇橹,风帆如墙;货船满载粮草,纤夫于岸边俯身拉纤,纤绳绷直如弦,肌肉线条清晰可见;渔船穿梭其间,渔夫撒网的弧线与江水波纹形成韵律呼应。矶顶小亭中,文人凭栏远眺,身边童子捧砚,似欲题诗,将 “自然人化” 与 “人化自然” 巧妙融合。
二、笔墨密码:北骨南风的技法融合吴宏的笔墨突破 “金陵八家” 常规,展现出 “以书入画” 的独特面貌: 线条的金石气:勾勒矶石轮廓时,笔锋逆入平出,线条斑驳如刻碑,转折处刻意保留 “锯齿状” 毛边,似借鉴青铜器纹样,强化岩石的历史厚重感;描绘柳枝则用中锋圆转,如 “吴带当风”,刚柔对比强烈。 墨色的戏剧化:莫愁湖部分以 “淡墨为主,浓墨破之”,先以清水打底,再趁湿点染花青,形成 “水晕墨章” 的效果;燕子矶部分则 “浓墨立骨,淡墨生韵”,矶石先用浓墨勾皴,再以淡墨染出阴阳面,层次分明如雕塑。 点染的节奏性:全卷苔点以 “梅花点”“胡椒点” 交替使用,莫愁湖岸用疏朗的 “梅花点” 表现草地,燕子矶头用密集的 “胡椒点” 象征灌木,通过点的疏密控制视觉节奏,暗合音乐的强弱节拍。
三、色彩哲学:浅绛山水的世俗化转译吴宏在此作中革新了传统 “浅绛” 技法,赋予其鲜明的地域特色: 主色调的地域适配:以赭石染堤岸、屋顶,模拟南京秋日 “暖冬” 的气候特征;花青染湖水、远山,与长江的深邃呼应;石绿点染苔痕、荷叶,增添生机,形成 “赭石 — 花青 — 石绿” 的色彩三角,既古朴又明快。 点睛色的民俗意味:民居门窗的朱红色、船工汗巾的粉紫色、文人衣袍的藤黄色,均取自民间服饰色彩,打破文人画的雅致垄断,使画面更贴近市井审美。这种 “雅俗共赏” 的设色策略,反映了清初商品经济繁荣下市民文化的崛起。
四、文化解码:一幅画中的南京记忆作为南京本土画家,吴宏在长卷中埋藏多重地域文化符号: 传说的可视化:莫愁湖 “郁金堂” 的描绘,将南朝梁代莫愁女的传说转化为图像,使自然景观成为文化记忆的载体; 军事的隐喻:燕子矶作为长江天险,画中帆船绕矶的艰难动态,暗含清初政权对 “长江防线” 的重视,具有政治地理学的隐性表达; 城市的呼吸感:从莫愁湖的慢生活到燕子矶的快节奏,从文人雅集到渔樵耕读,展现了南京作为 “江南都会” 的多元性 —— 既是帝王之都,也是百姓之城。
五、长卷的时间魔法:从 “游观” 到 “卧游”486cm 的长度使观者必须 “缓步移目”,如同亲身游览: 结语:流动的纸上诉金陵吴宏的《燕子矶莫愁湖二景图》不仅是一幅地理画卷,更是一曲关于南京的文化赞歌。他以长卷为舟,载着观者穿越清初的湖光江色,在莫愁湖的温柔中触摸历史的体温,在燕子矶的险峻中感受自然的力量。这幅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打破了文人画的精英主义传统,将城市风光、民间生活、地域传说熔于一炉,让山水画成为一部可读、可游、可感的 “金陵地方志”。当我们展开这幅近五米的长卷,看到的不仅是 300 多年前的山水形貌,更是一个城市的精神脉络 —— 它既流淌着莫愁女的眼泪,也奔涌着长江水的豪情,最终在吴宏的笔墨中,凝固成一曲永不褪色的金陵长歌。 
《江楼访友图》清 吴宏 立轴 绢本浅绛 161X79厘米 旅顺博物馆藏 此幅吴远度云是仿北宋初李成画法,实则借名而已,皴法已带唐伯虎乱柴皴法度,构图渲染全是金陵画派作风,然江天开阔,渔隐互答,远度此幅尤允佳品。是图笔墨精致,景色苍秀,真实地描绘了江南秋季的水乡风貌。构图采取平远手法,天地广阔而又层次分明。运用恰到好处的烘染技巧,略施淡彩,色调和谐且明快清爽,具有典型的“浅绛”风格。画心有作者自题“摹李营丘笔法于响雪庵中,外史吴宏”。钤“吴宏之印”、“远度”二印。《中国美术全集.清代绘画》、《中国绘画全集》著录。 水墨江南的访友诗 —— 吴宏《江楼访友图》赏析清代画家吴宏的《江楼访友图》(立轴,绢本浅绛,161×79 厘米,旅顺博物馆藏)是一幅融合古今、自出机杼的山水佳作。画心自题 “摹李营丘笔法于响雪庵中,外史吴宏”,虽标称仿北宋李成(营丘),实则以唐寅 “乱柴皴” 为骨,以金陵画派的开阔构图为魂,描绘了江南秋日江楼访友的诗意场景。此作笔墨精致,色调明快,既得李成 “烟林清旷” 之意,又具鲜明的地域特色与个人风格,堪称清初浅绛山水的典范。 一、构图:平远法中的江南叙事画面采用“平远式构图”,以 “近 — 中 — 远” 三层空间铺陈江南水乡的开阔与雅致: 近景:江岸的烟火温度
画幅左下角,江岸巨石嶙峋,以 “乱柴皴” 侧锋皴擦,线条短促而富有动感,模拟岩石的粗糙肌理,间以淡墨渲染苔痕,再以赭石色轻染阳面,展现秋日江岸的温润。巨石间隙中,杂树丛生,树干以双钩法勾勒,树叶用 “介字点”“垂头点” 混合点染,墨色浓淡相间,既有枯枝的萧瑟,又有常青树的生机。树下停泊一艘小船,船头童子持桨而立,船尾堆满渔具,暗示 “渔隐” 主题的同时,为画面注入生活气息。 中景:江楼的访友意象
画面中部,一座楼阁临江而建,飞檐翘角,以界尺勾勒轮廓,斗拱、栏杆细节清晰,屋顶用赭石色平涂,门窗以朱红点厾,在青绿色调中格外醒目。阁内二人对坐,一人抚琴,一人倾听,神态悠然;阁外平台上,另一人凭栏远眺,似在等待访客,童子抱琴侍立,人物虽小却动态生动,衣纹用 “琴弦描” 勾勒,线条流畅自然。楼阁后方,芦苇丛生,以 “双钩法” 描绘叶片,疏密有致,与楼阁的工整形成对比。 远景:江天的辽阔意境
画面上方,江水向远方延伸,与天际相接,以淡墨轻染水面,间以细笔勾勒波纹,表现 “风平浪静” 的意境。远处山峦连绵,以 “披麻皴” 结合淡墨渲染,山顶隐没于云雾(留白),山脚用花青轻罩,表现出 “山色有无中” 的朦胧感。江面上,一艘帆船渐行渐远,船身缩小如叶,帆影淡若轻烟,与近景的江楼形成呼应,暗合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的哲思。
二、笔墨:古今交融的技法创新吴宏在此作中展现了 “借古开今” 的技法智慧,融合李成的 “清旷”、唐寅的 “劲健” 与金陵画派的 “明快”: 皴法的突破性:虽题 “摹李营丘”,却弃用李成标志性的 “卷云皴”,转而以唐寅 “乱柴皴” 入画 —— 以短促的侧锋线条模拟柴枝交叉,既表现岩石的嶙峋,又具书写性,较李成更显刚健,与金陵画派 “清刚雅正” 的风格契合。 墨色的层次感:采用 “淡墨打底,浓墨提神” 的技法,近景岩石用浓墨皴擦,中景楼阁用淡墨渲染,远景山峦以极淡墨色晕染,再以花青烘染天空,形成 “由实入虚” 的墨色梯度。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增强了空间纵深感,还通过墨色的冷暖变化(近景偏暖,远景偏冷),暗示了秋日的光照特征。 点染的节奏感:树叶、苔点以 “三一法” 分布(三点一组,一浓两淡),芦苇叶片以 “平行排列法” 表现,既有秩序又有变化,如音乐中的节拍,赋予画面动态韵律。
三、设色:浅绛山水的地域演绎作为 “金陵八家” 中善用浅绛的代表,吴宏在此作中赋予传统浅绛技法以江南特质: 主色调的秋日适配:以赭石染堤岸、屋顶、树干,模拟江南秋日 “暖冬” 的气候特征;花青染江水、远山,与赭石形成 “冷暖对比”;石绿点染苔痕、树叶,增添生机,形成 “赭石 — 花青 — 石绿” 的色彩三角,既古朴又明快。 浅绛的文人雅趣:全画以淡彩为主,仅在楼阁门窗、船工头巾等细节略施朱红,这种 “克制的鲜艳” 既符合文人画 “雅正” 的审美标准,又暗合 “秋意渐深,暖色点睛” 的季节特征,避免了浅绛易有的单调感。
四、题识与意境:借古喻今的精神对话题识 “摹李营丘笔法” 背后,隐藏着吴宏的三重创作意图: 技法层面的 “似与不似”
虽言 “摹古”,却在皴法、构图、设色中融入鲜明的个人风格,体现了清初画家 “师古而不泥古” 的普遍心态。正如董其昌 “借古以开今” 的主张,吴宏通过对李成的 “创造性转化”,确立了金陵画派的独特面貌。 意境层面的 “渔隐” 情结
画中 “江楼”“渔舟”“芦苇” 等意象,共同构成了 “渔隐” 主题的视觉符号。这种对隐逸生活的描绘,既继承了李成 “士大夫幽人之所适” 的创作理念,又暗含清初遗民画家对仕途的疏离,具有时代精神烙印。 地域层面的 “江南” 叙事
画面中平缓的山峦、开阔的江面、临江的楼阁,均取材于南京及周边的水乡地貌,与李成笔下的北方山水截然不同。吴宏以 “江南化” 的改造,使传统山水图式成为地域文化的载体,展现了金陵画派 “师法造化” 的现实主义精神。 【观图显诗意】杪秋寻远山,山远行不近。与子别山阿,含酸赴修轸。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顾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隐。隐汀绝望舟,骛棹逐惊流。欲抑一生欢,并奔千里游。日落当栖薄,系缆临江楼。岂惟夕情敛,忆尔共淹留。淹留昔时欢,复增今日叹。兹情已分虑,况乃协悲端。秋泉鸣北涧,哀猿响南峦。戚戚新别心,凄凄久念攒!攒念攻别心,旦发清溪阴。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那可寻?傥遇浮丘公,长绝子徽音。
五、与吴宏其他作品的风格互证对比吴宏的《清江行旅图》《春山观瀑图》,《江楼访友图》展现出其艺术的成熟与综合: 六、文化价值:一幅画中的画史坐标《江楼访友图》的价值不仅在于艺术成就,更在于其画史意义: 结语:浅绛里的江南心吴宏的《江楼访友图》以浅绛为韵,以江楼为眼,在水墨与色彩的交响中,奏出了一曲江南秋日的访友乐章。画中没有宏大的山水奇观,只有平凡的江楼、普通的渔舟、悠然的文人,却让观者感受到一种超越时空的亲切 —— 那是中国人骨子里对 “有朋自远方来” 的期待,是对 “江湖相忘” 的隐逸向往,更是对 “淡妆浓抹总相宜” 的江南情结的永恒致敬。这幅作品不仅是吴宏个人艺术的缩影,更是中国传统山水 “以画会友,以心印心” 精神的生动写照。 
《松溪草堂图》清 吴宏 绢本设色 纵160.5厘米,横79.9厘米 南京博物馆藏 该画绘村前一座小桥,湖水绕村,树木绕斋,树林里楼台面水,宾主登楼安坐对谈,超然世外。笔墨挺健,景致平远,具有浓厚的写实风格。此画远处为较为平缓的山峦,山头仅露出水面。隐隐约约,烟雾蒙蒙,茫茫一片,山坡间新篁密密麻麻,白马湖东岸,在丛树掩映下的临水小村,一条清溪绕庄而行,竹树绕斋,楼台面小,并不华丽的庄园建筑,在苍松翠竹红枫的簇拥下显得古朴典雅;宾主登楼端坐其间,正在语笑风生,突然间一人回首远眺,似在观赏周围一片金秋美色,村边座落着一小板桥。一扁舟自远方来,泊于桥头,舟中一人捧物躬身而出,作献物状,岸上溪边另一人缓步走来作迎接状,神态自若。 此图款署“壬子秋九月,拟李咸熙笔意,呈石翁先生教之,金溪吴宏”钤印“吴宏私印”“远度”。画的裱边及玉池中有查士标,梁清标两人题诗,朱彝尊、程邃等七人题词。 水墨江南的草堂梦 —— 吴宏《松溪草堂图》赏析清代画家吴宏的《松溪草堂图》(绢本设色,纵 160.5 厘米,横 79.9 厘米,南京博物院藏)以江南仲秋为背景,描绘了松溪环绕、草堂隐现的水乡景致。画作以平远式构图、清淡设色、工写结合的技法,展现了秀美的江南山水与文人理想中的栖居意境,既具北宋山水的严谨构图,又含明代吴门画派的文人雅趣,是 “金陵八家” 吴宏的代表性作品。 一、构图:平远式的江南诗境画面采用“平远法”布局,通过 “近 — 中 — 远” 三重空间的平缓延伸,营造出 “江天一色无纤尘” 的开阔意境: 近景:松溪的烟火温度
画幅左下角,溪流蜿蜒而过,以细笔勾勒波纹,水口处用焦墨点染碎石,模拟水流的湍急。溪岸巨石嶙峋,以 “斧劈皴” 结合淡墨皴擦,石面肌理粗糙,间以赭石色轻染阳面,展现秋日阳光的温和。岩石间,松树挺拔,树干以双钩法勾勒,鳞片状树皮刻画细致,松针用 “车轮点” 密集点染,墨色浓淡相间,尽显苍劲;新篁(竹子)丛生,以 “个”“介” 字形笔法写竹叶,疏密有致,与松树形成 “岁寒三友” 的隐喻。 中景:草堂的隐逸意象
画面中部,草堂坐落于溪畔竹林间,白墙黛瓦,以淡墨勾勒轮廓,屋顶用赭石色平涂,门窗虚掩,门前小径通向溪桥。草堂内,二文人对坐论道,一人展卷,一人拄腮倾听,童子侍立烹茶,人物虽小却神态悠然,衣纹用 “铁线描” 勾勒,线条流畅。草堂右侧,一架木桥横跨溪流,桥上一人荷锄而归,身后童子抱琴,动态生动,为静谧的草堂注入生活气息。 远景:山峦的朦胧诗韵
画面上方,山峦起伏连绵,以 “披麻皴” 结合淡墨积染,表现出江南丘陵的平缓与温润。山顶新篁杂生,以石绿轻罩,山脚处烟雾蒙蒙(以淡墨湿笔晕染),形成 “山色有无中” 的朦胧感。远景与中景之间,留白处理的江面开阔平静,几艘渔舟停泊,渔夫整理渔具,既延伸了空间纵深,又暗合 “渔隐” 主题。
二、笔墨:工写兼济的技法特质吴宏在此作中展现了 “落笔大胆,收拾严整” 的笔墨功力,融合北派的刚健与南派的灵秀: 山石的写意性:以侧锋皴擦为主,“斧劈皴” 与 “披麻皴” 交替使用 —— 近景岩石用刚劲的 “斧劈皴” 表现坚硬质感,远景山峦用柔和的 “披麻皴” 体现温润特质,通过笔法的转换实现空间过渡。 树木的工细性:松树、竹子刻画细致,松针分组排列,竹叶 “攒三聚五”,虽繁密却秩序井然;杂树以 “蟹爪枝”“鹿角枝” 穿插,枝干转折处顿挫分明,尽显生机。 水墨的氤氲感:全画以 “湿笔淡墨” 为主,山石、云雾均通过水墨晕染形成自然过渡,尤其是远景山峦与江面的交界处,水墨交融似有若无,体现 “墨分五色” 的层次感。
三、设色:清淡雅致的仲秋基调画面以“浅绛山水”为基础,辅以花青、石绿,营造出江南仲秋的清朗与温润: 四、意境:文人精神的江南转译《松溪草堂图》不仅是江南水乡的写实描绘,更是文人理想的视觉化表达: “草堂” 的符号意义
草堂作为核心意象,是陶渊明 “桃花源”、杜甫 “草堂” 的延续,象征文人对简朴生活与精神自由的追求。画中草堂隐于松竹之间,远离市井喧嚣,却又有荷锄归耕的俗人,体现了 “大隐隐于市” 的处世哲学。 “松溪” 的人格隐喻
松树的苍劲、溪水的灵动,暗合文人 “君子比德于自然” 的审美取向 —— 松树象征坚贞品格,溪水寓意智慧流动,二者共同构成文人理想的人格范式。 地域文化的显性表达
画中平缓的山峦、密集的竹林、临水的草堂、停泊的渔舟,均为江南(尤其是南京周边)典型地貌,吴宏通过细腻的笔触,将地域风光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山水图式,体现了金陵画派 “师法造化” 的创作理念。 【观图显诗意】龙舒有良匠,铸此佳样成。立作菌蠢势,煎为潺湲声。草堂暮云阴,松窗残雪明。此时勺复茗,野语知逾清。
五、与吴宏其他作品的风格呼应对比吴宏的《江楼访友图》《春山观瀑图》,《松溪草堂图》展现出其艺术的典型特征: 六、结语:绢素上的江南栖居吴宏的《松溪草堂图》以细腻的笔触、清淡的色彩,在绢素间铺陈出一个可居可游的江南梦境。画中没有奇峰怪石,没有惊涛骇浪,只有寻常的溪桥、朴素的草堂、悠然的文人,却让人感受到一种直击心灵的宁静 —— 那是对江南水乡的眷恋,是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更是对文人精神家园的永恒追寻。这幅作品不仅是吴宏艺术的缩影,更是中国传统山水 “以画栖心” 精神的生动诠释,让千年后的观者依然能在水墨烟霞中,触摸到江南仲秋的温润与澄明。 
《秋山平远图》清 吴宏 纸本设色 淡墨秋山远,平芜入画来 —— 吴宏《秋山平远图》赏析清代画家吴宏的《秋山平远图》(纸本设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以疏朗的构图、淡逸的笔墨,绘江南秋日的平远之景。作为 “金陵八家” 中善写江天辽阔的代表,吴宏在此作中融合北宋李成的 “平远法” 与明代吴门画派的文人意趣,以 “淡墨轻岚” 的设色、“虚实相生” 的布局,展现了秋山无际、江天开阔的诗意境界,堪称其晚年 “清刚雅正” 风格的典范之作。 一、构图:平远式的秋意铺陈画面采用典型的 **“平远构图”**,以 “近水 — 中坡 — 远山” 的横向延展,营造出 “目极千里” 的视觉体验,打破了传统山水画的垂直空间局限: 近景:水岸的秋意初显
画幅左下角,坡岸逶迤,以 “披麻皴” 结合淡墨皴擦,表现秋日泥土的湿润质感,间以赭石色轻染,模拟衰草的暖色调。岸边几棵杂树疏落生长,树干以双钩法勾勒,枝条作 “蟹爪状” 低垂,树叶用 “介字点”“垂头点” 交替点染,墨色浓淡相间,既有黄叶飘零的萧瑟,又有常青树的生机。树下停泊一叶扁舟,船身以简笔勾勒,篷顶用赭石色渲染,船头无人,唯留钓竿斜倚,暗示 “野渡无人舟自横” 的寂寥。 中景:平坡的空间过渡
画面中部,平缓的坡地向远方延伸,以 “折带皴” 描绘土坡的起伏,再用花青加赭石交替渲染,表现秋草的斑驳。坡地上,竹篱环绕的茅舍数间,以淡墨勾勒轮廓,屋顶用赭石色平涂,门窗虚掩,门前小径蜿蜒,通向坡后。茅舍旁,二文人对坐于竹下,一人抚琴,一人静听,童子侍立煮茶,人物虽小却神态悠然,衣纹用 “琴弦描” 勾勒,线条流畅,与周围的疏朗景致形成呼应。 远景:秋山的缥缈之境
画面上方,远山连绵如黛,以 “没骨法” 用淡墨轻染,再以花青烘染山体暗部,山顶隐没于云雾(留白),山脚与江面交融,形成 “山色有无中” 的朦胧感。江面上,数艘帆船扬帆远航,船身以简笔勾勒,帆影用淡墨晕染,呈现出 “远帆如叶” 的透视效果,与近景的孤舟形成动静对比,暗合 “人生如逆旅” 的哲思。
二、笔墨:简劲疏淡的秋韵表达吴宏在此作中展现了 “以少胜多” 的笔墨智慧,笔法简练而意韵深远,深得 “淡墨秋山” 的精髓: 线条的清劲感:勾勒坡岸、树干时,线条爽利劲健,起笔收笔顿挫分明,似有金石之气,较李成的 “卷云皴” 更显刚健,体现金陵画派 “清刚” 的地域特色;描绘江水、云雾时,线条则婉转流畅,如流水无痕,刚柔并济。 墨色的层次感:采用 “淡墨为主,浓墨破之” 的技法,近景坡岸用淡墨打底,再以浓墨点苔提神;中景茅舍用淡墨渲染,仅在门窗处略施浓墨;远景山峦以极淡墨色晕染,通过墨色的 “由浓到淡”,自然形成空间纵深感。 点染的随机性:树叶、苔点以 “散点法” 分布,不求整齐,但求神似,如 “梅花点”“胡椒点” 随意散落,既表现秋树的疏朗,又增添画面的生动性,体现文人画 “逸笔草草” 的意趣。
三、设色:浅绛秋山的雅致格调画面以 **“浅绛山水”** 为基调,辅以花青、赭石,营造出江南秋日 “天高气清” 的爽朗氛围: 四、意境:秋山背后的文人哲思《秋山平远图》并非单纯的秋景写生,而是吴宏对文人精神世界的诗意建构,蕴含三重深意: “平远” 的空间哲学
平远构图打破了 “高远”“深远” 的压迫感,以水平延伸的视野象征文人 “胸怀天下” 的格局。画中无高大山峰,唯有平缓的坡地、辽阔的江面、缥缈的远山,体现了 “以平为贵” 的道家思想,暗含对 “中庸之道” 的追求。 “秋山” 的时间隐喻
秋日作为生命的成熟阶段,在画中象征文人的晚年心境 —— 褪去浮华,归于平淡。吴宏以疏朗的秋树、寂寥的孤舟、隐逸的文人,构建了一个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的精神图景,反映了清初遗民画家对人生价值的重新审视。 “访友” 的隐性叙事
画中虽无明确的 “访友” 场景,但茅舍中对坐的文人、江面上远航的帆船、岸边闲置的孤舟,均暗示着 “行旅” 与 “相聚” 的潜在叙事。这种 “有无相生” 的处理,让观者自行填补画面留白,体现中国传统美学 “言有尽而意无穷” 的境界。
五、与吴宏其他作品的风格互鉴对比吴宏的《江楼访友图》《松溪草堂图》,《秋山平远图》展现出其艺术的独特性: 从 “工细” 到 “疏简”:较《江楼访友图》的楼阁界画、《松溪草堂图》的树木工笔,此作笔墨更为简练,山石、树木以 “写意” 为主,仅在人物、舟船处略施工笔,体现了吴宏 “工写结合” 的全面技法。 从 “动态” 到 “静态”:《江楼访友图》有行旅的动态,《松溪草堂图》有生活的烟火,此作则以 “静穆” 为主,孤舟、茅舍、远山均处于静止状态,营造出 “万物静观皆自得” 的永恒意境,更接近元代倪瓒的 “逸气”。
结语:一纸平远见秋心吴宏的《秋山平远图》以简劲的笔墨、淡逸的设色,在尺幅间铺陈出江南秋日的辽阔与澄明。画中没有奇峰异石的视觉冲击,只有平淡天真的秋山秋水,却让人感受到一种超越时空的宁静 —— 那是对自然的敬畏,对本真的回归,更是对文人 “澄怀观道” 精神的永恒追寻。这幅作品不仅是吴宏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更是中国传统山水画 “以平远写心境” 的典范,让观者在水墨烟霞中,触摸到秋日江南的疏朗与深远,以及一位画家对生命境界的终极思考。 
《秋山萧寺图》吴 宏 设色绫本 立轴 1642年作 款识:元人画法。壬午重九前二日,金溪吴宏。 钤印:远度(朱)鉴藏印:胶西周氏古琴阁(白) 墨南考藏书画碑版(朱) 新建吴氏珍藏金石书画之印(朱) 说明:周墨南旧藏。 秋山深处的古寺钟声 —— 吴宏《秋山萧寺图》赏析明末清初画家吴宏的《秋山萧寺图》(设色绫本立轴,1642 年作)是一幅兼具宋元意趣与个人风格的山水佳作。款识 “元人画法。壬午重九前二日,金溪吴宏” 表明其师法元代山水的创作渊源,而鉴藏印 “胶西周氏古琴阁”“墨南考藏书画碑版” 等则记录了其流传脉络。画面中,吴宏以苍劲的笔墨、清逸的设色,描绘了秋山环抱、古寺隐现的静谧之境,既得元人 “萧疏淡远” 之神,又融入了明末画坛 “师古而化” 的创新精神,展现出画家早年便已成熟的艺术造诣。 一、构图:秋山环抱中的古寺幽境画面采用“深远式构图”,以层层递进的山景烘托古寺的幽深,形成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的空间叙事: 近景:溪桥的秋意引子
画幅左下角,溪流潺潺流过岩石,水口处用浓墨勾皴碎石,水花飞溅似有声响。岸边几棵古树参天,树干以双钩法勾勒,树皮皴纹如鳞,枝头叶片用 “介字点”“垂头点” 密集点染,墨色浓淡相间,展现出深秋的萧瑟与苍劲。树下一条石阶小径蜿蜒而上,通向中景的古寺,小径以淡墨轻扫,间以苔点点缀,暗示其幽僻少人。 中景:萧寺的核心意象
画面中部,古寺坐落在山坳之间,红墙黛瓦,以界尺勾勒轮廓,屋顶用赭石色平涂,门窗以朱红点厾,在青绿色调中格外醒目。寺前平台上,二僧人对坐论道,一人持杖,一人合掌,神态肃穆;寺后古松虬曲,松针以 “车轮点” 精细刻画,与古寺的庄严形成呼应。寺院周围,修竹成林,以 “个”“介” 字形笔法写竹叶,疏密有致,增添了几分雅致。 远景:秋山的缥缈背景
画面上方,主峰巍峨耸立,山体以 “解索皴” 结合淡墨积染,顶部用石青轻罩,山脚处云雾缭绕(以留白表现),形成 “山欲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 的视觉效果。主峰两侧,次峰如羽翼舒展,以淡墨勾皴,与前景的古树形成呼应,共同构成 “环抱古寺” 的守护格局,使画面中心的萧寺成为被秋山环抱的 “尘外之境”。
二、笔墨:元人法度与个人风格的融合吴宏在此作中展现了 “师法元人,自出机杼” 的笔墨功力,既有黄公望的 “苍劲”,又具王蒙的 “繁密”,更融入了明末画坛的写意精神: 山石的皴法创新:虽题 “元人画法”,却突破元人单一皴法 —— 主峰用 “解索皴” 表现岩石的嶙峋,次峰以 “披麻皴” 体现土坡的温润,近景岩石则借鉴唐寅 “乱柴皴”,以短促侧锋线条模拟柴枝交叉,较元人更显刚健,隐约可见其后来 “金陵画派” 的风格雏形。 墨色的层次递进:采用 “积墨法” 层层渲染,近景古树用浓墨提神,中景古寺用淡墨渲染,远景山峰以极淡墨色晕染,再以花青烘染天空,形成 “由实入虚” 的墨色梯度。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增强了空间纵深感,还通过墨色的冷暖变化(近景偏暖,远景偏冷),暗示了秋日的光照特征。 点染的节奏美感:树叶、苔点以 “攒三聚五” 之法分布,密集处如重奏,疏朗处如休止符,形成视觉上的韵律感。尤其是古松的松针与修竹的竹叶,虽繁密却秩序井然,体现了 “密不透风,疏可走马” 的构图原则。
三、设色:秋山古寺的雅致色调画面以“浅绛山水”为基调,辅以石青、石绿,营造出深秋时节 “霜叶红于二月花” 的绚烂与静穆: 四、款识与意境:师古与寄怀的双重表达款识 “元人画法” 背后,隐藏着吴宏的创作深意: 对元人精神的继承
元代画家多以山水寄托隐逸情怀,吴宏题 “元人画法”,不仅指技法上的师承(如黄公望的浅绛设色、王蒙的繁密构图),更指对 “不求形似,唯求意韵” 文人画精神的认同。画中古寺的静谧、秋山的萧疏,均暗合元人 “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 的审美追求。 对时代语境的回应
1642 年(壬午年)为崇祯十五年,明王朝已近覆灭,社会动荡不安。吴宏选择描绘 “秋山萧寺” 的清寂之境,可能暗含避世之心 —— 古寺象征精神净土,秋山隐喻乱世,二者的结合体现了明末文人 “处江湖之远” 的无奈与坚守。 地域文化的潜在表达
画中溪流的蜿蜒、山体的平缓,虽题 “元人画法”,却隐约可见江南山水的影子,暗示吴宏作为南方画家对地域风貌的潜意识表现,为其后来形成 “金陵画派” 的风格埋下伏笔。 【观图显诗意】凉气晚萧萧,江云乱眼飘。风鸳藏近渚,雨燕集深条。黄绮终辞汉,巢由不见尧。草堂樽酒在,幸得过清朝。
五、鉴藏与流传:画史脉络中的作品定位鉴藏印 “胶西周氏古琴阁”“新建吴氏珍藏金石书画之印” 等表明,此作曾为周墨南等收藏家递藏,其价值可从两方面认知: 结语:绫本上的秋寺钟声吴宏的《秋山萧寺图》以细腻的笔触、雅致的设色,在绫本间铺陈出一个远离尘嚣的精神家园。画中古寺的红墙在秋山的映衬下格外醒目,似在诉说着 “深山藏古寺” 的禅意,又似在隐喻着乱世中的精神坚守。这幅作品不仅是吴宏对元代山水的致敬,更是一曲写给明末文人的心灵独白 —— 它让我们看到,在王朝更迭的动荡中,总有一片秋山深处的古寺,守护着中国人对宁静与超脱的永恒向往。当观者的目光掠过画中的溪桥、古树、萧寺,仿佛能听见穿越时空的钟声,在秋山的寂静中回荡不已。 《秋山草堂图轴》清 吴宏 墨染秋山草堂静 —— 吴宏《秋山草堂图轴》赏析清代画家吴宏的《秋山草堂图轴》以秋山萧瑟、草堂静谧为主题,延续了 “金陵八家” 清刚雅正的艺术风格,融合宋元笔墨与江南景致,构建出文人理想中的栖居之境。画面中,吴宏以苍劲的笔触、清逸的设色,描绘了秋山环抱、草堂隐现的诗意场景,既有北宋山水的严谨构图,又含元代文人画的萧疏意韵,展现出对传统山水图式的创造性转化。 一、构图:秋山环抱的隐逸空间画面采用“三段式构图”以近、中、远三重空间层层递进,营造出 “山深人不觉,犹在画中游” 的意境: 近景:溪岸的秋意引子
画幅左下角,溪流蜿蜒而过,以细笔勾勒波纹,水口处用焦墨点染碎石,模拟水流的湍急。溪岸巨石嶙峋,以 “斧劈皴” 结合淡墨皴擦,石面肌理粗糙,间以赭石色轻染阳面,展现秋日阳光的温和。岩石间,杂树疏落生长,树干以双钩法勾勒,枝条作 “蟹爪状” 低垂,树叶用 “介字点”“垂头点” 交替点染,墨色浓淡相间,既有黄叶飘零的萧瑟,又有松柏的苍翠,暗示秋意渐深。 中景:草堂的核心叙事
画面中部,草堂坐落于坡地之上,白墙黛瓦,以淡墨勾勒轮廓,屋顶用赭石色平涂,门窗虚掩,门前小径通向溪桥。草堂内,二文人对坐论道,一人展卷阅读,一人拄杖倾听,童子侍立烹茶,人物虽小却神态悠然,衣纹用 “铁线描” 勾勒,线条流畅。草堂周围,竹篱环绕,修竹以 “个”“介” 字形笔法写竹叶,疏密有致;几株红枫斜出,叶片用朱砂点染,为秋景增添暖意,与草堂的静谧形成呼应。 远景:秋山的缥缈背景
画面上方,山峦起伏连绵,以 “披麻皴” 结合淡墨积染,表现出江南丘陵的平缓与温润。山顶草木稀疏,以赭石与花青交替渲染,山脚处云雾朦胧(以淡墨湿笔晕染),形成 “山色有无中” 的朦胧感。远景与中景之间,留白处理的江面开阔平静,一艘渔舟停泊,渔夫独坐船头,既延伸了空间纵深,又暗合 “渔隐” 主题,与草堂的文人雅趣形成呼应。
二、笔墨:工写兼济的秋韵表达吴宏在此作中展现了 “落笔苍劲,收拾含蓄” 的笔墨特色,融合北派的刚健与南派的灵秀: 山石的皴法融合:近景岩石用 “斧劈皴” 侧锋疾扫,线条刚劲如铁,尽显北派山水的骨力;远景山峦以 “披麻皴” 中锋缓写,线条圆转流畅,体现南派山水的韵致。这种 “刚柔并济” 的处理,既表现了秋山的坚实,又赋予其温润的江南特质。 树木的工细与写意:松树、柏树刻画细致,松针分组排列,柏叶以 “攒点法” 密集点染,虽繁密却秩序井然;杂树、红枫则以 “写意” 为主,枝干转折自然,叶片点染随性,体现 “工写结合” 的技法智慧。 水墨的氤氲效果:全画以 “湿笔淡墨” 为主,山石、云雾均通过水墨晕染形成自然过渡,尤其是远景山峦与江面的交界处,水墨交融似有若无,体现 “墨分五色” 的层次感。秋树的枝叶间以浓墨点苔提神,如翡翠嵌于铁石,增添画面生机。
三、设色:浅绛秋山的雅致基调画面以“浅绛山水”为基础,辅以花青、朱砂,营造出江南秋日 “天高气清,霜叶红于二月花” 的氛围: 四、意境:草堂之外的文人哲思《秋山草堂图轴》不仅是江南秋景的写实描绘,更是文人精神世界的诗意投射: “草堂” 的符号意义
草堂作为核心意象,延续了陶渊明 “五柳先生”、杜甫 “成都草堂” 的文化基因,象征文人对简朴生活与精神自由的追求。画中草堂隐于秋山之间,远离市井喧嚣,却有文人雅集、童子侍茶,体现了 “大隐隐于市” 的处世哲学,暗含清初文人对现实的疏离与对精神净土的坚守。 “秋山” 的时间隐喻
秋日在传统文化中常象征生命的成熟与沉淀,画中疏朗的秋树、寂寥的溪岸、静谧的草堂,构建了一个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的精神图景。吴宏以秋山的萧疏隐喻人生的起伏,以草堂的宁静暗示内心的坚守,反映了中国文人 “以自然喻人生” 的思维范式。 地域文化的隐性表达
画中平缓的山峦、密集的修竹、临水的草堂、停泊的渔舟,均为江南(尤其是南京周边)典型地貌,吴宏通过细腻的笔触,将地域风光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山水图式,体现了金陵画派 “师法造化,中得心源” 的创作理念,也为江南文化增添了视觉注脚。 题识:老树摘秋光,藤阴骋草堂;教儿通句读,(下面字迹模糊,恕难识全。)
五、与吴宏其他作品的风格呼应对比吴宏的《松溪草堂图》《秋山平远图》,此作展现出其艺术的典型特征: 结语:墨色秋山里的精神栖居吴宏的《秋山草堂图轴》以水墨为骨,以色彩为韵,在尺幅间构建了一个可居可游的精神家园。画中没有奇峰异石的视觉冲击,只有寻常的秋山、朴素的草堂、悠然的文人,却让人感受到一种直击心灵的宁静 —— 那是对江南秋景的眷恋,是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更是对文人精神家园的永恒追寻。这幅作品不仅是吴宏艺术风格的缩影,更是中国传统山水 “以画栖心” 精神的生动诠释,让观者在水墨烟霞中,触摸到秋日江南的疏朗与深邃,以及一位画家对 “诗意栖居” 的终极思考。
顾绍骅于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