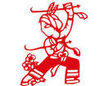悼念父亲
父亲走了。轻轻的,就像他来到这世界上一样。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出生,翻腾了八十多个春秋黄土,复归于黄土。
死了了了,正如无数已经死去的农民一样。然而,父亲绝不只是一个普通农民,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华民族的几个历史巨变过程,尤其是养育我成长并由此深深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个时代,面对无法抗拒的贫困、看不见尽头的饥饿折磨、始终不离左右的生存威胁,他用自己孱弱多病的躯体,支撑着一个七口之家,与贫穷、饥饿、疾病作了殊死的抗争,付出了肉体难以供给的辛劳,承受了生命难以承受的痛苦。他用混着泥土的汗水,用毕生的精力在黄土地上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命运交响曲,用带着呻吟的喘息声奏出了它的最强音。在父亲普通农民的肉体上附着的是一个神圣一般的灵魂。他所经历的苦难是中华民族苦难的缩影,不该被忘却;他表现出的无可比拟的勤劳精神是中华民族勤劳美德的化身,应与民族共存。
父亲出生于1923年1月22日、农历壬戌年腊月初六,据史书记载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民不聊生;据母亲说我的爷爷懒得出奇,家里一贫如洗;据父亲讲他在九岁的时候就开始赶着毛驴卖炭。父亲是腊月里的生日,农村人说虚岁,实际上他才满七岁!父亲36岁时生的我,我记事时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已是40岁出头的中年男子,当着生产队的队长,精明强悍,顶天立地,无论多黑的夜晚,只要父亲在身边,便什么也不用怕,无论有多大的难事,父亲总会有办法。家境也相当“殷实”,那时村里的穷人家很是不少,青黄不接时没有吃的,寒暑易节时没有穿的,天寒地冻时没有烧的,而我们家则全然没有这些困扰,有时还向他人出借粮食。父亲白手起家,但那时我们家一应家用器具,几乎应有尽有,万事可不求人,这在我们村几乎是独无仅有的。所以儿时的我,夜郎自大,由此颇有过几分对于出身的优越感。
在长大后我才渐渐知道,父亲把我带到了一个有名的穷地方,而且那时刚刚过了可怕的六零年,依旧处于贫困的年代。
如果人生是老天安排的,那父亲一定是受到老天爷贬谪的。父亲生在晋西黄土高原上一条偏僻的山沟里,那里沟如龙蟠纵横相衔,山似虎伏首尾互抵。用牛耕地,靠天吃饭,风雨不时,十年九旱。我们家那时能过得去,除了沾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光以外,全靠父亲的勤劳与节俭。勤劳本是一切农民的生存之道,但人生来带有几分惰性,而且人毕竟是血肉之躯,总有疲劳的时候,风里来雨里去,也难免有个头疼发热的时候,人原本是有七情六欲的动物,贪图享乐似乎也是合理的需求,然而父亲几乎颠覆了人的本性,他的勤劳简直登峰造极,村里人说他“贱骨头”,从不让自己消停一会儿,不管何时何地,他总能找出一些事来做;不论春夏秋冬,我从未见过父亲在有太阳的时候睡过觉,甚至打过盹儿;除了晚年身体完全垮下来以外,一生休过大约一周的“病假”,那还是由于在胯上挖了一块大疮,实在是不能站立了。父亲放松自己的方式仅仅是吸一袋旱烟,连伸懒腰、打哈欠这样极平常自然的生理反应动作都没见父亲有过。父亲不仅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而且,无论干什么,动作都非常之快,行路时,与他同行你得小跑才能跟上……我时常会有这样的疑问,是否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父亲身上下了咒,才让他终身不得停歇?
六十年代初期,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定型。就行政区域大小来说,那时的公社相当于后来的乡、镇。但“公社”一词显然并非区域类词汇,而饱含了政治色彩。所谓“公”就是土地公有,所谓“社”就是实行农业合作社制度:一个公社管辖若干生产大队(一个生产大队一般是一个自然村落),土地归生产大队所有。一个生产大队又根据村落的大小分为若干生产小队,简称生产队,我们村编了10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由20多个劳力、100余口人组成。每一个村民被编入生产队,称为“社员”。社员就在农业社里劳动并登记工分,到秋后根据农业社的收成分红。产的粮食先给国家上交公粮,然后社员分,生产队产什么就分什么、吃什么,吃粮标准是每人每年360斤(猜想是按每人每天一斤的“标准”计算,还剩五天大概是让肚子过礼拜吧),社员分够后如果还有剩的,再按“余粮”卖给国家。社员挣的工分,若秋后扣除口粮款后还有盈余,还可以分红。另外,作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补充”,还配发了一点“私有财产”即自留地。这样,既取消了之前搞的集体劳动、集体吃饭式的“共产主义”,又保留了一点“资本主义”的自留地(由此称为社会主义?),农民可以部分把握自己的命运。刚刚经过噩梦般的六零年的人们,自然会像落水的人碰上了岸边的树根,使尽全力抓住自救。那时我们家就父亲一个劳力,全家老少六、七条性命都扛在父亲肩上。
民以食为天。还好,农村本来就是出产粮食的。然而粮食是极其有限的:农业社里分的粮食,每人每天不足一斤,而且都是连皮、带壳、含水的粗粮,并不像城里人供应的都是白面大米般的细粮;自留地好年景时每人也不过添得几十斤。除了吃饭外,还要吃盐、穿衣、点灯、烧煤等等。虽然这样样所需之物土里不长,但是只要有了一样东西便会全有,那就是钱。问题是钱从哪儿来呢?照“经济学”的原理说,农民可以通过出售余粮来换钱。但是首先要有余粮可卖!十年九旱、靠天吃饭的地方,能有多少“余粮”?况且,即使卖上一点也换不得几个钱,因为国家收购粮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就个体来说,一个农民一年在生产队里的全部“收入”仅仅是二、三百个工分,工分的价值还要看年景的好坏,好年景再加人口少或劳力多的情况下,秋后扣除口粮款后还可以分得一点现钱,一般一个男壮劳力只能勉强挣够三口人的口粮钱。如果工分不够口粮款时,还得先给生产队交口粮款,然后才能分得粮食。我家自然是属于后者。没有粮换不来钱,没有钱又分不到粮,没有粮……这分明是一个死结。父亲全部的辛劳就用于解这个结。
粮食问题相对简单。主要来源是生产队,其次是自留地。所以一是盼生产队多打粮,二是多挣自己的工分,三是捎带种好自留地。那时正值壮年的父亲,当着生产队的队长,生产队搞得好坏应与之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队长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苦差,因为生产队该种什么并不由队长或社员做主,而是由公社决定,每年春播前都会下达所谓的“种植计划”,规定诸如高粱多少亩、小麦多少亩、土豆多少亩等等。因为国家收购粮是不要土豆的,种的土豆多了虽然百姓有的吃,但是国家的公粮任务恐怕完不成。队长的职责就是决定今年的高粱是南山种还是北山种而已,并没有自主权。另外,手底下的社员除了本本分分的庄户人家出身的以外,不少人有偷懒心理。所以,当时在生产队劳动俗称“跟农业社”,说得很是形象,不是跟着“跟着走”就是“跟着遛”。作为苦差的补偿,生产队长一年享受20个工分的补贴。然而这点补贴与父亲的额外付出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一来父亲天生勤快,不管在哪里干活,父亲从不会偷懒,他的口头禅是:“力气使了又来了”,就是说,力气使出去了它还会自己长出来,是没有穷尽的。二来父亲是队长,他要偷懒,别人谁干?第三是父亲有强烈的愿望,就是多打粮食。所以父亲总是下地时走在最前,收工时走在最后,啥活没人愿意干他就干啥活,而且从来舍不得误一天工。对于自留地只好抽空干了。但是自留地也是很重要的,在粮食实行限量供给的年代,自留地不啻是生命的缓冲带、救命的稻草,人们恨不得种出金子银子来。俗语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春天要施足底肥。上乘的农家肥是人类亲自造出来的,但那时这东西虽产于自己的私密处,却已被农业社占有了,属于“管制品”!自留地只能限量供给。这样人们只能退而求其次——用畜牲造出来的,所以农民家里都养猪或羊。猪、羊圈里产出的肥料大部分是人垫进去的黄土,一担一百多斤重。为多打点粮食,父亲每年春天都要利用生产队的休息时间把数吨重的猪羊粪用双肩担到自留地里,而且我家的地都在离村子很远的山上。选自留地时一般人都挑村子边上的地,种与收都省力,父亲则不然,因为离村子远的地丈量时面积稍有优惠,所以舍近求远。到了夏天锄草、间苗时,常常是大中午生产队收工了,父亲再顶着烈日干自留地里的活。秋收时生产队的活非常忙、非常累,我家自留地的庄稼一般是等到把生产队的都收完后才去收,有些不能等的,往往是由母亲带着我们几岁的孩子去收割。
这样,父亲从正月过完年一直要忙到将近立冬为止,也就是从大地刚开始解冻一直忙到大地重新封冻。
尽管如此,粮食还是极其有限的。农业社口粮360斤封顶,而且粮款挣不够还不能全部分到家;自留地每人几分旱地,三分靠人,七分靠天,有一年没一年。所以挖掘粮食只能用最后一招,也是最有效的一招,就是“厉行节约”——实际上是从嘴上硬性克扣。节约是相对于浪费而言,那时根本够不上浪费,又何谈节约!克扣是要讲究技术的,并不能给嘴贴上封条了事。秋天收粮食的时候,也是各种粮食的代用品最为丰富的时候,像萝卜叶子、红薯蔓子、米糠等等,父亲都要尽可能多地收集起来,整个冬天添加到粮食里面一起吃。添加的比例要视当年的收成而定。对于父亲这样的做法,我当时是持反对意见的,每次在做饭前抗议,吃饭时闹情绪。但是父亲坚定不移地推行他的政策,而且自己总是做出表率:无论我们觉得多难吃的饭,父亲都甘之如饴,从来没有说过有任何饭不好吃!这样做起到了双重节约效果,一是用较少的粮食做出较多的饭,二还可以有效地防止人吃得过饱。当时甚至有点仇恨父亲,长大后才理解了父亲这样做的苦衷。老实说不是父亲如此的精打细算,在后来的一些年份里我们全家可能就需要在被饿死或沿街乞讨之间做出选择。所以尽管在粮食并不富余的情况下还要粜一部分,我们家即使在最困难的年份里也没有断过炊,不仅没有饿死,而且还保持了做人的尊严。父亲一生非常节俭,从来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也从不在外面买东西吃,更不用说下馆子大吃二喝,对于我们也一样,容不得浪费任何东西。富而节俭一般认为是一种美德或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若穷而节俭就很少被认为是美德,因为别无选择。但是穷而节俭不是吝啬,吝啬是富人的专利。
虽然如此,为着得到钱我们家也卖粮,但卖的不是“余粮”,而是“好粮”。卖掉的都是当时十分珍贵的麦子、小米等好粮食,不为别的,只为价格高。卖粮的目的是为着买粮。就是以“高价”卖掉好粮,换的钱交生产队口粮款,然后领回其余口粮。市场上卖一斤好粮可以换回生产队的七、八斤口粮。这就是后来说的粮价“双轨制”现象,我家就是沾了这“双轨制”的光,才在口粮款挣不够的情况下能以粮易粮,使粮食周转起来!
硬性地从嘴上克扣下来的粮食不能叫余粮,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卖的,要钱还得另想办法。
然而钱岂是易来之物!对于成年累月地只在黄土地里连饭食都刨挖不够的农民,要得到几乎万能的钱,只能说比上天摘星星要容易一些。然而真应了那句俗话——天无绝人之路:钱虽然无比金贵,但竟也有“代用品”,而且还是当时最最不值钱的东西!
若论重量,烧恐怕是农村生活最大的一项消耗了。农村烧的有三样东西:庄稼秸秆、野生柴火和煤炭。庄稼秸秆生产队里倒是免费分配,但是“豆萁”远远不够“煮豆”用,而且许多种秸秆还是生产队的牛羊越冬的食物,并不能烧掉。所以大部分烧的是后二项。在村里买煤每斤才一分钱,但是一冬天少说也得烧掉近千斤的煤,一千斤可就十元了,十元钱在我家就是一笔巨款。若到煤矿上买煤每斤却只有三、四厘钱,一千斤就可以节约六、七元。但是最近的煤矿也有三、四十里路,且要翻两座山。就是为着省这几元钱,父亲每年要在农闲的隆冬季节直接到煤矿上去买煤。早披繁星走,晚戴残阳归,挑百、八十斤重的担子,走七、八十里远的山路,需往返十来趟、计行程千余里,饿了啃带糠的窝头,渴了饮结冰的河水,那份苦村里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承受。
可是煤仍然要钱买。所以除了冬天取暖用煤外,我们家一般不烧煤。烧野生柴火不用花钱,但需要父亲去砍。我们那里虽是山区,但山上并没有树木或植被,等到秋收后看,一个个山头恰似和尚的头,圆溜溜、光秃秃的。而且那时大家都在砍柴烧,所以砍柴很不容易。像样的柴火大都在远离村庄且无人能够得着的悬崖峭壁上。父亲从小练就了砍柴的技术和胆量,别人去不了的地方,他拿一把镢头刨几下就修出了“路”,砍柴时的惊险常令看着的人为之咂舌。平时在生产队地头休息时,别人或抽烟拉闲话或呼呼大睡,父亲却在附近的悬崖峭壁上找柴火;收工后,别人急着往家跑,父亲却非把发现的柴砍走。隆冬季节生产队一般不开工,父亲把一冬的煤担够后,有时间专门去砍柴。隆冬季节滴水成冰,一般人总是吃饱饭后找个暖和的地方扎成一堆聊闲天(村里人叫“打闲”),父亲则难得享受这样清闲的日子。直到现在我依然记着父亲那时砍柴出走和归来的样子:吃完早饭后跟母亲说一声要去的地方,其用意大概是万一出事时方便寻找。出走的时候太阳照在朝东的山崖上,父亲戴一顶虎头帽,上身穿一件黑色棉袄,腰里系着白色的腰带,下身穿灰色的土布中式棉裤,用白布条扎着裤腿子,脚上穿着母亲自己缝的双层白布袜子和方口布鞋,袖着双手,腋下倒夹着一把镢头,肩上搭着一条两丈多长、手指般粗细的麻绳,口中呼出长长的白气,鼻尖上有时会挂着一滴清鼻涕,下了坡走到河滩里,河面上的冰渣在脚下嘎嘎作响……等回来的时候,只有远处的山尖上朝西的一面还映着天空淡红色的光亮,借着那点光亮,看见远处的父亲背着一大背柴火朝家走来。到我家院里还要上一道长长的陡坡,父亲背着约有一、二百斤重的柴火,上坡时被压得脸几乎要贴着地面,每一步只能挪出几寸距离,脚落地时踏出沉重的咚咚声响。满面尘土,胡子梢上和帽子边上结着白霜,到院子里把柴火放下后,后背上却腾腾地冒着热气。等把柴火解开摞好后,父亲才解下腰带打掉身上的尘土……一个冬天父亲砍的柴火,要在二十来米长的院子边上堆起两米多高的一道墙。那时我家院子是敞开的,父亲砍的柴火就当围墙用,更可当好几千斤煤烧。
然而,省得煤钱省不得油钱。现钞或多或少是要有一点的。
对于没有手艺的农民,唯一的生钱之道就是饲养猪、羊、鸡之类的家畜、家禽。我们家亦如是。然而稍一算账就会知道,实际上这并不赚钱,比如养猪。那时个人养的猪要卖给国家,国家收购生猪的最低标准是一百二十斤,价钱根据大小与肥瘦划分等级:大而肥者能给二等,绝少有养到一等标准的,刚达标者只给三等,价钱是每斤三毛。要把猪养肥必须得吃粮食,那时一斤高粱都可以卖到两、三毛钱!再上膘的猪也不可能吃一斤粮而长出几斤肉来,何况那时并没有现在的催肥术。父亲养猪的理由是一图变钱,二图攒粪。由于喂不起粮食,我们家养的猪主要吃粗糠和草。然而光吃糠和草根本不可能把猪养肥,所以我们家养猪只养一幅“骨架”,等到需吃粮食催肥时一般就转手卖了。养猪羊时,割草几乎也都是父亲一人的事,所以只要地里有青草,父亲下地时身上总是挎着一个大袋子,在耕地或锄地时顺便把遇到的草收集起来,也利用地头休息时间和往返沿途采集草。因此父亲从地里回来时,不是背上背着或肩上挑着柴火,就是腰里斜挎一布袋草,通常是两者兼而有之。辛苦多半年喂大一只猪或羊,不过换得十几元——有时只有几元钱,为着寻觅、采集千万苗的小草,却不知要走上多少里路、低头弯腰又要多少次……这正是村里人说的——在土疙瘩缝里抠钱!还好这不费多大力气,只是花些功夫而已,然而就是这“功夫”使得父亲与闲暇、休息等基本绝缘。
父亲的辛劳,再加上母亲纺花织布的操持,钱虽然紧缺——世上本来就没有不缺钱的人,左右看看别人,我们家有吃有穿,日子过得还算满足。好在我们家除了交纳口粮款外,一年大概有二、三十元钱就可以活下去了。
死结也许是不可能解开的,尤其是仅凭父亲的一点力气在土疙瘩林里翻腾。或许这就是生活本来的面目。但是由于父亲的勤劳,这个死结得以最大限度的松动。在父亲强有力的臂膀支撑起来的家里,我——一个在穷年代、穷地方、穷人家出生的孩子也有着温暖幸福的童年。
然而,在随后十几年的岁月里,这个死结就像是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儿听到了唐僧的咒语,越套越紧,离被套死也就是差一口气。父亲为着松开它,所付出的努力已远远不是勤劳二字所能包容的。
“文革”来了。的确是“史无前例”!就连我们交通闭塞的小山沟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虽说经济贫穷、文化落后,却不妨碍保持政治的“先进性”!以大破“四旧”发端,矛头指向“牛鬼蛇神”,上房搬兽头,入户抄古董,焚书拆庙,颠覆传统。引深到“灵魂深处闹革命”,导致有的人心理畸形:睹富丽美艳之物如犯忌之品,必毁之而后安;视穷酸破烂为“革命本色”,崇之尚之。接着大搞“路线斗争”,专批当权的“走资派”,到“狠抓阶级斗争”,就人人有资格挨批了。革命革命,最后终于革到百姓的“命”上了。
文革伊始,“革命群众”在下面批斗批得头晕脑热,“革命干部”在上面争权争得你死我活,没几时就“天下大乱”了,对于“高瞻远瞩”的“革命家”来说, “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只是耍的一个小小的手段,在此过程中可以尽情享受“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风流潇洒,但是,农民——革命的“基本群众”,恰如乘着无桨的小舟被抛入惊涛骇浪中的渡客,感受到的恐怕只会是恐怖而已——如果还容其“感受”的话。
农村里几乎没人管,村干部害怕犯错误挨批斗,只敢“抓革命”,不敢“促生产”。“革命群众”都是惹不起的角色,生产队选一个队长就很困难:“敢闯敢干”的不能吃苦又不通农业技术,大家不放心,能吃苦懂技术的又惹不起“敢闯敢干”的,自己不愿干。选来选去最后当上队长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受人拥戴的老好人,另一种是离不开的人。父亲最后还是继续当上了他的队长,但他是属于后一种情况。跟过农业社的人都知道,大部分“社员”有合伙熬粥的马车夫心理,都指望着别人出力,或天天只干轻省的活。所以当生产队长不仅要精通农事、能以身作则、苦累在先,而且还要会管人。前者父亲是无人不服。但是管人就不在行了,其一,父亲急性子、暴脾气,看见偷懒耍奸的人忍不住要数说几句,为此得罪不少人;其二,在人人都想偷闲的情况下,他却不识时务,农忙时常常让社员加班加点,所以不少人不欢迎他当队长。但是,人们也都清楚,父亲对生产队极端负责,在那样的年代父亲让当队长最放心,毕竟活命比啥都要紧。最反对父亲当队长的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害怕他得罪人。父亲自己很愿意当队长,但绝不是有“官”瘾或有利可图。生产队长有职无权,那不叫官;一年额外补助几个工分,根本补偿不了所受的劳累和由此带来的其它损失。记得当时父亲说过:“我们家七口人,全靠农业社活,现在乱的没人管,万一农业社倒塌了,七口人就没活法了。”所以他要拯救生产队,同时也拯救我们家。
由于农业社收入极低,正常情况下一个工分通常也只能分到三、四毛钱,更何况在世道大乱的情况下,人们越发不看好农业社,没有了强力管制,年轻力壮者大都干别的营生去了,或外出打工,或从山里倒卖木料,甚至有的混迹赌场,剩下死守着农业社的基本是老弱病残者、老实巴交的和人口多、不敢冒险外出的,合起来只有七、八个劳力。春天播种时,一般要出三头牛,一头耕牛需配六、七个劳力,正常时候一个生产队的男劳力正好且略有富余,但那几年根本凑不齐这么多人。因为播种要赶节气或趁墒情,为着凑够一班人马,父亲叫张三、喊李四,有时还得登门求告,通常要把十岁左右的男孩都动员上,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反正那时的学校也不正常。如果凑不够三头牛的人手而只能出两头牛时,通常会延长劳动时间,直到把牛累得卧倒在地,鞭子用力抽打都起不来时才收工。上工时到处听见的是父亲吆喝人的声音,到了地里父亲啥活没人干就干啥活,往往一个人要干两、三个人的活。到了夏天庄稼出苗后,要趁苗小时选苗、间苗,由于用的工具是一把小锄,所以土话叫“小锄”。由于播种时墒情不好,怕种子发不了芽而缺苗,所以下种量较大。一旦种子都发芽、出苗就特别稠密,间苗晚了就会严重影响幼苗的成长。而且此时正是龙口夺食的夏收时节。由于人手少,每个人几乎要忙到极限:清早天刚亮下地,早饭送到地里,中午熬到日头偏西,收工回家补充给养,稍事休息,下午继续干到天黑看不见为止。小锄时,人得蹲着,身体折成三折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时值夏至前后,正是昼长夜短之时,干活时间长不说,尤其在中午那会儿,背受烈日暴晒,面被地面蒸烤,如同在炼狱里煎熬,而父亲每天都要熬过晌午才收工。一般人难以忍受,故颇有微词,而父亲根本不顾别人的感受,每当此时,父亲总是一声不吭,只是手下更快地干着活,为别人做出样子,他干活不是干,而是抢。他为庄稼着急,只能咬紧牙关坚持、再坚持。由于父亲的表率作用,别人也无可奈何,慢慢的就习以为常了。实际上父亲也是血肉之躯,并不比别人强壮,因为人手少,他必须这么做。那几年当队长,父亲为搞好农业社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以至于根本顾不上管理自留地,许多活竟让我——刚满十岁的孩子独自去干!在父亲苦心经营下,仅靠不足十个劳力耕种着生产队的全部四、五百亩土地,虽在动乱的年头仍维持了正常的生产,收成也要略好于其他生产队。不仅让我家能苟全性命于乱世,也惠及生产队的其余百余口人。
然而,遗憾的是父亲那几年的辛苦并没有换来好日子。中国古人确信天人感应,但天道幽冥无从考证。人们常把“天灾”“人祸”连在一起,也许是因为二者常结伴而行,或许也可以作为这个信念的旁证吧。事实是,文革那几年我们那里竟然应验了这个信念,年年遭灾,春天墒情不好下不了种,好容易长出苗了,夏天又晒个半死,农民今年看明年,明年盼后年,竟然没有遇见一个好年景!仿佛老天也玩弄、甚至是惩治百姓。本来在靠天吃饭的山区,靠几个劳力养活一百多口人就不是一件易事,不用说老天降灾,如果不帮忙,人已经承受不起。所以那几年不仅没有“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而且连自己的口粮都打不够,常常是今年先交了公粮,来年再吃国家的“返销粮”。当然交的是晒干的麦子、谷子、黄豆等粮食,“返销”的就成了红壳子高粱甚至是红薯片。但是毕竟大家的命还是保住了,然而都是在生死线上挣扎着过来的。
一般来说,人们会认为“治世”好于“乱世”,正如古人说:“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但是,世道竟也有颠倒的。
文革中期,武斗被叫停了。荷枪实弹打得你死我活的“革命”与“反革命”两派几乎是一夜之间又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终于由“天下大乱”达到了“天下大治”。打也为“革命”,和也为“革命”,革命是要进行到底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头一件事还是夺取政权,不过不能用枪杆子。大概是1968年,县里从外地调来一位县委书记,到任后一看百姓的生活状况极为震惊,马上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那时的百姓被尊称为“革命群众”,上级部门不敢怠慢,立即不知从哪儿调来大批的红薯片救济百姓,此举不知救了多少条人命,全县百姓由此极口称颂那位书记的功德,以至于我——那时还是刚满十岁的小孩到现在依然记得他的名字叫邓峰。本来这位书记从外地而来,与当地的派系没有恩怨,又有恩于当地百姓,但是很快就被夺了权。“革命委员会”刚刚建立,就从上面传出“革命舆论”说,邓峰是个讨吃书记,要坚决打倒!果然是高手出招,专打软肋,一击致命,没过几天就被批倒了,换了一个新书记。这新书记果然大有“志气”,不仅表示坚决不吃国家的救济粮,还扬言要实施粮食亩产“达《纲要》”、“跨黄河”、“过长江”三步走的宏伟战略,多交余粮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应该说这种“革命精神”确实可嘉!接下来 “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抓革命,促生产”的措施不折不扣的执行,“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更是常搞不懈,革命形势步步紧跟……然而土地是冷静的、诚实的,它只听从唯一理智的自然法则,结果是粮食产量不仅没上去,反而一年不如一年。但是卖“余粮”是硬道理!运动、口号都是花架子,真功夫总是最后使出来:先把原定的每人每年360斤的吃粮标准降到280斤,然后十二岁以下小孩吃粮按年龄打折(当时叫折成)。土豆、萝卜、瓜菜等也要折合成粮食凑数;最后干脆瓜菜等啥也不许种了,所有的地里都种上“红”一色的“高产”作物——五号高粱。为着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把原来分给个人的自留地没收了,理由很是“冠冕堂皇”,叫“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取缔了一切买卖,堵死了所有的财路,把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里都驱赶到黄土地上围着粮食转:天暖了种田,天冷了“造地”。地从哪里来?向龙王要!政策要执行的龙王爷头上了……天地良心!这每一项措施——除了龙王爷吝啬以外,其效果都是“立竿见影”的。但是……但是说什么好呢!亲历过的我现在不还依然活着吗?
但是谁又知道能让我活下来,父亲是怎样熬过那段岁月的!
开始的几年里,父亲大部分年份依然当着他的队长,但是队长已经不起啥作用了。春天上面有严格的“种植计划”,绝不能违抗。秋天庄稼尚未收完,生产大队就直接管上了:全村统一行动,所谓“学大寨”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社员都似苦役犯,队长就是犯人中的犯人。没有亲历过的人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那时的人怎么可能活下来呢?我只能说:这就是奇迹!或许是那个时代的人发明的一种新的“营养品”——“精神食粮”起的作用吧!不过,那时高处的树叶、地上的野菜凡能吃的都被人吃光了,甚至于地底下黄鼠藏下的食物也常被人类盗走。
终于,父亲的身体开始垮了,队长是不能再干了。实际上父亲也老了,彻底不干队长的那年,他已经54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