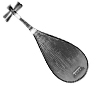一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出了“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的论断,认为作者的精神活动,亦即为文之用思,受着“志气”的统辖和控制;此后,又专作《养气》之篇,“所以补《神思》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1〕,可见两者关系密切, 故研讨《神思》篇必及于《养气》;探究《养气》亦必兼至《神思》。
刘勰所谓的“养气”,究竟具有怎样的具体内涵呢?
“气”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各家在言及“气”时,含义很不一致。孟子有“知言养气”之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2〕这是一种主观的道德和精神修养。 周振甫先生扼要地把它概括为一句话:孟子“所说的养气就是培养一种正义感”〔3〕。王充的《论衡》中曾有《养性》之作,虽已失传,但从其有关著述中可得到旁证,他讲的主要是一种延年益寿的养生之道。如《自纪》中所说:“养气自守,适时则酒,闭目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曹丕的《典论·论文》,首开以“气”论文之先,响亮地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主张,认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此说主要是指作者先天的气质和个性,以及其与作品风格的关系。
刘勰《养气》篇所言之“气”,虽与上述诸说不无联系,但其具体内涵和旨归却是不同的。刘勰讲的不是道德精神修养,不是养生之道,也不是作者的气质、个性和作品风格,而是为了保证“文思常利”,所必须具有的体力和精力,心境和情绪。《神思》篇说:“养心秉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养气》篇则补充说:“纷哉万象,劳矣千想。玄神宜宝,素气资养”,不要因“钻砺过分”,“销铄精胆”,造成“神疲而气衰”的状况,这显然是指精神力气而言的。《神思》篇提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养气》篇则又进一步阐发说:“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这显然说的是作者临文时的心境和情绪了。
那么,是不是培养起了充沛的体力和精力,良好的心境和情绪,即可获得“文思常利之术”呢?不是的,体力和精力,心境和情绪,在写作构思过程中,固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它们只是构成“统其关键”的“志气”中的部分内容。《养气》篇所言之“气”,与《神思》篇中的所谓的“志气”,是既相互联系,相互补充,而又不能等同归一的。大致而言,“志气”中包括着《养气》篇所言之气,却并不仅仅是体力和精力,心境和情绪。
在《文心雕龙》全书中,“气”字的含义也很宽泛,在不同的章节、范围内有不同的用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指作者的气质、才气,如“才有庸俊,气有刚柔”。(《体性》)
二指作品的气势、格调,如“精理为文,秀气成采”。(《征圣》)
三指气象、气貌,如“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物色》)
《神思》篇中所谓的“志气”,与上引诸义不同。当代龙学家们对它做了多种解释:
一曰“所谓‘志气’,是指作家的世界观而言。”〔4〕
二曰“‘志气可解释作情志与气质,在这里泛指思想感情。 ”〔5〕
三曰“志气”指“意志力量”,说:“精神居住在胸中,能聚能散,其关键在于意志力量的统辖。”〔6〕
四曰“志气”是一种“精神状态”,说:“作家运用想象,能否周游天地,贯穿古今,全在于作家主观精神在构思时的由政治地位、社会关系、生活处境所造成的强弱低昂的状态。”〔7〕
世界观对于文学创作,特别是对作品的思想倾向,起着决定性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掌握文思开塞的“关键”。创作实践表明,世界观先进者,未必都“天机骏利”;世界观落后乃至反动者也未必都“六情底滞”。
作者的气质、情志、思想感情,也影响、制约着创作,主要表现为倾向的表达和风格基调的形成,但它却也控制不了文思开塞的“关键”。心理学著作中,一般把人们的气质分为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抑郁质四种类型。试想,哪一种气质的作者,文思易开或文思易塞呢?这显然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写作作为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当然需要意志力量发挥作用,但只有坚强意志而不具备其他写作条件的人,也不会常常“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反之,一个意志脆弱的人,在写作实践中,也并不见得没有一点“忽撞天机”、“文思泉涌”的情况。
比较而言,把“志气”释为一种精神状态,似乎更为符合刘勰所论之旨。这从“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在《神思》篇中的地位、上下文之关系,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
“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的上文是“思理为妙,神与物游”,这可以说是“志气统其关键”的前提,因为只有在“神”与“物”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文思,进一步才有“开”与“塞”的问题。“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的下文,则是在与“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对举之后,旋即用表示因果关系的“是以”二字连接,转入《神思》篇中至关重要的一段:
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
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在这段话中,显然地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在临文、构思之时,要进入虚静状态,使心腑清明澄澈,无杂念萦怀,亦无外力干扰,养成一种积极、专注的精神,轻松自如地致力于写作构思,如《正义》所云:“精义入神,是先静也;以致用,是后动也;是动因静而来也。”〔8 〕二是为文用思,要有“积学”、“酌理”、“研阅”、“驯致”等诸多方面的修养,即后人所谓的“养其根而俟其实”的“根本功夫”。这种“根本功夫”是在作者特定的生活境域中,日积月累,长期涵养而成的,是文思得以广泛展开的基础。如上所述,既然临文时的虚静状态和长期的“根本功夫”的修养,都是由于“志气统其关键”而来,那么“志气”的内涵,也就可以推想了。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因为“志气”统辖着文思开塞的“关键”,所以要求得“文思常利之术”,一须“虚静”,二须涵养,这样来理解“志气”二字的具体内涵,或许就扎实一点了。
《神思》篇中还有一句话不可忽视,即“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意思是说,刚刚提笔写作之时,信心和勇气很大,欲望和激情也很强烈,但文章写成之后,只剩下原来心想的一半了。这样解释“气倍辞前”的“气”,就使刘勰为求得文思常利之术,而阐发的“养气”说,有了更为具体的内容。联系《养气》篇中“贾余于文勇”的句意,把“气”释为勇气和信心,则又有了一个力证。
综合《神思》、《养气》两篇所论,大致上可以说,刘勰所谓的“养气”,实质上即是培养、孕育“志气”;而这种对文思开塞起着“关键”作用的“志气”,则是以作者才学识力诸多方面的修养为基础的、在写作构思过程中由体力和精力、心境和情绪、欲望和激情、勇气和信心等多种因素所形成的一种精神状态。以此验之于古今创作实践,大抵是有据可依,信而不爽的。
当然,在“文变殊术”的写作实践中,不同作者有着不同的构思习惯和构思方式,主“虚静”者有,主“迷狂”者亦有,倡“从容率情”者有,倡“苦吟”者亦有。全面地看刘勰及其同道所论似乎有点顾此失彼了。但就他们各自的体验而言,却是理据统一,符合实际的。如果用我们今天所持的观点来阐释,构思中的“迷狂”和“苦吟”,又何尝不是一种精神状态呢?
二
在刘勰之前,晋人陆机的《文赋》,曾形象地描述过写作构思时有开塞的状貌和感受,但他未能明白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的道理,只能“抚空怀而自惋”,发出“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的喟叹。从刘勰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对陆机及其著作的评价来看,刘勰的“养气”之说,实际上是对陆机的疑问所作的一种“妙识文理”的回答。它不仅界定了“养气”的具体内涵,而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明了“养气”的意义和方法。这在我国文学批评史和写作理论史上,具有发轫之功。
首先,刘勰认为“养气”是作者进入写作过程,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如前所述,刘勰所谓的“养气”,包括着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临文时的精神状态;二是长期的才学识诸方面的修养。他在概要阐述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之后,紧接着说:“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显然是说,只有在才学识多方面修养的基础上,于临文时养成良好的精神状态之后,才能使“玄解之宰”定墨;“独照之匠”运斤,真正进入写作过程。为了表示强调,刘勰旗帜鲜明地提出:这就是驾驭、支配文思顺利进行的首要方法;这就是布局谋篇、制胜文苑的最重要的开端。把“养气”在写作实践中的意义,提高到这般程度,可以说是史无先例的。
刘勰既重视临文时的良好精神状态的培养,又突出才学识等诸多方面修养的意义。他主张“学业在勤”,赞赏“锥骨自厉”的学习精神,认为从事写作,必须具有广博的学识和见解。他在提出写作构思快慢不同的情况之后,又进一步说,写作构思“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在刘勰看来,写作构思无论是快是慢,是难是易,都要依靠学识的广博,才能的练达。学识浅陋,写得慢也没有意义;才智粗疏,写得快也是徒然。以“才疏”和“学浅”而取得成就的人,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把作者的才学识修养与写作构思直接联系了起来,从根本上阐明了解决文思开塞问题的要义。刘勰说:“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这里所谓的“博见”,可以理解为学识;这里所谓的“贯一”,则可以理解为综合概括的能力,两者结合起来即可有助于解决写作构思过程中经常出现的“苦贫”和“伤乱”问题。联系古今中外的写作实践加以验证,“博而能一”这一言简意赅的理性概括,是极其富有指导意义的。
其次,刘勰认为“养气”可以导致文思的畅通,乃至灵感的迸发。《神思》篇指出,在写作构思过程中,“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其意谓写作构思过程中,思、意、言三者之间,衔接紧密,则文思畅达;关系疏远,则文思滞塞,而且往往有近在眼前而求之于四海之外的情况。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刘勰指出:“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的主张。及至《养气》篇,刘勰对此意又有了新的补充和发挥,他一再指出:
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
之数也。
志于文也,则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若销铄精
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岂圣贤之素心, 会文之
直理哉。
刘勰的意图非常明确:一方面,他反对在写作构思过程中“钻砺过分”、“销铄精胆”;另一方面,他主张为文用思要“率志委和”、“优柔适会”。前者会使人“神疲而气衰”,不可能再进行正常的写作构思;后者则会导致“理融而情畅”,使写作构思达到左右逢源、酣畅淋漓的境地。
所谓“率志委和”,是指在写作构思过程中,顺应作者的心情,从容不迫、恬静自然的一种精神状态;所谓“优柔适会”,则是指悠然宽舒地适应写作构思的具体情况;等待、创造文思畅达的时机、运会,这两者都是在虚静之中,经过“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清和其心,调畅其气”得来的。归根结蒂,都是养气的结果。
在刘勰看来,“率志委和”了,“优柔适会”了,情理即会合了,文思即畅达了,“藏若景灭,行犹响起”的灵感,也就可能倏然而至了,这正如“水停以鉴,火静而朗”的道理一样。对此,他在《总术》篇中是这样论述的:
若夫善弈之文,则数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
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
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断章之功,
于斯盛矣。
这段话主要是讲“执术驭篇”,即掌握了写作之术再进行写作的情况,虽非专论“养气”之功,但由于刘勰视“养气”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因而就使它与“养气”有了直接的联系。在这段话中,所谓“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是说善于写作的作者,能够掌握写作的规律性,有条有理,按部就班,等待着“情会”,亦即灵感的到来,顺应着有利的时机,遵循着正常的原则,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充分发挥出为文之术的技巧和作用,这显然与“率志委和”、“优柔适会”之意是息息相通的,可以互为补充的,至于“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等句,说的则是文思畅达,灵感迸发后的表现和结果,有力地补充、印证了“养气”能够导致灵感发挥作用的深刻内涵。
第三,刘勰认为“养气”可以破除写作构思过程中的滞塞和阻隔。“思有利钝,时有通塞”,在写作中,碰到滞塞不通的情况怎么办?刘勰除了提出“吐纳文艺,务在节宣”的一般要求外,还具体地指出:“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主张在心境不好、情绪烦乱的时候,就不要勉强地再往下写,暂时放一放,勿使思路堵塞不通。有了兴致,得心应手了,那就展开胸怀,任意抒写;思理杂乱,难以为继,那就放下笔掩怀休息。在逍遥自在,怡然自得之中,消除疲劳和怠倦;在闲暇之余,培养为文的勇气,磨砺才思的锋芒。这样做,就会使文思“刃发如新,凑理无滞”,顺利进行下去。从写作实践来看,古往今来,均不乏其例,刘勰视之为“卫气之一方”,也是“盖有征矣”的。
上述几点,均从写作主体方面着眼,阐述“养气”的方法和意义。如果联系当时文坛的实际,那刘勰“养气”说的旨归和价值,就更为重大而深远。从根本上说,它是为矫正“去圣久远”、“离本弥甚”的诡滥文风而发的。
三
多年来,在龙学研究中,刘勰的“养气”说,似乎是一个被冷落、被忽视的课题。据专家统计,从1907年至1985年的70余年间,公开发表的研究“养气”篇的专题论文只有三篇;对《神思》篇的专题研究虽然相当多,在此期间公开发表了70余篇论文,但大都着重于创作构思中的联想和想象,而较少专论对文思开塞起着关键作用的“志气”。这或许正为后人的探求,留下了一份珍贵待采的宝藏。
追溯一下刘勰“养气”说的历史发展过程,以致于现代科学研究的状况,它是上有本依,下有影响的。在浩瀚的典籍和丰富多采的实践中,都可以为刘勰的“养气”说找到笃实的根据,印证他的观点、主张,绝非面壁“虚造”。
先于刘勰的许多哲人、贤士,儒、道、佛诸家都曾论及“气”的内涵、作用和养气的方法。《礼记·大学》中说:“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庄子·刻意篇》中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形不亏”;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则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样一些论断,以及本文前面提及的孟子、王充、曹丕等人的有关说法,虽与刘勰的“养气”说具有不同的对象范围和具体内涵,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相互沟通的。至若佛家的禅定之法,对于在广有影响的定林寺修经十余年的刘勰来说,则必然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这就在实际上使刘勰的“养气”说,有了深厚的哲学基础。而从为文之主体方面讲,刘勰的“养气”说,则是他在兼融儒、道、佛各家观念之后,所形成的“自然之道”,亦即他的任自然观,在论及文思开塞时的反映和表现,范文澜先生谓:“彦和论文以循自然为原则”,这是深得刘勰本意的。
刘勰之后,“养气”说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文坛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历代文家渐次把“养气”的内容与写作实践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成为我国传统写作理论中品位很高的一项研究内容,并在写作实践中发挥着导引作用。一方面,唐朝韩愈、宋朝苏辙、清朝刘大櫆等人,上承孟子养气之说,发展而为文章之中所表现出来的气势,即所谓“文气”,此说与文思开塞关系不密,因置勿论;另一方面,更多的文家则直接继承刘勰的养气说,对影响着文思开塞的“气”,做了具体阐发。如唐朝到中国来留学的日本僧人遍照金刚在其名著《文镜秘府论·论体》中曾说:
“心或蔽通,思时钝利,来不可遏,去不可留。若又情性烦劳,
事由寂寞,强自催逼,徒成辛苦。不若韬翰屏笔,以须后图,待心
虑更澄,方事连缉。非止作文之至术,抑亦养生之大方耳。”在《论文意》中,他又说:“意欲作文,乘兴便作,若似烦即止,无令心倦。常如此运之,即兴无休歇,神终不疲。”〔9 〕把上引两段话与刘勰在《养气》篇中所论,对照起来,我们只能说是异曲同工,何其相似乃尔了。
到了宋朝,苏轼以诗言虚静、养气对创作构思的意义:“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10〕他把“虚静”视为作者感物、通物、获得佳作的前提,这与刘勰之“养气”说,也是神理契合的。此后,清代著名戏剧作家和理论家李渔,亦与刘勰同调,他在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切身感受写成的《闲情偶记·词曲部》中说:“开手笔机飞舞,墨势淋漓,有自由自得之妙,则把握在手,破竹之势已成,不忧此后不成完璧。”这说的是文思通畅顺利的时候;而如果思路不畅,“文情艰涩,勉强支吾”,他也主张“不如不作之为愈”。他说:“如入手艰涩,姑置勿填,以避劳苦之势,自寻乐境,养动生机,俟襟怀略展之后,仍复拈毫,有兴即填,否则又置。如是者四,未有不忽撞天机者。”显然,这与刘勰所谓的“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是一脉相承的。近代学者吴曾祺也反对那种“神气沮丧,情绪不属”、“搔头抓耳,尘垢满爪”、“姑以成篇为事”的苦思冥想,主张作文要“适机”。他指出:“行文有机。机之来如木之生春,水之赴壑,皆有自然而然之妙。固有一题到手,经营累日,而不得一字者,机未至也。此时,且不必遽著思想,姑取平日所喜文字,读之数十遍,胸中便有勃然不可遏抑之候”;“然又必方寸之间,空灵四照,故能机来而与之应,此则刘彦和所谓‘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盖不虚不静,则如一物横亘于中,而理之在外者,无自而入,意之在内者,无自而出。关键不通,皆足为机之害。”〔11〕在这里,吴曾祺所谓的“适机”之“机”,与李渔所谓的“养动生机”、“忽撞天机”之“机”,事实上,都已涉及到了构思过程中的灵感、兴会现象,它虽并不是文思通畅顺利的全部内容,却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种表现。他们共同认为,灵感、兴会之来,与在“虚静”状态下的“养气”,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他们都主张在“机”之未至之时,“姑置勿填”,“不必遽著思想”,而要“自寻乐境”,以“俟襟怀略展”,产生“勃然不可遏抑之候”,否则,即将“关键不通”,而“为机之害”。应当说,这与刘勰所论,是如影之随形,实为一体的。
及至现代,“养气”说的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低谷”,但仍有一些学者、作家从自己的治学和创作实践中,总结出了十分可贵的经验,为传统的“养气”说,补充了新的内容。如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论及自己的写作体验时,曾非常生动地说:“思路有畅通时,也有蔽塞时,大约要思路畅通,须是精力弥满,脑筋清醒,再加上风日清和,窗明几净,临时没有外扰败兴,杂念萦怀。这时候静坐凝思,新意自会象泉水涌现,一新意酿成另一新意;如是辗转生发,写作便成为人生一件最大的乐事。一般‘兴会淋漓’的文章大半都是如此做成。”〔12〕著名作家王蒙也曾说:“写的时候不妨尽量放松一点,放松了,思维和内心的活动才能充分活跃、不受阻碍地进行……放松了,就不会别别扭扭、疙疙瘩瘩的。”他还说:“苦思冥想,惨淡经营,憋了半天,硬是憋不出来的情形也是会有的。但我认为,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放一放,有意识地培养培养创作的情绪再写。”〔13〕
综上所述,可以明显地看出,古今文家,对“养气”说,对文思开塞之所由,都是有共识的,它是久经验证,颠扑不破,极有生命力的。但他们又都未能对“虚静”、“养气”、“灵感”、“运会”等等在创作实践中屡屡有所感悟的现象,做出科学的、系统的阐述;特别是未能论证“虚静”、“养气”,何以能导致文思畅通乃至灵感迸发、运会骤至的原由,甚至消极地主张“且去静坐”,忽视了客观需求和为文主体的能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总结他们的实践经验,吸纳他们的研究成果,弥补他们的缺陷,纠正他们的误解,使肇始于刘勰的为文“养气”之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较为完善的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特点的理论定势,不是很有意义的吗?
从发展上看,随着现代生理学、心理学、气功学以及思维科学研究的深化,刘勰及其同道者们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所不可能认识,不可能做出科学解释的奥秘,正在不断地被破译。传统的“虚静”、“养气”之说,已被许多中外科学家用于治病、强身、健脑、益智。如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外科医生柏涅·赛戈尔发现:“沉思默想乃是松驰思想的一种特殊运动,这种运动能够治疗和预防多种重病。”〔14〕
近几年,国外还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开发人体智能的“超觉静坐技术”。其方法是按一定要求闭目凝神静坐,使人由兴奋思维状态转为平静并进而达到超觉状态,即“入定”或“忘我”状态。凡受过此项训练的人,都感到头脑清晰,耳聪目明,精力充沛,心平气和,记忆力增强。
在日本,川烟爱义博士花了半个世纪的岁月进行健脑研究,他的重要方法,就是“三分钟超觉静思”。这种种情况,都为传统的“养气”说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新的论据。
目前,气功科学的研究也已渐渐深入到了各种学科,并直接地和文学创作构思联系起来,标志着“养气”说的研究,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领域。综合现代心理、生理、思维、气功科学的新成果,用之于“养气”说的研究,必将使我国这一古老而又珍贵的学术瑰宝,发出更为明丽的光彩。
注释:
〔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1962年9月版, 第204页。
〔2〕《孟子·公孙丑上》
〔3〕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版, 第254页。
〔4〕马宏山:《文心雕龙散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71页。
〔5〕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10月版,第104页。
〔6〕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漓江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249页。
〔7〕陈思苓:《文心雕龙臆论》,巴蜀书社,1988年6月版, 第69页。
〔8〕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第496页。
〔9〕[日]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年版,第138、153页。
〔10〕苏轼《送参寥》,转引自周振甫、冀勤《钱钟书〈谈艺录〉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11页。
〔11〕转引自周亦才《涵芬楼文谈选注》,求实出版社,1987 年9月版,第59页。
〔12〕《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286页。
〔13〕王蒙:《漫话小说创作·谈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28页。
〔14〕香港《大公报》,1992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