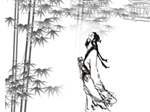|
-
方幼安诊余漫笔 方幼安
临诊之余,偶有一得之体会,漫笔随记,不成篇幅,谨以就正高明。
一、强间、脑户三穴之组合使用
上述三穴均属督脉,脑户穴在文献中曾有禁针灸之记载,但多年来予以三穴组合使用,用以治疗精神、神经症状,收到一定效益。
予曾用百会、强间、脑户等三穴(以下暂名“头三针”)治疗大量老年性动脉硬化型痴呆,不少于200例,绝大部分患者经针刺一段时间后,其痴呆症状均有明显改善。如病程不太久,症状不太严重者,仅需一二十次治疗,即可看到改变,面部表情较针前明显活跃,反应明显增快。
又曾用“头三针”治疗大量小儿脑病,包括脑发育不全和脑炎后遗症,亦不少于200例,亦绝大部分经针刺一段时间后,其智力均有不同程度好转。
又曾用“头三针”治疗癫痫数十例。有些病例是在用抗癫痫药后仍频繁发作的基础上加针“头三针”后,发作次数明显减少,程度减轻。有些病例是在针刺药物同用见效后,逐渐撤药,直至撤净,完全使用针刺,并最终亦停止针刺,随访较长时间,未见复发的。
又曾用“头三针”治疗小舞蹈病及扭曲痉挛10余例,针刺后症状明显减轻,直到完全正常。
又曾用“头三针”治疗神经官能症、抑郁症、强迫症、失眠症,均有效。
以下记载数例。
一例为60岁老妇人,患头痛昏眩多年,如周围环境稍有喧闹,或略事劳动,即要发作,如加重其诱因,发作更为严重。发作时,左眼区从眉毛以上直到眼下孔周围,必定出现明显浮肿,而右侧眼区始终正常。当头部昏胀疼痛消失后,其左眼区局部浮肿亦随之消失。予为之针百会、风池、攒竹、太冲等穴,每次针后,其痛立止,其肿亦消,但始终不能根治,如是者已1年之久。嗣后,予在原处方基础上,加针强间、脑户两穴,仅1次,不仅头痛发作明显减少,尤以眼肿之证,即不再出现,再继续一段时间作巩固治疗,诸恙全消。从这一例观察:单针百会一穴与“头三针”同针,效果大不一样。
一例为5岁男童,患脑发育不全后遗症,其症甚轻,仅左下肢轻度跛行,膝关节过伸,既无内翻,又无外翻,经取穴,髀关、伏兔、阳陵泉、委中等穴,治疗l个月12次后,有所好转。某日,家长偶然补诉,患儿在行走时,有一个“一抖一抖地动作”,患儿不能自止,呵禁亦不止。这一现象由来已久,并非症状好转后出现。予乃试在头部加针“头三针”仅两次后,家长反映,这一“一抖一抖地动作”即不复存在。
一例为20岁男青年从广东来就诊,周身扭曲痉挛,伴不能正常讲话,严重构音不清,头部不停顿地左右扭曲,两上肢不停顿地大幅度上下前后挥舞扭动,身躯摇摇晃晃不停顿地前后左右扭动,两下肢步履不稳。独立行走困难,需要他人在旁搀扶维护。初诊时在冬季,由于周身不停扭曲,故大汗淋漓。病程已经3年,神经科投以各种镇静剂无效而来针灸。予以为周身扭曲痉挛,可不必在肢体取穴,应平衡其督脉,试为针“头三针”,第三次后开始见效,继续针刺,逐步好转,在沪共治疗3个月,头部、躯干及四肢扭曲,均能较好控制,能讲:“方医生再见,谢谢”等简单语句。患者在针灸开始时,因原用药物效果不显,故家属自动停药,除用“头三针”外,未针刺其它穴位。针刺3个月离沪时已明显好转。
与上一例扭曲痉挛基本相同又一例为5岁男童,亦来自广东,亦取“头三针”,未用它穴,未服用药物(因原药无效停服),治疗3个月,基本好转回原地。
又一例为女性青年,30岁,未婚。五年前因琐事自感秀属,情志抑郁不欢,深自苦恼而不能自释。曾就医于精神病院,用镇静剂后益增其精神恍惚,心中闷郁,甚至喃喃自语,就诊于予。证见形体丰腴,表情呆滞,两目迟钝,初不自诉症情,一旦说起后,即滔滔不绝,但多话不对题,虽非答非所问,但亦离谱甚多。诉说主症为自觉头顶有物重压,心中抑郁寡欢,思想不能集中,看书看不下,夜晚失眠等症。予亦为之取“头三针”,留针20分钟,出针时,患者自诉头顶重压之物若失,心中豁然开朗,为几年来所未有。隔日复诊,告针后当晚能安睡,诸症俱见减轻。仍续针“头三针”,未用它穴,每周2次,如此经半治疗,患者判若两人,不仅主诉全消,且精神饱满,说话条理,恢复病前状态。
又一例为75岁老妇人,患左侧偏瘫3个月,以往有高血压史多年,眼底动脉硬化,脑部CT片示:多个缺血性小病灶。除右侧肢体偏瘫症状外,神情明显呆板,目光呆滞,问之不答。予除针刺头针相应运动区外,加针“头三针”,针刺5次后,除肢体运动好转外,面部表情明显活跃,主动讲话。继续针刺,继续好转,与此同类中风患者,例数甚多,加针“头三针”后,精神状态均有明显好转,但对脑萎缩之病人,疗效尚不明显。予从大量临床实践中发现,“头三针”对精神、神经症状,确有不可思议之疗效,与仅针刺百会或仅针刺脑户,有截然不同之后果,与百会加四神聪亦有不同之后果,予已从大量实践中获得确认。“头三针”除仅知“督脉入脑”之朴素说法外,其机理究在何处,尚待于进一步研究。
“头三针”之操作法为循督脉向后,浅针卧刺,成人进针3-4厘米,小儿酌减。
二、“后太阳”穴之发现
经外奇穴太阳,为治头痛之经验穴,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另一定位,优于常用定位,位置在丝竹空穴水平向后移至鬓发际,由于位置在太阳穴之后,故暂名“后太阳”。我之所以发现此穴,因感头痛时,其痛点基本上均在“后太阳”穴区,故开始试在痛处针刺,竟发现镇痛效果甚好,大大优于太阳穴。其进针操作法为浅刺卧针,向鬓发内以水平方向进针4厘米左右,小幅度捻转,留针30-60分钟,两侧两针。
此外,予曾多次遇到少年妇女在行经期头痛,同时发现此类患者在第3颈椎棘突有隆起压痛,取后太阳加颈3压痛点有明显效果,其颈3隆起压痛与行经期头痛成正比关系,通过上述方法治疗,当隆起压痛消失后,其行经期头痛亦随之消失,屡试屡验。
三、神道穴之新体会
予在临床曾发现有众多自诉胸闷之患者,感到胸部压紧不适,深呼吸后方稍可缓解片刻,一如心血管病缺氧之症状,故多数自己怀疑心脏疾患而求医,但经心电图或更新仪器之检查,均属阴性。予发现此类患者在督脉神道穴均有隆起压痛,有时望诊即可确认。在神道穴针刺并温针,有明显效果。一经针刺,患者自感一如雨过天晴,阴霾消散,胸中顿感舒畅。经治疗几次后,其胸闷之症状,将会随神道穴之肿痛,同步消失。屡试不爽,确有良效。
四、风池穴进针方向之体会
风池穴属少阳经,根据文献记载,可平肝熄风,兼治目疾。
予在实践中发现,由于进针方向之不同,针刺感传将随之各异,所获效果亦不相同。换言之、即是对不同的适应,要达到不同的治疗效果,必需要采用不同的进针方向。如治目疾,如何验证是否达到治疗之要求,则需要通过“气至病所”的客观反映,方能获得验证。
予在取风池穴治肝胆诸疾,或驱泄风邪时,其进针方向为对准对侧直视瞳孔,进针后小幅度捻转,针感在局部。如治目疾,必需要紧靠枕骨下方,斜方肌起始部之外侧取穴进针、如偏离穴位即不可能得到预期针感,针尖必需对准同侧直视瞳孔,进针深度要达到4-5厘米。操作手法必需在达到规定深度后用小幅度反复捻转,针感可循足少阳经分布路线渐渐上行,通过顶部侧面,渐渐到达额部阳白穴或眼区。有些患者会感到眼内有冲击感,偶有患者在第一次针刺时针感不一定到达眼区,但继续针两次后,多数能达到。医者在操作时,如患者尚未感到针感上行,切勿操之过急加大其捻转幅度,如此会造成针感过强,后遗不适,应耐心操作,必有收获,这一操作法,大大有利于治疗各种眼疾。
五、天柱、天鼎穴之新体会
天柱穴属足太阳膀胱经,天鼎穴属手阳明大肠经,古今针灸书籍未载天柱能治腰痛与天鼎能治肩痛,但予发现此两穴分别可治腰痛、肩痛,并经长期实践观察,证实确有显著疗效。予发现天柱可治腰痛之经过,为在50年代末为治一右侧腰痛患者,他3天俯仰活动不利,无扭伤史及受风寒史,脉舌正常,经外敷药物及理疗未效。经予检视:脊椎居中,未见侧突后突,两侧腰肌未见强直,直腿抬举阴性,“4”字试验阴性。予试循足太阳经筋所过,从腰上行至颈部循序按压,发现足太阳经筋“其直者结于枕骨”之经筋处,即现代医学解剖部位斜方肌之起始部明显隆起,高于对侧,兼明显压痛,此处正是天柱穴。予乃在该穴试刺一针,捻转得气,行针约半分钟,并嘱患者逐渐活动其腰部,仅1-2分钟,其痛明显减轻,活动大见好转,留针10分钟,中间行针一次,出针时腰痛若失,活动恢复正常,同时天柱穴之压痛亦消失,隆起平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