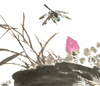摘要:“说”祭是一种以论说的方式说服神灵满足祭祷者诉求的言语行为,“说”祭祝辞因其特定的情境、内涵与形态而固定为格套,具有鲜明的文体属性,经过祝史的书面化处理与篇章化撰作,便生成祭祷性说体。诸子论说本质上跟祝史“说”祭一样,都是“陈论其事”的言语行为,以犀利的言辞陈述并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诸子论说在方法与策略、思维与逻辑等方面受祭祷性说体的影响,于是形成议论性说体。诸子论辩时先简要表明观点,再详细加以阐述,于是形成经说体。晚周时期,诸子称自家学说为“经说”而贬斥他家学说为“小说”。两汉后,目录学家借用“小说”一词,泛指所有不本于经典的论著,于是又形成了传统的小说体。
关键词:六祈;说祭;祷辞;说体;小说
作者:刘晓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上海 200241)。
“说”是中国古代重要且复杂的文体形式。周秦两汉时期,存在大量以“说”名篇的文献和以“说”命籍的文献集成,如《赵良说商君》《庄子·说剑》《墨子·经说》《韩非子·说林》《说苑》等。《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也收录不少解说儒家经典的“说”类文献,如《齐说》(说《论语》),《长孔氏说》(说《孝经》);“诸子略”更是专设“小说家”类,收录《伊尹说》《鬻子说》等九流之外的“小说”。清人姚鼐《古文辞类纂》将天下文章分为十三类,其中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辞赋六类都包含不同类型的“说”体,可谓众“说”纷纭。一般认为,说体起源于战国时期诸子的论辩与游谈。然而大量文献表明,商周时期即已存在一种祭祷神灵的说体,这种文体对诸子论说有着直接影响。从诸子的论说中,又蘖生出经说与小说两种对应而生的说体。围绕与“说”体相关的若干问题,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出土文献为主,结合传世文献,从古代礼仪制度入手,追溯说体的渊源,并探讨其流变。

“说”体溯源:作为仪礼的“说”祭
“说”祭乃先民祭祷天神地祇人鬼时的仪礼。《国语·楚语下》记左史倚相“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博物志·史补》记子路与子贡过郑神社,“社树有鸟,子路搏鸟,社神牵挛子路,子贡说之,乃止”。倚相说于鬼神与子贡说于社神,都是指向神灵行“说”祭之礼,以求祛病禳灾。
“说”祭之名见于《周礼》。《周礼·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类,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说。”郑玄注云:
祈,嘄也,谓为有灾变,号呼告神以求福。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则六疠作见,故以祈礼同之。……郑司农云:“类、造、禬、禜、攻、说,皆祭名也。”……玄谓类造,加诚肃,求如志;禬禜,告之以时有灾变也;攻说,则以辞责之。禜,如日食以朱丝萦社,攻如其鸣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瀸灭无光,奈何以阴侵阳,以卑侵尊?”是之谓说也。禬,未闻焉。造、类、禬、禜皆有牲,攻、说用币而已。
六祈包括类、造、禬、禜、攻、说六种祭礼,是为了禳灾祈福而向神灵举行的祭祷仪式。孙诒让云:“'掌六祈以同鬼神示者’,谓内外常祭之外,别有此祈祷告祭之事,其别凡六也。……祈祷必特为祝辞,与常祭不同,故此官职之。……《说文》'示部’云:'祈,求福也。’'口部’云:'嘄,声嘄嘄也。’《汉书·息夫躬传》颜注云:'嘄,古叫字。’《尔雅·释言》云:'祈,叫也。’《一切经音义》引孙炎注云:'祈,为民求福,叫告之辞也。’郭注云:'祈,祭者叫呼而请事。’”可知六祈之“祈”,实际上是巫祝向神灵呼告以求福佑的言语行为,伴随这种行为产生的,是具有特定含义与形式的祝辞。《周礼·春官·大祝》:“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孙诒让云:“先郑后注云:'辞谓辞命也。’凡祈祭告神之辞命,有此六者。辞者,词之叚。”
“说”祭之礼,在先秦卜筮祭祷简中多有记录。包山二号墓楚竹简记载了贞人盐吉为左尹邵佗占卜并举行“说”祭的一次经过:
宋客盛公边聘于楚之岁,荆夷之月,乙未之日,盐吉以保家为左尹佗贞:自荆夷之月以庚荆夷之月,出入事王,尽卒岁。躬身尚毋有咎。占之,恒贞吉,少有忧于躬身,且志事少迟得。以其故敓之,囟攻解于人禹。占之当吉,期中有喜。(简198)
“宋客盛公边聘于楚之岁”是一种以事系年的纪年方式,“之岁”前的内容即该年发生的大事,《左传》“昭公七年”有“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盐吉”是巫祝,为职业贞人,多次见于包山楚墓竹简。“保家”读如苞蓍,草名,指贞卜用具。“佗”即邵佗,楚怀王时任左尹,是墓主。“贞”即卜问,此处指筮占。“躬”亦即“身”。“志事”即仕途之事。“咎”即灾难。“敓”与“说”通,即《周礼·大祝》“六祈”之“说”。“囟”借作“鬼”,《广雅·释天》:“鬼,祭先祖也。”“攻”即“六祈”之“攻”。“鬼攻”即祭祀先祖及鬼神。“人禹”可能指去世的祖先。
这是一则结构完整的卜筮祭祷记录。自“宋客盛公边”至“左尹佗贞”为前辞,记录举行卜筮祭祷的时间、巫祝名、卜筮用具和请求贞问者的姓名;自“自荆夷之月”至“尚毋有咎”为命辞,记录贞问事由:邵佗出入宫廷侍王是否顺利、爵位何时到来、疾病吉凶如何;“占之”一句为占辞,是根据卜筮结果所作的判断:“恒贞吉”,即长期来看是吉兆,“少有忧于躬身,且志事少迟得”,即近期身体有微恙,爵位不能速得;“以其故说之”一句为祷辞,又称说辞,是为了解除忧患而向神灵举行的祈祷;“占之当吉”一句为第二次占辞,即在“说”祭之后,根据神灵指示所作的最后判断。“前辞”“命辞”与“占辞”属于卜筮的内容。“祷辞”属于祭祷的内容,这正是“说”祭的记录。“故”训为“事”,“其故”指占辞所言之事。“说”指行“说”祭之礼,“以其故说之”指祭祷者因占辞所言忧患之事而向神灵行“说”祭之礼,祈求神灵福佑。“攻”即责让,“鬼攻解于人禹”指责让死去的先人,以便解除忧患。
有关“说”祭的记录在卜筮祭祷简中比比皆是,“以其故说之”俨然已成卜筮祭祷仪程中的格套。试举数例:
望山楚简:
□志事,以其故敓之,享归佩玉一环柬大王,举祷宫行一白犬,酒食。(简28)
□无大咎,疾迟瘥,有祟,以其故敓之,赛祷。(简63)
葛陵楚简:
□以其故敓之。举祷楚先:老僮、祝融、鬻熊各两牂。(甲三188)
以其故敓之,赛祷北方□。(乙三61)
秦家嘴楚简:
占之吉。有祟,以其故敓之。(M13·2)
占之恒贞吉,少有慽于宫室,以其故敓之。(M13·14);

事实上,除了卜筮祭祷,“说”祭还见于朝政治理与日常生活。当国家遭遇灾难或有不祥之兆时,君臣大多会举行“说”祭以禳灾祈福。上博简《竞建内之》记载齐桓公问日食的征象,鲍叔牙回答将引发天灾。桓公便提出举行“说”祭以祓除灾难:“……坴,隰朋与鲍叔牙从,日既,公问二大夫:'日之食也,害为?’……鲍叔牙答曰:'害将来,将有兵,有忧于躬身。’公曰:'然则可敓与?’隰朋答曰:'公身为亡道,不践于善,敓之,可乎?’”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婚嫁、丧葬、农作、出行等也会行“说”祭之礼。如《九店楚简》“日书”:“亥、子、丑……无为而可,名之曰死日。生子,男不寿。逃人不得。利以说、盟、诅”;《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除篇”:“害日,利以除凶厉,说不祥。祭门、行,吉”(五正贰)。
周秦时期,“说”祭已广泛流行,成为人们沟通鬼神、禳灾祈福的重要途径。那么作为仪礼,“说”祭的独特性是什么?这对我们考察“说”体起源至关重要。由于文献不足,汉儒解说“六祈”要么存有阙疑,如云“禬,未闻焉”;要么语焉不详,如释“类造”为“加诚肃,求如志”;要么与史实不符,如云“攻、说用币而已”,然据前引楚简可知,“说”不仅用币,还用牲、帛等。郑玄将“攻”“说”连解,云“攻说,则以辞责之”,这显然不符《周礼》原义——五曰攻,六曰说——如果“攻”“说”无别,那么“六祈”分类就没有意义。清儒注经,于“六祈”也没有太多发明。孙诒让对“攻”“说”的阐释,基本上承续了汉儒的观点:“云'攻说则以辞责之’者,《论衡·顺鼓篇》云:'攻,责让之也。’《广雅·释诂》云:'说,论也。’谓陈论其事以责之,其礼尤杀也。”孙氏对“攻”“说”的解释没有问题,但他为了附会郑玄又将“攻”“说”的含义合二为一,仍然泯灭了“攻”“说”的区别。李学勤先生指出,“'说’是告神的祝词,只'陈论其事’,没有责让的意思。郑玄把说和攻混为一谈,是不妥当的。攻则确是责让,《论衡·顺鼓》所述甚详”。李先生所论独具只眼,这里不妨略作申论。尽管六祈皆为“号呼告神以求福”的言语行为,但在“号呼”的过程中,应当还伴随着其他行为方式,这正是区辨六祈的重要依据。由于文献不足,“类”“造”“禬”的具体情形已不得而知,但“禜”“攻”“说”三者还是约略可以区分。“禜”祭大都使用绳索,“朱丝”往往是“禜”祭的标配。《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侯伐齐,将济河。献子以朱丝系玉二瑴,而祷曰:'齐环怙恃其险,负其众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唯尔有神裁之!’沉玉而济。” “ 攻”祭一般伴随鸣鼓。《春秋繁露》:“大旱雩祭而请雨,大水鸣鼓而攻社。”与“禜”“攻”皆有附加动作不同,“说”祭是一种纯粹的言语行为,其独特性在于言说的内容与方式。《释名·释言语》:“说,述也,宣述人意也。”《 广雅·释诂》:“说,论也。” “ 说”之要义,就在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将祭祷者面临的灾难与困境告诉神灵,祈求解除忧患,给予福佑。郑玄举董仲舒《救日食祝》为“说”例,这没问题。只是古人救日食时除了祝祷,还要鸣鼓,于是“说”与“攻”又有了关联。历代经师将“攻”“说”连解,原因或即在此。《左传·庄公二十五年》:“凡天灾,有币无牲。祈请而已,不用牲也。非日月之眚不鼓。”孔颖达疏云:“《周礼·大仆职》云:'凡军旅、田役、赞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是日食、月食皆有鼓也。”实际上,由于祭祷仪式的复杂性,一场祭祷活动往往会综合多种祭礼。《博物志》卷五:“《止雨祝》曰:'天生五谷,以养人民。今天雨不止,用伤五谷。如何?如何?灵而不幸杀牲,以赛神灵。’雨则不止,鸣鼓攻之,朱丝绳萦而胁之。”这场为“止雨”而行的祭祷中,“天生五谷”至“以赛神灵”为“说”祭,祭祷者向神灵诉说淫雨给生民带来的灾难,祈求神灵止雨。祭祷者允诺神灵,止雨后将杀牲赛祷神灵。“雨则不止”以后,指“说”祭失效,祭祷者采取后续行动,“鸣鼓攻之”为“攻”祭,“朱丝绳萦而胁之”为“禜”祭。由于祭祷的最终目的是说服神灵祓除忧患,因此有论者将此类禳灾祈福的祭祀活动统称为“说”,这样“说”又由专名变成泛称,统称祭祷活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说”祭是一种以论说的方式说服神灵满足祭祷者诉求的言语行为。祭祷者将面临的灾难或困境诉诸神灵,祈求解除忧患,给予福佑。伴随这种言语行为,会产生一种独特的言辞样式,它以论说为手段,以说服为目的,使用特定的语气与措辞向神灵表达祭祷者的诉求。郭英德先生指出:“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于是人们就用这种言说行为(动词)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名词),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因“说”祭而产生的这种言辞样式,我们称之为“说”体。
“说”之成体:从言语行为到文章体式

据现有文献判断,殷商时期已有作为言语行为的“说”祭;晚周时期,由“说”祭产生的言辞样式被命名为“说”体。
《墨子》在论述“兼爱”时举商汤为祈雨而行“说”祭为例,其对“说”祭祝辞的记录与称引,呈现了“说”由言语行为到文章体式的生成过程:
且不唯《禹誓》为然,虽《汤说》即亦犹是也。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即此言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以祠说于上帝鬼神,即此汤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汤取法焉。且不惟《禹誓》与《汤说》为然,《周诗》即亦犹是也。
孙诒让注云:
《周礼·大祝》六祈,六曰“说”,郑注云:“说,以辞责之,用币而已。”此下文亦云“以祠说于上帝鬼神”。若然,则说礼殷时已有之。
孙诒让认为《汤说》之“说”即《周礼·大祝》“六祈”之“说”,并指出“说”礼殷时已有。其实这段文献不仅表明殷时已有“说”礼,还表明晚周已有“说”体。《墨子》将商汤的祝辞命篇为《汤说》,与《禹誓》及《周诗》对举,“誓”与“诗”既是言语行为,也是文章体式,则“说”与“誓”及“诗”可并列为文体。又同为涉汤事,《尚书》分列“汤誓第一”与“汤诰第三”,“誓”与“诰”既为文体,那么“汤说”之“说”也为文体不言自明。在前引《九店楚简》与《睡虎地秦简》“日书”中,“说”常与“盟”“诅”并举。《周礼·春官·诅祝》:“诅祝掌盟、诅、类、造、攻、说、禬、禜之祝号,作盟、诅之载辞,以叙国之信用,以质邦国之剂信。”郑玄注云:“载辞,为辞而载之于册,坎用牲,加书于其上。”诅祝既然能据“盟”“诅”之祝号撰作文辞并载之于册,那么“说”之祝号也能成为文辞且自成一体。
吴承学先生指出,“在某种场合,对某种文体形态的使用,一开始具有偶然性,人们的文体意识是朦胧的。此后,在类似的场合,不断地重复运用某种言语模式以表达类似内容,对特殊形态的言语运用形成习惯,技巧日渐成熟,文体因此逐渐成熟和定型,而文体分类观念亦随之发生。”客观地说,“说”体在先秦祭祷文献中更多地是以一种隐藏或包孕的形式存在,即作为整个“说”祭活动记录的一部分或一个段落,很少以独立的篇章姿态出现。但“说”祭祝辞的频繁出现,以及前人将“说”祭祝辞命篇为“某某说”并与其他文体并举的辨体行为,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至迟在晚周时期“说”体已经形成。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保存着大量的“说”祭祝辞,为我们把握“说”体的内涵与形态提供了丰富的例证,姑举几例:
周家台秦简:
已龋方:见东陈垣,禹步三步,曰:“皋!敢告东陈垣君子,某病龋齿,苟令某龋已,请献骊牛子母。”……所谓“牛”者,头虫也。”(简326−328)
操杯米之池,东向,禹步三步,投米,祝曰:“皋!敢告曲池,某痈某破。禹步芳糜,令某痈数去。”(简338−339)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梦:人有恶梦,觉,乃释发西北面坐,祷之曰:“皋!敢告尔。某有恶梦,走归之所。强饮强食,赐某大富,非钱乃布,非茧乃絮。”则止矣。(简13−14)
行到邦门困,禹步三,勉壹步,呼:“皋!敢告曰:某行毋咎,无为禹除道。”即五画地,掓其画中央土而怀之。(简111−112)
清华简:
恐溺:乃执币以祝曰:“有上茫茫,有下汤汤,司湍滂滂,侯茲某也发扬。”乃舍币。救火:乃左执土以祝曰:“皋!诣五夷,绝明冥冥,茲我赢。”既祝,乃投以土。
结合《墨子》“汤说”与上述文献,我们不难发现“说”体形成的若干重要标志。从内涵上看,“说”体产生有特定的应用场合与功用目的,用于祈求神灵解除忧患,如已龋、破痈、祛梦、除道、救火、恐溺。从形态上看,“说”体有特定的套语、句式与章法结构,形成了独特的言语模式。如引首有“祝”“祷”之类行为动词;以“皋”为发语词,此即郑玄所言“嘄”,是为了提醒神灵注意的长声呼唤;以“敢……告”表达诉求,向神灵提出自己的愿望;文辞大多有韵律,音节齐整,如“非钱乃布,非茧乃絮”“大命不敢请,佩玉不敢爱”。

“说”祭祝辞因其特定的情境、内涵与形态而固定为格套,具有鲜明的文体属性。从祭祷记录中析出的“说”体文,由于是口头表达的文字记录,因而具有鲜明的口头化、简约化、民间化特征。在周秦时期,还存在另一种“说”祭祝辞,它不是“说”祭仪式后对祝辞的简单记录,而是“说”祭仪式前有意撰作的祝辞文稿,因而具有书面化、体制化、文人化特征。“说”祭祝辞的篇章化,标志着“说”体的完全形成。接下来我们将分析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说”体文本——《尚书·金縢》中周公之“说”与《秦骃玉版》中秦骃之“说”,以阐述“说”从言语行为到文章体式的生成过程。
先看周公之“说”。《尚书·金滕》记载了周公为武王祛病而行“说”祭的过程,周公的“说”辞不仅含义丰富且具有层次,“陈论其事”的过程还非常讲究策略。《尚书·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墠。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圭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王
翼日乃瘳。……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
文中“史乃册祝曰”一段为周公的“说”祭祝辞。作为“说”体,该文目的非常明确,希望先王能够祓除武王之病——“遘厉虐疾”。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周公提出了让自己代替武王罹病的方案——“以旦代某之身”。为了说服先王接受自己的方案,周公提出了令人难以拒绝的理由——“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为了促使先王答应自己的请求,周公采用了软硬兼施的论说策略——“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圭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
除了成熟的说辞与高明的论说策略,《尚书·金縢》最值得关注的是周公之“说”已十足篇章化,无论是内容的深度还是篇幅的长度都绝非一般“说”祭祝号的记录可比。“史乃册祝曰”一句,孔安国传云“史为册书祝辞也”,孔颖达正义云“史乃为策书,执以祝之曰”,表明周公的祝辞由史官事先写定,是正式的官方文书。史官对祝辞的写定,不但使周公之“说”变得条理清晰、逻辑严密、措辞得体,而且从思维的层面确定了“说”作为文体的可能性——它不再是对“说”祭祝号的简单记录,而是具备了立意、构思、修辞、命篇等环节的创作过程,这个过程表明“说”体的产生已从自发的言语行为上升为自觉的篇章撰作,“说”祭祝辞也从口头形式的祝号物化为书面形式的文本。末尾“以启金滕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再次表明周公之“说”在“说”祭之前即以“书”的形式呈现,是史官有意撰作的书面文本。

再论秦骃之“说”:
有秦曾孙小子骃曰:孟冬十月,厥气戕凋。余身遭病,为我慼忧。呻呻反侧,无间无瘤。众人弗知,余亦弗知,而靡有定休。吾穷而无奈之何,咏叹忧愁。
周世既没,典法散亡,惴惴小子,欲事天地、四极三光,山川神祇、五祀先祖,而不得厥方。牺豭既美,玉帛既精,余毓子厥惑,西东若惷。
东方有土姓,为刑法氏,其名曰经,絜可以为法,□可以为政。吾敢告之,余无罪也,使明神知吾情。若明神不□其行,而无罪□宥,□□蜸蜸,烝民之事明神,孰敢不精?
小子骃敢以介圭、吉璧吉纽,以告于华大山。大山有赐,已吾腹心以下至于足髀之病,能自复如故,请□祠用牛牺二,其齿七,□□□及羊豢,路车四马,三人壹家,壹璧先之;□□用二牺、羊豢,壹璧先之;而覆华大山之阴阳,以□□咎,□咎□□,其□□里,世万子孙,以此为常。苟令小子骃之病日复故,告大令、大将军,人壹□,□王室相如。
这是秦骃玉版上的铭文。铭文内容乃秦骃为祛病而向神灵“华大山”举行“说”祭的祝辞。祝辞结构谨严,层次分明,显然不是“说”祭祝号的简单记录,而是一篇精心撰作的书面文章。秦骃首先陈述自己久病不愈却无从医治的惨状,借此博得神灵的怜悯和同情。接着秦骃解释自己本想用牺牲玉帛祭祀神灵,却因周世衰落、典法散亡而不知所措;幸而有刑法氏土经可为法正,秦骃告诉他自己并无罪愆,希望神灵明鉴。最后秦骃祈求神灵让自己康复如故,允诺将用牺牲、玉璧、车马来祭祀华大山,并强调一旦康复如故,将让地方、军队长官与王室一块来拜祭神灵。
与一般说辞直接向神灵表达诉求不同,秦骃的说辞没有直奔主题,而是在提出诉求之前做大量铺垫,比如描述自己久病不愈的惨状,解释无法可依的无辜。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秦骃极力营造悲苦的氛围,向神灵示弱,就是想博得神灵同情。这种“苦肉计”加“苦情戏”的论述策略往往容易奏效,在情与理两个层面都能打动神灵,说服神灵接受自己的祈求。除了布局谋篇,秦骃的说辞在遣词造句方面也颇具匠心。开头用节令气候的肃杀衬托自己久病不愈的凄惨,言辞哀伤而惹人怜恤;中间铺陈自己想要祭祀的神灵与打算供奉的祭品,语带夸张而充满诱惑;最后提出自己的诉求并允诺祭祀的等第,语气诚恳而难以拒绝。此外,秦骃的说辞在语句上也很有特点,大量使用四字句式,语言整饬,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气势。可以这样认为,秦骃的说辞体现了高超的论说水准和娴熟的文字表达技巧,已是一篇相当经典的“说”体文。
综上所述,可知“说”祭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说”祭祝辞是这种言语行为产生的言辞样式。祝史把这种言辞样式整理成诉诸特定载体的文字记录,成为一个内容与结构相对完整的文意单位,便构成篇章。在流传过程中,有人根据该篇章的内容、创作目的、体式等性质,将其命名为“某某说”,“说”便具有文体的意味。当这种言辞样式在重复使用的过程中被固定成格套,祝史又依据这种格套撰作书面的篇章,“说”便由言语行为变成了文章体式,成为具有特定内涵与形态的文体。

战国时期,诸子驰说,策士横议,出现了一种议论性质的说体。《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师旷之对,晏子之说,皆合势之易也,而道行之难,是与兽逐走也,未知除患。”《 吕氏春秋·审应览·重言》:“成公贾之讔也,贤于太宰嚭之说也。太宰嚭之说,听乎夫差,而吴国为墟;成公贾之讔也,喻乎荆王,而荆国以霸。”晏子与太宰嚭之“说”属议论形式的说辞,著于竹帛,便是议论性质的说体。秦汉以后,“说”作为文体已被广泛接受。陆机《文赋》论文章“体有万殊”,便包括诗、赋、论、说等十种文体。《 后汉书·冯衍传》提及冯衍善著,也包括赋、诔、铭、说等多种体式。刘勰《文心雕龙》将贤臣向君王的进谏之辞与行人策士的游说之辞都归入说体,与议、传、注、评等共同构成论体。真德秀《文章正宗》分文章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议论类包括说、书、论、对等体,录有《赵良说商君》等十二篇说体文。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收录战国至汉初的说体文,如苏秦《说秦惠王》、张仪《说韩王》等共三十八篇。姚鼐《古文辞类纂》将文章分为十三类,其中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辞赋六类都包含不同类型的说体,仅书说类便收《触龙说赵太后》等三十八篇说体文。历代文体学论著与文章选集表明,战国时期议论性质的说体已相当成熟且盛行于世。
一般认为,说体之兴与晚周诸子的论说与游谈有着密切关联。章学诚云:“周秦诸子……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笔之于书,而非有意为文章华美之观;是论说之本体也。”刘永济云:“说体之盛,始于战国游谈。纵横之士,尤工驰说。”诸子论说与游谈促成了说体的兴盛,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感兴趣的是,诸子发表学术理想,谈论治国方略,为何要命名为“说”?换句话说,既然刘勰认为论体“陈政,则与议说合契”,为何要在“论”“议”之外另立“说”体?这是对说体之名的疑惑。诸子撰作说体文,有无可资借鉴的论述模式?换句话说,从文体溯源的角度看,影响说体产生的因素是什么?这是对说体之实的疑惑。在我们看来,诸子陈政的活跃只是战国时期说体兴盛的外部条件,并非说体兴起的内在根源。古代仪礼多为文体之源,《文心雕龙·宗经》云“《礼》以立体,据事制范”,《释名》云“礼,体也,得事体也”。事体与文体的关联为我们考察说体起源提供了思路上的启发,可以借“说”之名逆推“说”体与“说”祭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比两种说体的文体特征,我们发现祭祷之说在“说”之语义、文体的功能与属性、论说的方法与策略、论说的逻辑与思维等诸多方面都影响了议论之说。
从说之语义看。祭祷性说体与议论性说体之间的渊源关系,首先体现在作为文体名称核心要素的“说”字上面,二者的语义基本相同。作为言语行为,“说”有两个基本义项:解说与谈说。许慎《说文解字》:“说,释也。从言兑。一曰谈说。”桂馥《说文解字义证》:“说,释也者。《易·小畜》释文引作'说,解也’。《广雅》:'解说也。’……《周易》有'说卦’,《庄子》有'说剑’。”桂馥支持许慎的观点,认为“说”的本义即解说。杨树达持论跟桂馥、许慎不同。他从“说”字形符“兑”入手,认为“说”的本义是谈说:“盖兑者锐也……言之锐利者谓之说,古人所谓利口,今语所谓言辞犀利者也。”杨树达认为,“谈说者,说之始义也。由谈说引申为说释之说,又引申为悦怿之悦”。值得关注的是,杨树达所举四条论据,第一条便是《周礼·春官·大祝》“六祈”之“说”,其后三条都是诸子与策士之“说”。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杨树达又以祭祷之说与议论之说互证,如《吕氏春秋·劝学》“凡说者,兑之也,非说之也。今世之说者,多弗能兑,而反说之”一句,杨树达云:“愚谓'兑’与《周礼》'攻’'说’之义相近,故吕氏以与'说之’为对文。盖吕氏言,凡说人者,在以辞相攻责,非谓使人悦怿也。今世之说者弗能攻责而反悦之,此世之所以乱,不肖主之所以惑也。” 杨树达的论述过程无意间证明了祭祷之“说”与议论之“说”同出一源,语义基本相同。无独有偶,高亨在笺注《吕氏春秋·劝学》篇时,也对“说”之音义做了新的诠释:“亨按'说者’之说当读为'说教’之说,'说之’之说当读为'喜悦’之悦。兑读为夺,实借为敓。兑、夺、敓古通用。……此言凡说教者乃彊取学者以从我,非顺学者之意以喜悦之;而今世之说教者,则多弗敓之,而反喜悦之也。”高亨释“说者”之“说”为“说教”之“说”(失爇切);“兑之”之“兑”为“夺取”之“夺”,“夺”与“敓”通,又无意间打通了“说”与“敓”的界限——在卜筮祭祷简中,绝大多数的“说”字正是以“敓”字形式出现的——这再次证明祭祷之“说”与议论之“说”的语义基本相同。
从文体的属性与功能看。“说”之语义基本相同,导致了祭祷性说体与议论性说体的属性和功能大体一致。《释名·释言语》:“说,述也,宣述人意也。”《广雅·释诂》:“说,论也。”孙诒让据此认为六祈之“说”,是“陈论其事”的意思。再看议论之“说”。陆机认为“说炜晔而谲诳”。六臣注曰:“说者,辩词也,辩口之词,明晓前事,诡谲虚诳,务感人心。”表明议论性说体的本质是陈述事实的辩词。从这个角度看,祭祷性说体与议论性说体属性一致,都属于论体。只不过前者是祝史向神灵陈论自己的诉求,后者是诸子或策士向人主陈论自己的主张。以犀利的言辞陈述并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则是祭祷性说体与议论性说体一致的功能。只不过前者试图说服的对象是神灵,而后者试图说服的对象是人主。
从论述的策略与方法来看。陆机认为说者可以“炜晔谲诳”,而刘勰认为应坦诚相待:“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而陆氏直称'说炜晔以谲诳’,何哉?”其实对于议论性说体来讲,炜晔谲狂或披肝沥胆只是策略与方法的差异;就目的而言,感动对方、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主张,二者殊途同归。祭祷性说体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同样是祈求神灵祛病,《尚书·金縢》中周公之说软硬兼施,称得上炜晔谲狂;而秦骃玉版中秦骃之说掏心掏肺,则可谓披肝沥胆。在具体的说体文本中,很容易发现议论性说体与祭祷性说体策略与方法的一致性。试举一例。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 年),秦国攻打楚国,黄歇试图说服秦王放弃攻楚:“(黄歇)说昭王曰:'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斗而驽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请言其说。臣闻之……’”这种提请对方“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论述策略,与《尚书·金縢》中周公试图说服先王祛除武王疾病如出一辙:“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如果按照议论性说体的命名方式,《尚书·金縢》中的周公之说可以称之为《周公说先王》,秦骃玉版则可以称之为《秦骃说华大山王》。
从论述的逻辑与思维看。诸子常常引用“语”类文献作为论说与游谈的资料,其中便包括祭祷类故事。《韩非子·显学》以巫祝说神“使若千秋万岁”来类比儒者说王“听吾言则可以霸王”,讥讽作为显学的儒家学说不切实际,对人主开空头支票。《 吕氏春秋·异用》以网者之祝与商汤之祝作比,用“未必得鸟”与“网其四十国”两种不同结果论说治国者当以德服人。《 墨子》除《兼爱》引商汤祷雨之祝来论说“兼爱”,《耕柱》还用翁难乙铸鼎之祝来论说“鬼神之明智于圣人”,《鲁问》又以鲁人豚祭之祝来论说“施人薄而望人厚”的荒谬。商汤以身祷于桑林的故事,除《墨子·兼爱》外,还见于《吕氏春秋·顺民》与《说苑·君道》。诸子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出了许多论说之术,《说苑》“善说”云:“孙卿曰:'夫谈说之术,齐庄以立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谕之,分别以明之,欢欣愤满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行矣。’”其实只要仔细揣摩《尚书·金縢》中武王的说辞与秦骃玉版中秦骃的说辞,所谓“谈说之术”便已了然于胸。除了以理服人,议论之说还讲究以情感人:“故凡说与治之务莫若诚。听言哀者,不若见其哭也;听言怒者,不若见其斗也。说与治不诚,其动人心不神。”这同样容易让人联想到秦骃祷病时的哀叹与悲鸣。“说”祭原本就见于日常生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可“说于神灵”。耳濡目染之下,诸子论说、游谈时受其影响,不但采用巫祝之说作为论说的资料,还因袭其论说的策略与方法,进而影响议论之说的逻辑与思维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综上所述,我们从说之语义、文体的属性与功能、论述的策略与方法以及论述的逻辑与思维等层面比较了祭祷之说与议论之说,我们发现两者之间极其类似。从发生的时间来看,祭祷之说无疑要早于议论之说。高步瀛论说体源流时指出,“三代之世,必不以扺掌议论为长;腾口有功,其在春秋之季”。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流行于“三代之世”的祭祷之说与产生于“春秋之季”的议论之说,二者之间乃源与流的关系,祭祷之说影响了议论之说的形成,议论之说是祭祷之说的别体。

在议论性说体中,存在一种比较独特的文体,它由“经”与“说”两部分组成。“经”是学说或观点的纲要,《左传·昭公十五年》:“礼,王之大经也。”孔颖达疏云:“经者,纲纪之言也。” “ 说”是对“经”的解释或说明,吴讷《文章辨体》云:“按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这种由“经”“说”前后呼应形成的文体,一般称为经说体。
“经”“说”组合成文体,较早见于《墨子》。《墨经》六篇,《经上》《经下》是纲要性条目,文字简短,除两条有十一字,其余者不超过十字;内容简约,先提出概念,再对其作简要界定。《经说上》《经说下》与《经上》《经下》对应,是对经文的诠释、说明或例证。如《经上》云:“故,所得而后成也”;“体,分于兼也”;“知,材也”。《 经说上》分别解说云:“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值得注意的是,《经下》已有“说在……”的提示语,“说”即解释说明该节经文要旨的理由或例证,如上文所举“说在同”“说在类之大小”“说在二与斗”等。《墨子·经上》云:“说,所以明也。”孙诒让注曰:“《说文·言部》云:'说,说释也。一曰谈说。’谓谈说所以明其意义。毕云:'解说’。”
《韩非子·储说》是经说体的典范。《储说》分《内储说上·七术》《内储说下·六微》等六类,每类又分“经”“说”两部分。“经”是观点提要,概要说明论点;“说”是说明论点的具体例证。如《内储说·七术》开篇列出人主治国的七条纲目:“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接下来简要概述每条纲目的内容,即“七经”,如“经一参观: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哀公之称'莫众而迷’”。与“七经”相对应的是“七说”,如“说一”:
卫灵公之时,弥子瑕有宠,专于卫国。侏儒有见公者曰:“臣之梦践也。”公曰:“何梦?”对曰:“梦见灶,为见公也。”公怒曰:“吾闻见人主者梦见日,奚为见寡人而梦见灶?”对曰:“夫日兼烛天下,一物不能当也;人君兼烛一国,一人不能拥也。故将见人主者梦见日。夫灶,一人炀焉,则后人无从见矣。今或者一人有炀君者乎?则臣虽梦见灶,不亦可乎?”
不难看出,“说一”中的事例是“经一”中“其说在……”一句的完整阐释,是解说“参观”的具体例证。这种说经方式与《墨子·经说》有很大不同。《墨经》内容深奥,其“说”又大多采取以理释理的方式,理论思辨色彩浓厚,后人要读懂“说”的诠释并非易事。《韩非子·储说》采取以事释理的方式,用生动具体的历史故事或寓言故事来阐述自己的学说与观点,借助于“说”,“经”的内涵便简单明了。
经说体的产生与战国时期诸子的辩说之风有关。周勋初先生指出:“他们在宣讲或辩难时,势必要先提纲挈领地列出论点,然后加以解释和发挥,这样记录成文时,就成了经说体。”周先生进而指出,《吕氏春秋》编写的体例“也是依据'经’'说’前后呼应的原则。每纪首篇采用了阴阳五行家著作的'月令’,起到'经’的作用;其后联缀的四篇论文,则对'月令’作重点的理论阐述,起着'说’的作用”。这种以“说”释“经”的思路延续到汉代,影响了刘向编撰《说苑》。有论者以《说苑·臣术》为例,指出“《臣术》共二十五则,除第一则总论外,其余选录的都是有关君主与大臣选贤举能、勤政节俭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实际上是对总论的具体化,即通过历史事实来对总论加以论证……由此,刘向撰写的总论与其下编撰的资料存在一种阐释关系,也就是经说、经传关系”。
在儒术独尊之前,儒、道、墨、法等诸家学派均可称自家学说与观点为经。章太炎云:“古之为政者,'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故诸教令符号谓之经。……经之名广也。”章氏指出,孔子有《孝经》,老子有《道德经》,墨子有《经》上、下,韩非内、外《储说》也署名为经,原因即在于此。孙诒让注《墨子·经上》,开篇就说:“毕云:'此翟自著,故号曰经。’”与此相应,自家学说的解说是经说,而他家学说及其解说便是小说。庄子分百家之学为七派,除“庄周”外,其他各家即是“小说”;荀子分百家之学为六派,除“子思、孟轲”外,其他各家即是“小家珍说”。“小说”之“小”,往往与低微、卑贱同义,《说苑·谈丛》:“夫小快害义,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伤德,大政不险。”以“小”饰“说”,也常见于周秦两汉的论说之中,体现了以自家学说为正统而睥睨他家学说的价值立场。扬雄云:“或问:'焉知是而习之?’曰:'视明星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桓谭云:“陛下宜垂明德,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⑧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小说”便成了不本儒家经典的一切学说的代名词。姑举数例:
孔疏曲傅传说,谓:“刘歆、班固不见古文,谬从史记;皇甫谧既得此经,作帝王世纪,乃述马迁之语,是其疏也。顾氏亦云止可依经诰大典,不可用传记小说。”
《法言·吾子》:“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晋李轨注:“铃以喻小声,犹小说不合大雅。”
惟《家语》《孔丛》《小尔雅》《神异经》《搜神记》等,或系伪书,或同小说,不敢取以说经,疑误后学。
上述文献中,“小说”或与“小声”“伪书”并称,或与“大典”“大雅”对举,价值判断的意涵非常明显,是与“经说”相对而言的派生词。
刘向校理群书,将儒家经典以外的书籍另立名目以为“百家”,其判断标准也是经说。《说苑序奏》云:“所校中书《说苑》、《杂事》……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所谓“浅薄,不中义理”,即是以儒家经说为参照系,对其他学说所作的价值判断,“百家”即“百家之说”。班固《汉志》“诸子略”著录儒、道等十家学说,他认为儒、道等九家“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而源自“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便定性为小说家。由此可见,《汉志》所言小说同样是以经说为参照系所作的学说归类,所录十五家小说,明确以“说”命籍者就有《伊尹说》等五家。班固注《伊尹说》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注《黄帝说》云“迂诞依托”。“浅薄”“迂诞”“依托”的定性与刘向对《百家》的定性如出一辙,仍然是以儒家经说为参照系所作的价值判断。记言类的《伊尹说》等因“浅薄”而归入小说家,记事类的《青史子》等同样因不本于经而著录于小说家。章太炎云:“史之所记,大者为《春秋》,细者为小说。故《青史子》五十七篇,本古史官记事……是礼之别记也,而录在小说家,《周考》《周纪》《周说》亦次焉。”

周秦两汉文献中的“说”“小说”等语词,以及诸子说经时所举的故事片段,很容易让人在追溯中国小说文体起源时浮想联翩,认为周秦时期就存在现代意义的小说。有论者“推断先秦时期曾存在一种以讲述故事为主旨的叙事文体”,“说体中的'小说’与后世纯文学分类中的小说文体,在许多特征方面的确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宽泛地讲,它们本身即可被视为文学性的小说”。更有论者断言“庄子'小说’一词,是后世虚构性叙事文体'小说’概念的创始。《汉书·艺文志》所录古代的小说家中就有五部以'说’为名,充分显示出'说’与'小说’的渊源关系”。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也很有迷惑性,不妨稍作辨析。认为先秦时期存在纯文学小说的看法,是基于现代小说观念的认知,以虚构故事作为小说的核心要素。姑且不论这种“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看法是否合适,即便如此,《墨子》“经说”与《韩非子》“储说”“说林”中的故事,也并非全出虚构,其中有大量历史事件与生活事件的记载。与其说出自诸子的向壁虚造,不如说出于诸子的记录整理。以《韩非子》为例。《外储说左上》中“宋襄公与楚人战”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内储说下》中“文公之时,宰臣上炙”见于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是当时的法律案例。周勋初先生通过详细比对,指出《战国策》中的故事见于《韩非子》的有37 则之多,因此他认为《说林》“是为创作而准备的原始资料汇编”,而“这些故事定然是从《战国策》系统的史书中引录过来的”。至于《庄子》中“小说”一词,纯粹是与“经说”相对的概念,庄周以此表达对他人学说的鄙夷与蔑视,与虚构与否毫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以《墨子·经说》与《韩非子·储说》为例,从诸子论说中抉发出经说体。经说体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与论说方式,“经”是对“说”的概括提要,“说”是对“经”的解释说明。周秦时期,经说体是诸子陈政的重要文体,广泛见于儒、道、墨、法等学派。诸子称自家学说为“经说”,他家学说便成了“小说”。两汉时期,“经”的概念得到强化,目录学家们在整理传世文献时,便借用“小说”一词,泛指所有不本于经典的论著。翟灏云:“古凡杂说短记,不本经典者,概比小道,谓之小说。”这样,由“经说”衍生出来的“小说”,既是一个文体概念,更是一种文献类别。由于兼具文体与文类的属性,甚至更偏重于文献价值内涵的判别,因此周秦两汉时的小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章学概念,与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更相去天渊。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11&ZD10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小说文体古今演变研究”(41300-20103-22205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