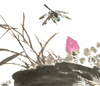《〈大正藏〉疑難字考釋》前言(節選)
文丨李國英
全面系統地整理歷代漢字,是漢字數字化的一項重要的基礎性的工作。歷代漢字的系統整理本質上就是把古今漢字的家底徹底搞清,包括字形的全面清理,異寫字和異構字的全面整理,實際使用的頻度和字域的調查等工作。只有這項工作做好了,做扎實了,我們才能給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提供一個漢字的清單,文字學界提不出這樣的清單,編碼界就没有一個全面而系統的編碼憑據,只能以未經全面整理的局部資源爲編碼依據,始終無法確切知道已編碼字占需要編碼字總體數量的比例,還有没有字需要編碼,編碼工作什麽時候可以結束。也不太清楚,編碼工作多大程度上滿足了漢字數字化工作的需求,哪些地方還不能滿足社會對漢字數字化的緊迫需求。顯然,上述想法只是一個理想化的推論,實際上,由於漢字的系統整理滯後於漢字編碼的現實需求,漢字編碼不可能等漢字全面而系統的整理之後產生一個需編碼漢字的清單之後再開始。但從整體而言,以往漢字整理工作的滯後,並不意味著漢字編碼不需要這樣一份清單,漢字數字化、漢字理論研究、漢字社會應用不需要這樣一份清單。相反,這樣一份清單是急迫需要的,整理出來的時間越早越好。有了這樣一份漢字字形的清單,我們就可以從總體上對清單中的全部漢字字形進行全面的認同别異的整理,整理出一組組由於書寫變異產生的異寫字,並爲每一組異寫字確定代表形體,建立每個異寫形和代表形的關聯關係;整理出一組組由於造字方法不同,或用同一種造字方法採用不同的構字成分產生的異構字,並爲每一組異構字確定代表形體,建立每個異構形和代表形的關聯關係;同時,還需要整理異字同詞的清單,在一組組記録同詞的異字中確定代表字,並建立每個字和代表字的關聯關係。在上述認同工作的基礎上,還需要系統地對同形字進行離析,建立同形字的清單,並將同形字代表的不同字依前面所述方法分别認同到相應的關係中。
上述整理工作,本質上是分層次的認同别異工作,認同的一個層次是異形同字,另一個層次是異字同詞。全面而系統的漢字認同别異工作,是從根本上提高漢字使用效率的基礎性的工作。從更廣闊的視野觀照漢語信息的數字化工作,還要整理詞與概念的關係,對表達同一概念的不同詞進行整理,建立起相應的關聯關係。這樣就可以建立起“形→字→詞→概念→概念系統”的關聯關係系統,這個經過認同别異分層遞進的關聯關係系統,是一種關係清楚、結構化了的信息資源。在這個結構化的關係鏈中,從最底層的每一個漢字形體,到中間的字、詞、概念,再到終極的概念系統,每一個要素都有一個清晰而明確的位置,並和其他要素構成清晰而明確的關係。在這個關係鏈條中“形→字→詞”是最基礎的,這項工作的基本流程是從現實文本出發,對異寫和異構形體進行認同,對同形字進行别異。在認同别異的過程中,有一個不能迴避的環節,就是疑難字的考證,主要包括音義未詳和關係未溝通兩種類型。音義未詳從來源分,有一般文本中的音義未詳,雖然有特定上下文語境,但是音或義,或音和義未詳;有字書中的音義未詳,字書中收録形體作字頭,未注明音或義,或未注明音和義,或直接注明音未詳、義未詳或音義未詳。關係未溝通指在各種類型的認同别異的工作中,當認同的未認同,當别異的未别異,或錯誤地認同别異,漢字的清單中,這些相關的屬性不清楚,就會直接影響上述關係鏈的建構。在這個意義上講,疑難字的考釋是漢字系統整理的基礎性的一環。
我國歷代文獻的文本,數量龐大,來源不同,形式多樣;文本中的文字也有古今的不同,字體的變異,從整體上對歷代文本中的漢字進行認同别異的工作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歷代漢字的系統整理,從文獻形態的角度劃分,可以分爲出土文獻用字的整理和傳世文獻用字的整理;從文獻内容的角度劃分,可以分爲一般文獻用字的整理和小學類文獻收録字的整理。各種來源的文字,在統一的目標下分頭整理,最後加以統合,應該是整理工作可行的路徑。一般文獻的用字,屬於使用狀態的文字,是真實使用的文字,真實文本中使用的文字,處於真實使用的現實環境中,具有兩個重要的特點:一是具有實際使用的語境,一是具有使用的時代信息。豐富的實際使用的語境,便於我們整理文字時歸納和確定文字的具體用法;使用的時代信息,便於我們整理文字時確定文字使用的時代。
但是,歷代文獻中出現的漢字實際使用的語境不總是足夠豐富,使我們能夠歸納出它的用法,加之,一個在語境中實際使用的未識字,它的讀音和意義是很難斷定的。這也就是歷代文獻中存在大量音義未詳字的根本原因。時代越早,語境資源越少,釋讀的難度越大,所以,卜辭中的大量甲骨文至今都不能釋讀。一般文獻中使用的字的時代信息是個複雜的問題,它涉及到文本產生時代的文本和文本抄寫或印刷時代的文本的複雜關係,一個特定文本中使用的字的時代需要綜合判斷。小學文獻當中收録的字,指歷代字書、韻書、訓詁專書中收録的作爲被解釋對象的字頭,這些字屬於儲存狀態的文字。就初始的來源而言,字書收録的字都是從一般文本中搜集而來的,就實際存在的小學專書而言,最早小學專書收字的直接來源是實際使用的文本,後出小學專書的收字來源則有兩個主要渠道,一是來源於實際使用的文本,一是從之前的小學專書中轉録。這些小學專書的目標,都是在搜集、整理、研究的基礎上,對收録的字進行解釋,解釋的内容包括讀音、意義、結構、理據、正俗、本借、源流等内容;不同類型的小學專書採用不同編排方式,反映字形、讀音、意義的聚合信息。這些重要信息反映了小學文獻編纂者對漢字搜集、整理、研究的結果,也是我們今天漢字的系統整理的重要憑據。
但是,小學專書收録的字,常常丢失了語境信息,字書在傳承中又會出現字頭字形的變異, 甚至是錯誤,這就需要我們在整理字書文字時,儘可能找出這些字使用的語境,還原字的真實的使用狀態,同時釐清字書的字形的變異,反映的是真實文本當中發生的文字變異,還是字書傳承過程當中出現的變異,辨明字書傳承過程中出現的錯誤字形。因此,一般文獻中的使用狀態的文字和小學專書中收録的儲存狀態的文字的屬性具有互補性,都是漢字系統整理的重要對象。而其中歷代小學專書收録的字,具有基礎性,是系統整理優先的切入點。以字書爲切入點整理漢字時,一方面要特别注意文本傳承過程中出現的文字現象,關注字書傳承關係和版本源流的梳理,另一方面要特别注意字書收録字頭字形及其説解與文獻實際使用狀況的互證,盡可能找出字書收字的來源。總之,整理漢字的兩種切入點,互有優劣,不可偏廢,而是雙向並進,各揚所長,互爲補充。
我從90年代初就投入了以全漢字整理爲終極目標的《漢語大字典》收字的整理工作,1999年第一屆招收博士生的博士論文選題都是古代字書收字的整理與研究。此後的二十多年的時間,我所指導的碩、博士生論文及博士後的選題一大部分都集中在古代字書專書,包括了《説文》《玉篇》《篆隸萬象名義》《類篇》《龍龕手鑑》《新修玉篇》《改併四聲篇海》《字彙》《康熙字典》《廣韻》《集韻《爾雅》《廣雅》《玄應音義》《慧琳音義》《可洪音義》等多種字書 (即包括狹義的字書、韻書、訓詁專書和音義書)收字的整理和研究。持續不斷地開展了以全漢字整理爲總目標的歷代字書文字的整理。
2002年,受教育部委託,我首次參加了國際標準化組織表意文字工作組(ISO/IEC JTC1/SC2/WG2/IRG)在越南河内召開的第二十次工作會議,參與並追蹤計算機字庫的國際編碼工作。二十年來參與計算機字庫國際編碼工作實踐,不斷強化我對漢字系統整理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促使我堅定地在漢字系統整理這條艱辛的道路上走下去。2007年,北京師範大學與教育部共建“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文字整理與規範研究中心”,中心的核心目標就是開展服務於國家文字規範和計算機字庫國際標準的漢字整理工作。2011年,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啟動“中華字庫”工程,我和周曉文教授共同主持承擔了“版刻楷體字書文字整理”項目包的研發工作。“中華字庫”工程曾於2006年被列入《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的重大建設項目,2009年被列入國家《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經過反復論證,於2011年作爲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重大科技攻關項目正式啟動。該工程以對文字學深入研究爲基礎,充分利用信息技術,探索建立人—機結合的文字搜集、整理、篩選、比對和認同技術平台,按照統一的規範和工程標準,以流傳至今的漢字和少數民族文字古今文獻爲對象,對古今漢字和各少數民族文字進行全面系統地整理,整理出古今漢字及各少數民族文字的總表,爲我國文字的信息化、規範化、社會應用和理論研究提供堅實的基礎。
“版刻楷體字書文字整理”項目的目標是,利用 “中華字庫”工程總體組研發的數字化漢字整理平台,按工程的統一規範,對流傳至今的全部版刻楷體字書用字進行全面搜集整理,提取字書中出現的全部字形,研製用字總表和未編碼字總表,爲計算機字庫國際編碼提供基礎性資源。完成這項工作主要需要:(一)在全世界範圍内搜集流傳至今的漢字字書(包括《説文》《玉篇》一類的狹義字書、《廣韻》《集韻》一類的韻書、《爾雅》《方言》《釋名》一類的訓詁專書和《經典釋文》《玄應音義》《慧琳音義》一類的音義書)目録(包括同一書的不同版本);(二)盡可能全面獲取各書及不同版本的紙本複製本和電子圖檔;(三)選定全文文本數字化的書目;(四)對選定的文本利用採集平台進行文本數字化;(五)提取未編碼字形,編制未編碼字形總表及屬性數據表,爲完成屬性數據,需要對字書中音義未詳的疑難字進行全面考證;(六)建立字書原始屬性數據庫,提取字書中説解字形、字音、字義、字際關係等信息,並建立結構化的屬性數據庫。其中包括的一個基礎性的環節,就是對歷代字書中存在的疑難字進行全面的搜集、整理和系統性的考證。近几年來,我與課題組的同仁及已經畢業的博士生組成了專門的小組,利用課題組自己建立的數字化資源,對歷代字書的疑難字進行了全面的清理與考證,已完成了大部分的考證工作。這項工作完成之後,課題組將向社會發佈考證的結果,包括已考出的字和待考字,這樣,就把近兩千年來在歷代字書中積累下來的疑難字的底賬算清,給全漢字的整理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距離我們進行全漢字整理的目標接近了一步。
正如前面討論所言,全漢字的整理、字書收字的整理和文本用字的整理,互爲表裡,相輔相成。多年來, 我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字書收字的整理工作上,同時也十分重視和關注文本用字整理工作,我曾指導博士生做過“《詩經》用字整理與研究”“《尚書》用字整理與研究”等一類的傳世文獻專書用字研究的論文。但大規模的文獻用字的全面整理非一人之力所能爲,非短期之内所能成,需從國家層面組織專家團隊進行持續的努力方能成其事,“中華字庫”工程就是一次此類工作大規模的實踐。我個人則因爲機緣的巧合,做了本書的撰寫工作。
《大正藏》,全稱《大正新修大藏經》,是大規模佛教典籍彙編——《大藏經》的一個版本。此版《大藏經》由日本高楠順次郎與渡邊海旭發起成立的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主持編纂,日本大正十三年(1924)開始編纂工作,昭和九年(1934)完成。著名日本學者小野玄妙等人負責編輯校勘工作,校勘工作以再雕本《高麗大藏經》爲底本,以當時能夠搜集到的大量刻本和寫本爲參校本,全面標記了版本異文,材料十分宏富,具有很高的學術參考價值,是目前在學術界頗受歡迎的漢文藏經集大成性的文獻。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古籍數字化的發展,佛經文獻的數字化也逐步開展起來,其中,90年代初,由日本各大學組成的佛典輸入團體SAT開始建設“大正新修大藏經原典資料庫”,經過多年的努力建成了《大正藏》電子資源庫,並在互聯網向全世界開放。2013年國際標準化組織表意文字工作組(IRG)啟動CJK編碼字符集擴F的工作,SAT派專家參加了會議,並將經過整理的“大正藏SAT DB”中的部分未編碼字提交,申請編碼。本書的寫作就是在SAT提交的申請國際編碼字表的基礎上展開的,當初的目的很單純,想對待編碼字進行審核,爲編碼工作提供專業依據。著手審核工作之後,發現其中包括大量音義未詳的疑難字,轉而進入疑難字考釋的工作。始料未及的是,這項工作一做,就持續了近十年的時間。這期間,正是我主持的“版刻楷體字書文字整理”項目研發的階段,兩項工作交錯進行,讓我切身體會到了字書文字整理和文本文字整理相輔相成的關係。

《大正藏》书影
近些年來,近代漢字疑難字的考釋成了一個研究的熱點,每年都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涌現。就其成果内容而言,總體上可以納入傳統語言文字學的考據的範圍,很多專家在考釋的過程中,不斷總結適合近代漢字疑難字考釋的方法,考釋方法逐漸走向細密化,使得考釋成果的可靠性也不斷提高。在這種條件下,進一步討論傳統語言文字學方法論的基礎,建構傳統語言文字學的方法體系,也應該是我們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目標。
就其本質而言,任何方法都是實現目標的途徑和手段。清代學者戴震在《與是仲明論學書》一文中指出:“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清楚地説明了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目標是經典的思想内容,而理解經典思想内容的途徑是從文字到語言,從語言到思想的發現程序,在這個程序中,文字是切入點,處在基礎的位置。清段玉裁《廣雅疏證序》一文進一步指出:“聖人之制字,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學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治經莫重於得義,得義莫切於得音。”把詞分解成音、義兩面,字則仍處於基礎的地位。同時,把考字的程序和語言文字本體的規律結合起來,認爲,在語言文字的本體上,是先有需要表達的意義,然後才有負載意義的聲音,有了音義結合的語言,才有記録語言的文字的形體。而考字,即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研究程序,是由上述語言文字本體規律制約的,它決定了其過程必然是“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的研究程序。這啟發我們認識到,以解釋書面語言意義爲目標的傳統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途徑和方法是由漢語語言文字的規律決定的,傳統語言文字學解讀文獻語言意義的方法,本質上是運用漢語漢字的規律來解決文獻語言中影響正確理解文獻語言意義的問題的手段。這個手段不是單一的一種方法,而是由衆多方法構成,内部成系統的一個方法集。
早在東漢時期,許慎就在《説文解字》一書中構建了漢字形義互求的方法,爲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礎。許慎在《説文解字敘》 中寫道:“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異也,初造書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又寫道:“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前面論述了漢字造字的原理及文獻與文字的關係,後面則明確提出了,小學教育的基礎是六書,而把六書作爲小學教育的基礎的根本理由,就在於“厥意可得而説”,也就是説,憑藉六書的理論,漢字的構形理據——漢字的形體和據以構形的意義之間的關係,可以得到解説。《説文解字》全書,以保持了原始構形意圖的小篆形體爲説解對象,每個字都先解説與形體相切合的本義,又根據本義分析該字字源結構,今人把它總結爲漢字形體、本義互求、互證的方法,即漢字的形義互求法。這一方法的具體含義是:根據保持了原始構形理據的漢字形體,推求漢字與形體相切合的意義,即字的本義;根據漢字的本義,分析漢字的字源結構,解釋漢字的構形理據,即漢字形體得形緣由。形義互求的方法,自許慎創立到今天,對傳統語言文字學一直發揮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成爲傳統語言文字學方法的基礎。其根本原因就在於,這種方法切合漢字構形的規律,本質上是運用漢字構形規律來探求、説解、論證漢字的形義關係。從今天的研究結果和認識水平來看,漢字的功能是記録漢語,爲了創製記録漢語的漢字,造字時就把漢字所要記録的漢語作爲造字的依據。和其他所有語言一樣,漢語包括讀音和意義兩個要素,依據漢語造漢字時,理論上有三種選擇:根據讀音,根據意義,同時根據讀音和意義。從漢字史的事實看,漢字個體字符的創製,這三種類型都存在。把讀音作爲造字依據的包括:用標音造字法造的標音字,如“齒”,本爲象形字,所從之“止”,爲後加的標注讀音的成分,是根據該詞的讀音選擇“止”字作標音成分的;用聲符造字法造的雙音符字,如“㐜”爲仇匹的“仇”的後出字,構件“求”和“九”都是根據詞的讀音選取的;用切身造字法造的切身字,如“ ”是切身字,是爲記録梵語“
”是切身字,是爲記録梵語“ (tya)”這個音節造的譯音字,造字時,把“”的讀音作爲造字的依據,根據前面的輔音“t”選擇了“丁”字,根據後面的“ya”選擇了“夜”字,“丁”“夜”組合成“”字,等等。把意義作爲造字依據的包括:用象形造字法造的象形字,用指事造字法造的指事字,用會意造字法造的會意字,增加或改變形旁所造的分化字等。同時把音義作爲造字依據的形聲字。從類型上看,漢字的造字依據和造字方法具有多樣性的特征,但不同造字依據和造字方法的數量分佈並不平衡,把意義作爲造字依據所造的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分化字在成熟的漢字體系中佔的比例很高;把讀音作爲造字依據造的標音字、雙音符字、切身字數量很少,只是特例;同時根據音義造的形聲字,義符是根據意義選取的,聲符是根據讀音選取的,也包括了意義,且形聲字聲符的聲首都是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這些表意字。因此,傳統語言文字學把形義互求的方法作爲最基礎的方法,是符合漢字系統的整體特征的。但是,在具體研究問題的過程中,還是要根據研究對象所屬的類型選擇不同的研究方法,比如,上述把語音作爲構形依據的標音字、雙音符字、切身字等,就不適合採用形義互求的方法分析和考證。
(tya)”這個音節造的譯音字,造字時,把“”的讀音作爲造字的依據,根據前面的輔音“t”選擇了“丁”字,根據後面的“ya”選擇了“夜”字,“丁”“夜”組合成“”字,等等。把意義作爲造字依據的包括:用象形造字法造的象形字,用指事造字法造的指事字,用會意造字法造的會意字,增加或改變形旁所造的分化字等。同時把音義作爲造字依據的形聲字。從類型上看,漢字的造字依據和造字方法具有多樣性的特征,但不同造字依據和造字方法的數量分佈並不平衡,把意義作爲造字依據所造的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分化字在成熟的漢字體系中佔的比例很高;把讀音作爲造字依據造的標音字、雙音符字、切身字數量很少,只是特例;同時根據音義造的形聲字,義符是根據意義選取的,聲符是根據讀音選取的,也包括了意義,且形聲字聲符的聲首都是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這些表意字。因此,傳統語言文字學把形義互求的方法作爲最基礎的方法,是符合漢字系統的整體特征的。但是,在具體研究問題的過程中,還是要根據研究對象所屬的類型選擇不同的研究方法,比如,上述把語音作爲構形依據的標音字、雙音符字、切身字等,就不適合採用形義互求的方法分析和考證。

《说文解字》书影
隨著傳統語言文字學發展,在形義二者互求的基礎上,又發展出形、音、義三者互求和古今形、音、義六者互求,使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研究方法越來越豐富,不斷系統化。段玉裁在《説文敘》“厥誼不昭,爰明以諭”一句的注中寫道:“誼兼字義、字形、字音而言。昭,明也。諭,告也。許君之書主就形而爲之説解。其篆文則形也。其説解則先釋其義,若元下云始也、丕下云大也是也。次釋其形,若元下云从一从兀、丕下云从一从不是也。次説其音, 若兀爲聲、不爲聲及凡讀若某皆是也。必先説義者,有義而後有形也。音後於形者,審形乃可知音,即形即音也。合三者以完一篆。説其義而轉注、叚借明矣。説其形而指事、象形、形聲、會意明矣。説其音而形聲、叚借愈明矣。一字必兼三者,三者必互相求。萬字皆兼三者,萬字必以三者彼此憿逪互求。”明確提出了“一字必兼三者,三者必互相求”的觀點。三者互求方法的最大價值,是把傳統語言文字學的方法從造字領域擴展到用字的領域。形義二者互求,依據的是漢字造字規律,形要求是保持了原始構形意圖的形,義是與形體相切合的義,用形義互求的方法解決問題的範圍只能限制在符合造字規律的形義關係的分析與考證。漢字一旦創製出來,進入應用領域,完成記録漢語的功能,就不是只記録形義切合的本義,還會擴展出新的用法,這就要求傳統語言文字學有適用於使用中的漢字的研究方法,形、音、義三者互求就是解決使用中漢字的研究方法。段玉裁所言“合三者以完一篆,説其義而轉注、叚借明矣”,轉注、假借就是兩種用字的方法。段玉裁的弟子江沅對這個問題概括更加清晰,他在《説文解字注·後敘》中説:“許書之要在明文字之本義而已。……經史百家字多假借,許書以説解名,不得不專言本義者也。本義明而後餘義明,引申之義亦明,叚借之義亦明。形以經之,聲以緯之,凡引古以證者,於本義,於餘義,於引申,於叚借,於形於聲,各指所之,罔不就理。……蓋必形聲義三者正,而後可言可行也。亦必本義明,而後形聲義三者可正也。”這段話清楚地説明了,許慎的《説文解字》主要是“明文字之本義”,而明文字本義的方法就是形、義互求。進入使用狀態“經史百家”的文字,除了記録本義之外,還要記録引申義和假借義,這就在客觀上要求有適合研究使用狀態文字的方法,這就是形、音、義三者互求的方法。而三者互求方法的基礎還是形義二者的互求,即所謂“本義明而後餘義明,引申之義亦明,叚借之義亦明”。段玉裁的《説文解字注》就是運用形、音、義三者互求的方法研究文獻用字的典範。
更難能可貴的是,段玉裁還明確提出了古今形、音、義六者互求的方法,使傳統語言文字學的方法更趨系統和嚴密。段玉裁在《廣雅疏證序》中説:“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義,有今義,六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五。”在形、音、義三要素互求的基礎上,又加上了各要素古今變異互求互證的方法。古形和今形可以互求,古音和今音可以互求,古義和今義可以互求。古形和今形的形體差異,是漢字書寫變異的結果,而書寫變異是有規律的,古形和今形的互求,就是利用漢字書寫變異的規律證明古形和今形的形體變異關係;古音和今音的差異,是漢語語音變化的結果,而漢語語音的變化是有規律的,古音和今音的互求,就是利用漢語語音變化的規律證明古音和今音的語音變化關係;古義和今義的意義差異,是漢語語義演變的結果,而漢語語義的演變是有規律的,古義和今義的互求,就是利用漢語語義演變的規律證明古義和今義的語義演變關係。而形變的形體源頭,音變的讀音源頭,義變的語義源頭,都需要通過形、音、義三者互求,最終需要形、義二者互求來實現。三者互求是由二者互求派生的,六者互求是由三者互求派生的,二者互求是根源,是基礎,三者互求、六者互求是二者互求的衍生物。它們之間形成一種相互依存的方法體系,運用這一套方法,就使得古今實際使用的書面漢語的形、音、義之其然和所以然可以互求互證,具有了系統的可論證性。如果把這些方法分解成具體的方法,則可以包括:根據漢字據義構形的造字規律及漢字形義統一原理產生的漢字形義互求的方法,根據漢字用字假借規律及用字本借關係原理產生的求本字的方法,根據漢語詞義演變規律及詞義引申的本義引申義關係原理產生的求本義的方法,根據漢字書寫變異規律及本形與變形的關係原理產生的求本形的方法,根據漢語語音變化規律及本音與變音的關係原理產生的求本音的方法,根據漢語造詞規律及漢語詞際之間的發生學關係原理而產生的詞語推源法等等。推源和理流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本質上語言文字各要素之間源流關係的互相證明,加之形、音、義之間的相互證明,就使得傳統語言文字學對文獻的解釋具有了立體的可論證的特征。不難看出,傳統語言文字學的方法,都是語言文字本體規律的運用,本質上是利用語言文字本體規律解決語言文字使用中語言文字形式、内容及形式與内容的理解,包括文獻中疑難字詞的考證。從這個意義上講,把傳統語言文字學判定爲經學的附庸,雖有一定道理,但並不十分準確。説這種説法有一定道理,從經學的視角看,傳統語言文字學確實只是解經的工具;從語言文字研究的本體看,傳統語言文字學也没有把語言文字本體規律的研究作爲主要的、核心的目標,而是爲了達到“解經”的目的去研究語言文字本體規律的。説這種説法不十分準確,從學科分立的立場看,經學和傳統語言文字學,雖有密切的關係,但都是各自獨立的學科,各有各的目標和旨趣,不存在誰是誰的附庸的問題,就如數學是很多學科的工具,我們不會把數學學科看作其他學科的附庸一樣。從本體研究和應用研究的關係看,傳統語言文字學以解經、解釋文獻語言作爲主要目標,爲了實現自身的研究目標,它也必然會涉及語言文字本體規律的研究,但本體的研究畢竟不是主要目標。隨著學術的發展,現代學科分化的趨勢,漢語的語言文字本體研究發展爲獨立的學科是符合學術發展的趨勢的,是歷史的必然。但是,語言文字本體研究獨立學科的建立,並不意味著以解釋文獻語言爲目標的傳統語言文字學消亡,或者是弱化,因爲兩者研究目標、旨趣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學術的、社會的功能也不同。
本書的主旨是對《大正藏》的疑難字進行考證,使用的方法總體上就是傳統語言文字學的方法。因應材料的特殊性,方法的選擇會有些偏重,對一些特殊的現象,也會採用一些特殊的方法。以下從運用形音互求的方法考證疑難譯音字、運用文本文字同化的規律考證疑難同化字、運用分化造字的規律考證疑難分化字、運用書寫規律考證書寫變異產生的疑難字等方面分别略作説明。